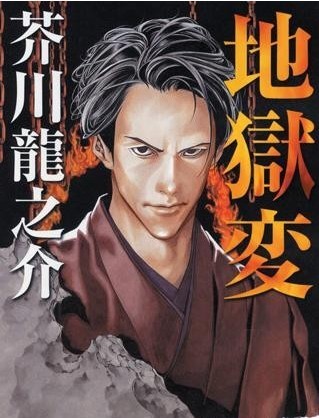短篇作品-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尖丛中劈过去就跟小和尚们劈柴一样,怎么就能把那个他们都视为魔头的“一刀门”掌门劈着呢?这个问题他想了好久,很久后的一天,一心法师突然参悟了,大笑着说了一句“原来就是没招啊”,然后圆寂了。
鲍二可不关心他一向讨厌的和尚操什么心,他看到大师兄被自己一刀砍倒后松了口气,知道自己已经赢了。他觉得很痛快,上一次打架是和铁皮在河滩上对掰的时候,严格的说那次他输了,这么久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使他这会儿非常的开心。他用的是刀背,大师兄肩骨被敲断了,可是没什么大事。大师兄坐在地上楞楞的,鲍二赶紧过去扶他,大师兄拔开他的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样啊,是我参得不透啊!”他自己站起来,一脚把掉在地上的刀踢到一边,鲍二没抓住,他头也不回的下了岭,再也没回“一刀门”来。后来听说他成了江湖上独来独往的怪侠,老跟名门正派过不去,他从此再没使兵器,但那拳头比拿着兵器的人还厉害。鲍二多少年后在丝瓜藤下喝着稀粥听着大师兄的传闻时,觉得师兄好象还是把什么东西弄拧了,不过不要紧,鲍二从没牙的嘴巴里漏出一句话:“我还是最佩服他。”
那天鲍二打完了架就记挂着回乡下去,师弟们不让,喊着掌门拉着他的袖子不让走,让他留下来教徒弟。鲍二急了,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招式可教你们!我那是劈柴的招式,只能在乡下混,这个什么破江湖我呆不了!鲍二说“一刀门”将来怎么样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只是个乡下人,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去吧。
鲍二也是头也不回的下了山,在山脚下看见有个熟悉的人影儿在前面晃,追上去揪住一看,真的是多少年没见的师父。师父说在这儿等他呢,说师娘怕大师兄想不开,追上去劝解去了。鲍二问师父为啥不也追去,师父指了指脸上的一道红巴掌印说你师娘不让,她说好不容易有知道闺女消息的机会了,如果我不肯留下来问问你她跟我没完。鲍二说梅子好得很,还给师父添了个孙子。师父听了乐得合不拢嘴,说好,好,过一阵子我和你师娘去乡下看你们去。然后师父拍着鲍二的肩膀说,你这个关门弟子我没收错,好小子,有出息。
师父也惦着大师兄,颤颤地跑去追他和师娘了,临走说代我向你嫂子问好,她现在叫什么来着?黑姑是不是?鲍二听了追在后面问你知道黑姑以前叫什么吗?师父脚下跑得快,看上去想溜掉,边跑边说我忘了。鲍二一个劲儿的追,他问黑姑到底是什么人呢?师父越发跑得快,在前面嚷着说你管她是什么人呢,她是个明白人!鲍二听这话不追了,他也觉得要不要知道黑姑到底是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
鲍二就这样回了家。
那天看比试的人中有几个刚出江湖的年青人,他们非常的崇拜鲍二这个心目中的大侠,于是偷偷地跟在他后面回到了乡下,他们想看看大侠生活的地方,因为他们想大侠一定是用了什么办法才练出这么高的武功的。年青人看到鲍二走进了一家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农家小院,女主人带着儿子上地里去了,院子里静悄悄的。
鲍二推开院子门,院门发出“吱嗄”的声音。那时候银杏叶儿飘,满院子金黄,年青人们惊奇地看到,听到院门响从屋里摸摸索索走出一个干瘦的瞎老太婆,而他们崇拜的大侠就在那金黄的院子里对着瞎老太婆倾金山倒玉柱地跪了下去。
黑姑试探着问:“是二娃子回来了吗?”
二娃子规规矩矩地对嫂子磕了个头,恭恭敬敬地应了声:“是我,娘。”
(完)
222007年10月28日 星期日 2:02:47 PM《香蝶作品集》 2007。8武侠系列·春华秋实
短篇作品红花
(一)
月华之美在它的朦胧,朦胧月色中总有迁客骚人于重重花影间饮着琼浆感叹自己的际遇。卢秀才便是这样一个多情的才子,满腹诗书却埋没于学堂作个教书先生,这使他常常会做出怀才不遇的感叹。
今夜又是月色朦胧,卢秀才的心情亦因那月色而凄凄,于是拎一壶酒,带几碟小菜,于城外十里长亭独坐。
酌一杯酒,月影于杯中婆娑起舞,望亭外,夜露压得花枝低,卢秀才在月下花间很优雅地啜下一口酒,幽幽地叹了口气,然后站起来,走到亭边望月举杯,念道:“举月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有笑声从亭外林中传来。
这是很扫兴的一件事,世上雅者多瞧不起俗人,而俗人也多半看不惯雅者,卢秀才早已看透了这一点,只是看透了也无可奈何,他叹口气,端着杯慢慢踱回亭中石凳旁坐下,依然沉溺于自己的伤感。
“先生好雅兴,如果寂寞的话,不如在下陪你饮一杯罢?”一个飘逸的身影从林中走了出来,那是一位俊朗的后生,著青色的长衫和软帽,腰间的三尺长剑给他平添了几分侠气。
卢秀才没有回答,这个年轻人的潇洒为他添了几丝惆怅。年轻的时候卢秀才也佩过剑,但那只是文人装束的一部分,虽然也认真练过,却从未真正使用过一次长剑。
少年走进了长亭,“可以吗?”他和气地笑,笑得很洒脱,一付无忧无虑的样子。卢秀才站起来整了整衣衫,然后,揖手行了一礼。虽然不喜欢,但礼数却是不可不周的。
对饮几杯后,卢秀才慢慢发现这个少年非但会喝酒,诗词也作得极好,字里行间隐隐透出几分清新之气,绝非一般俗人的附庸风雅,这使卢秀才肃然起敬,再次整衣行了一礼。
“少年游侠,文武双全,实在是令在下佩服。”卢秀才诚心诚意地赞道。少年只是谦谦地一笑:“哪里,在下只是胡乱说几句罢了,先生才是才华横溢,令在下佩服得紧。”这话让卢秀才受用得很,他忽然觉得,今夜偶遇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件幸事。
后来卢秀才睡着了,伏在亭中的石桌上。
少年见状,楞了一楞,本来兴致正高,秀才突然睡着,总是件遗憾的事。少年推了推秀才,见他的确只是睡得香甜,于是放了心,转头向亭外说道,“出来吧。”
树叶儿沙沙地响,花枝被拔开处,一个穿着束身黑衣的年轻女子走出来。她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衣衫稍稍有些被露水打湿。
“为何不多等一会儿呢?等我和先生喝完酒也不迟嘛!”少年叹道,“找我有事吗?”
“是逍遥剑杜少华吗?”女子走进了亭子,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血色,而且,也没有什么表情。
“正是在下。”少年微笑着回答,他仔细地打量这个女子,她很年轻,模样也端正,长得有点像“小仙子”吴玉笙。
杜少华想:很久没有去看望玉笙,明天去看看她吧,顺便向她爹提亲。想到这里,杜少华笑了起来——玉笙一定会很开心,等了自己这么多年,总算能给她一个交待了。
“逍遥剑杜少华,作案二十一起,杀人十七,伤人三十五,刑判处死。”黑衣女子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来,轻轻摊开放在杜少华前面的桌上。纸上有白纸黑字的处死令,以及鲜红的官府大印。
杜少华楞住了,“你是谁?”
“刽子手。”女子收了纸,放回怀中。
“官府的刽子手?”杜少华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情重复了一遍,“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女子没有回答,她从腰间取下了一双手套,黑丝的手套,慢慢往手上戴去。
“真是愚蠢!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寻死路的好。”杜少华站起来,不屑地说,“看在你刚才只是点穴而没有伤害卢先生的份上,我放你一条生路。”
“跟我走吧,”女子戴好了手套,抬起头说,“我也不想让秀才睡醒后,第一眼看到的,是你的尸体。”
夜风吹来,吹得人背上发凉,两个人站在那里凝视着对方,谁也没有马上动手的迹象。
“我所杀都是该杀之人,官府就不分青红皂白?”杜少华叹了口气。
“杀人就是杀人,你没有权利随便夺取别人的性命。”女子回答,“什么理由也不行。”
“那么你又凭什么杀我?”杜少华反问。
“我有按律杀人的权利,”女子回答,“我是刽子手。”
杜少华笑了:“这样美的月色,这样美的意境,却从一个女人口里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很奇怪吗?”他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喜欢杀人吗?”
“与喜不喜欢没有关系,除不了藉。”女子漠然地回答。
是的,在官府的簿本中,军有军籍,匠有匠籍,连妓女和刽子手也有他们的籍,这些籍决定了人的身份,而且很多都是世袭的,这个就叫命,是很多人生来就注定的东西。
“是吗?”杜少华突然对面前的女子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这样回答的话,说明你真的是刽子手了。”
“跟我走吗?”女子再次问道。
“好吧,既然你不可能收手。”杜少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与女子并肩走出了长亭,“但是,我不会取你性命。”
“那很抱歉,除非有新的判令,否则我会杀死你。”刽子手没有丝毫的感动。
“你认为官府的律条都是对的吗?”杜少华问。
“刽子手不需要多余的判断,”女子回答,“但是,我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他们消失在黑暗中。
那天晚上,卢秀才到了后半夜才醒来,醒来后发现那个飘逸的少年早已如来时那样无声息地走了。卢秀才很伤感,因为他知道除了那个人,世上已经很少有人能够了解他的抱负与才华。自那以后,他常常会于月色姣好之夜去十里长亭,希望能再遇见那个少年,与他把酒共饮。“下次,一定要先问问他的名字。”卢秀才想,“也许,能和他成为真正的朋友。”
十天后,“小仙女”吴玉笙得到了“逍遥剑”杜少华的死讯,他失足从崖上跌落下来,头颅破裂而死。
杜少侠的葬礼很隆重,因为他是江湖中有名的青年俊杰,一身正气,追杀并除掉了不少武林败类。黑道白道都有人来送葬,连一贯对他有所避讳的官府也送来了挽联。吴玉笙以妻子的身份为杜少华送葬,据说,她将为杜少侠守孝三年。
杜少华出殡的时候,名叫秀的那个刽子手正在溪边洗她的双手。黑丝手套掖在腰间,早就洗干净了,但手上会有不净的感觉。最难洗净的是指缝,虽然手套编得很细致,可是,日子长了,总会有血从丝与丝的缝隙间渗过来,渗到指缝中。
溪水澄清,清可见底,一个小和尚从秀身边走过,他笑着对秀说:“你身上好臭,血的臭味。”
(二)
打正月初八夜里上了灯,京城的街道晚间就热闹起来,当街数座灯架上吊挂着各式精巧花灯,四下里围列着诸门买卖。往东看,雕漆床、螺钿床,金碧交辉;往西瞧,羊皮灯、掠彩灯,锦绣夺眼。北一带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厢尽皆书画瓶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入了夜便喜洋洋地往街上走,灯市热闹得紧。
仙月楼的楼下是那花灯挂得最花梢的地方,人也较他处要来得多。红绡同两个楼里的姐妹,搭伏着楼窗子,边磕着瓜子边看楼下的热闹。
红绡把绫袄的袖子搂着,露着那纤纤玉指夹着瓜子儿。她几个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着瓜子儿,把磕了的瓜子皮都吐下来,落在人身上,一边嘻笑不止,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个个仰着往上瞧。红绡偏又把那一对小金莲从栏杆处露出半截来,勾引得人心慌。
鸨婆扭着腰肢走上楼来,“红绡,客来了。”
“妈妈,今儿我要陪人去看灯,实在没有空呢!”红绡满不在乎地把瓜子送到嘴里去。
“该不会又是那个小白脸吧?”鸨婆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红绡啊,妈妈是为你好,那样的小白脸,你养着他有什么用,当他靠得住么?”
“钱我没给你少赚,养不养小白脸那是我的事吧?”红绡翻了翻眼皮。
鸨婆哼了一声,看看她已定了心,小声地骂了两句,只好走下楼去。
“你那个王公子来了。”陪着磕瓜子的姐妹推了红绡一把,示意她看楼下街道,果然王公子站在楼下仰头望她,不一会儿便上得楼来。
“死人!等你你却总不来!”红绡从窗口那儿走过去,拿粉拳在王公子胸口捶了两下。
“红绡姐姐莫怪,这两天没了米钱,正忙着四处筹借,所以来得晚了。”王公子将她搂在怀里,软语相劝。
“你又骗我,前几日不是才与你银子吗?”红绡的手忽然摸得公子胸前有一物,便笑道,“是不是买了什么好东西给我?”边说着,边伸手去公子胸袋中将那东西掏了出来。王公子脸色大变,赶紧去抢,红绡已经跑了开去。
红绡往手里看,见王公子怀里那东西是一只大红光缎平底小鞋,鞋尖绣着鹦鹉摘桃,针线十分的细致。
“那……那是准备买给你的,不知合不合适,所以先拿一只来你试试。”王公子的脸上早变了颜色。
红绡往手上看了半天不哼声,然后把那鞋往脚上试了试,觉得颇有些紧,便恼道:“哪里找来的破鞋,你还当个宝贝掖着!”一边奔到柜边,将剪刀抢到向手中红鞋绞去。
“姐姐使不得!”王公子惊叫一声,扑上去抢,红绡已将那鞋绞得稀烂。王公子站那里楞了半天,红绡把烂鞋扔在地上,不理他,坐回楼边自顾自地磕瓜子。王公子鼻子里狠狠地哼了一声,甩袖子走出门去。
“那样的小白脸,原本就是靠不住的。”一个姐妹道,“红绡与他的钱,只怕都花在别的女人身上了。”
“象我们这样的人,哪里会有人真心相待呢?红绡要从良,还是找个有钱的人好。”另一个姐妹应声道。
红绡叹了口气:“这个我原也知道,见他文雅,还指望能有些与众不同,谁知仍是这种货色。”
姐妹们见她闷闷,有心宽慰于她,便问道:“狮子楼要放烟火



![(伪装者同人)[伪装者]明楼中心短篇集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1/214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