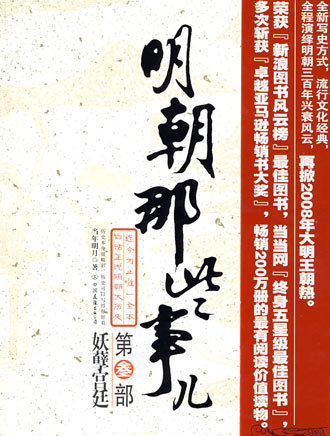夏娃的女儿-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难为情,也许他根本不承认这叫杂乱,因为他自己对此已非常习惯。他吸烟总是用
一只粗笨的德国烟斗,把天花板和被猫爪子撕破多处的糊壁纸熏成了黄色,使屋里
的东西看上去就像刻瑞斯'注'的金色谷子。那只猫有一身光亮蓬松的长毛,任何看
门女人见了都想要它。它安详大方地呆在那儿,俨然是这屋子的主妇,长长的胡须
使它显得非常庄重。它威严地蹲在一架美妙的维也纳出产的钢琴上。伯爵夫人进来
时,它冷冷地向她投去假情假意的一瞥,一个对伯爵夫人的美貌感到惊异的女人大
概也会用这样的目光来迎接她。猫蹲在琴上一动不动,只抖了抖右边两根银色胡须,
然后又把它那两只金色的眼睛转向施模克。钢琴又老又旧,木质倒很好,漆成金、
黄两色,可是已经很脏,油漆也已褪色、剥落了。琴键磨损得像老马的牙齿,而且
被烟斗上掉下来的烟油染成焦黄。钢琴搁板上的一堆堆烟灰告诉人们,前一晚施模
克曾乘着这古老的乐器向音乐的盛会驰骋。方砖地上满是干泥巴、碎纸片、烟灰和
不知何物的碎屑,就像有一个星期没打扫的寄宿学校宿舍的地板,从那里,校工可
以扫出成堆成堆又像厩肥又像破布的东西。地上还有栗子壳、苹果皮、红鸡蛋壳'注'
和不小心打碎的盘子,碎片上粘着干了的酸菜糊。如果伯爵夫人的眼光稍微老练点
的话,就能从这些碎屑上了解到施模克的生活情况。这些盖满尘土的垃圾形成一张
地毯,在脚下咔吱作响,从壁炉里冉冉飘下的灰烬落在上面。壁炉用彩石砌就,里
面有一块煤做的圣诞柴,圣诞柴前面是两块就要烧尽的木柴。壁炉上方有一面镶着
框的镜子,镜框上刻有一些狂舞的人像。镜子的一边挂着那只威武的烟斗,另一边
是一只中国陶罐,这是教授放烟草的地方。屋里的家具同莫希干部落'注'的印第安
人茅屋里的家具一样简单:两张靠背椅,一张铺着又薄又瘪的垫子的小床,一张没
有大理石台面的被虫蛀过的五斗柜,一张缺了腿的桌子(上面还留有吃剩的简单早
餐),都是从旧货店里买来的。窗户没挂帘子,插销上悬着一面刮胡子用的镜子,
上面搭着一块布片,是用来擦拭刀片的,布片上留着一道道污痕,这大概是施模克
为美惠三神'注'和尘世所作的惟一牺牲。那只猎是受保护的弱者,得到最好的待遇,
它占用了靠背椅上的一只旧垫子,垫子旁边放着一只杯子和一只白瓷盘子。然而,
施模克、猫和烟斗,这活生生的三位一体,把这些家具搞成的样子是任何文笔都描
写不出的。烟斗把桌子烧坏了好几处。猫和施模克的脑袋把两张椅背上的绿色乌得
勒支丝绒磨得油腻腻的,又光又滑。猫承担了一部分清洁工作,要是没有它那条蓬
松美丽的尾巴,五斗柜和钢琴上空白的地方大概永远得不到打扫。屋子的一角堆着
鞋子,要清点其数目必须作一番了不起的努力。五斗柜和钢琴的台面上堆满了乐谱
本,书脊被虫咬坏,边角发白、磨破,一张张纸头从硬纸夹里露了出来。墙壁上一
溜边贴着女学生们的地址,是拿粘信封用的小面团贴上去的,面团下面没有纸头就
表示该地址已经作废。纸头上有粉笔写的若干算式。几只前一天喝空了的啤酒壶装
饰着五斗柜,在那堆古旧的物件和乱纸中,它们显得又新又亮。一只水罐上搭着一
条毛巾,一块蓝白相间的普通肥皂湿淋淋地放在柜子的香木贴面上,这就是老人的
全部卫生设施。衣帽架上挂着两顶帽子,都已旧了,还有那件伯爵夫人一直看见他
穿在身上的三层领外套。窗下摆着三盆花,大概是德国花;紧靠着花盆有一根冬青
条做的手杖。虽然伯爵夫人的视觉和嗅觉在这儿感到不舒服,但是,施模克的微笑
和目光犹如神灵的光辉,使屋里黄黄的色调变得金光灿烂,使杂乱无章变为生气勃
勃,遮盖了室内的寒伦相。这位神奇的人物懂得很多神奇的东西,也向别人揭示出
很多神奇的东西,他的灵魂像太阳一样闪光。他见到自己的圣赛西尔时笑得那么坦
诚、那么天真,以致周围一切都焕发出青春、欢乐、纯洁的光芒,这是人类最珍贵
的财宝,他把它们慷慨地倾倒给人们,并用以遮盖自己的贫困。无论多么倔傲的暴
发户也会觉得,计较这位音乐之神的使徒居住与活动的环境是一件可鄙的事。
“啊,亲爱的伯雀(爵)夫人,什么风怕(把)您吹来的?”他说,“难滔
(道)我套(到)了这个年纪还要唱赞美歌吗?”这个想法使他爆发出一阵难以遏
制的大笑。“难滔(道)我蹦(碰)上好运气了吗?”他带着狡黠的神情接着说,
然后又像孩子似地笑了。“您丝(是)为音乐而来,不丝(是)为一个可怜人而来,
这我自(知)滔(道),”他显得有点伤感地说,“但丝(是),不管您丝(是)
为什么而来,您要自(知)滔(道),这里的一切——肉体、灵魂和财产,全苏
(属)于您!”
他拿起伯爵夫人的手吻了吻,一滴眼泪落在那只手上。这善良的人每天都惦着
人家给他的恩德。欢乐使他暂时忘却,可是当他记起来时,感受就加倍强烈。他立
刻拿起粉笔,跳到钢琴前的一把扶手椅上,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地在纸上写下几个大
字:一八三五年二月十七日。这个动作是那么可爱天真,并且带着那么不可遏制的
感激之情,伯爵夫人深深地感动了。
“我妹妹也要来的,”她对老人说。
“她也会来吗?什么司(时)候?什么司(时)候,但愿在我死之前来!”他
说。
“我代她来求您帮个忙,以后她自己会来谢您的。”她说。
“快,快,快说!”施模克喊道,“需要我做什么?丝(是)否需要套(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只需在每张纸上写明:签此票据支取一万法郎。”说着她从手笼里抽出拿当
按照格式准备好的四张期票。
“啊,这很快就能判(办)到,”德国人像小绵羊一样温顺地回答。“只丝
(是),我不自(知)滔(道)我的笔和墨水在哪儿。走开,米尔先生,”他对猫
喊道,猫无动于衷地看着他。“这丝(是)我的猫,”他指着猫对伯爵夫人说,
“这只可练(怜)的猫和可练(怜)的施模克生活在一起!它多漂亮!”
“是的,”伯爵夫人说。
“您腰(要)它吗?”他问。
“您真这么想吗?”她说,“它不是您的朋友吗?”
猫遮住了墨水瓶,此刻它猜到施模克要用,便跳到了床上。
“它机灵得像猴知(子),”他指着床上的猫说,“我叫它米尔,为的是颂扬
我很熟悉的我们柏林伟大的霍夫曼'注'。”
好心人在期票上签了字,天真得就像一个孩子做母亲吩咐他做的事,不假思索,
然而确信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一个劲儿对伯爵夫人介绍他的猫,一点不关心那些票
据,殊不知,根据涉及外国人的法律条文,这些票据可以使他永远失去自由。
“您的确认为,这些贴了印花的小字(纸)头……”
“您丝毫不用担心,”伯爵夫人说。
“我一点也不担心,”他粗声粗气地说,“我丝(是)问,这些贴了印花的小
字(纸)头真能使杜·蒂耶太太高兴吗?”
“啊!当然,”她说,“您给她帮忙,就如同您是她的父亲……”
“能对她有点用处,那我就感到很考(高)兴了。听我给您弹个乐曲吧!”说
着他把票据丢在桌上,一步跳到钢琴前面。顷刻间,这位天使的手指已在古旧的琴
键上来回跳动,他的目光已透过屋顶看到了天空,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已在空气中
回荡,沁入人的心灵。他自然而朴素地表现了神圣的绝妙的东西,他赋予木头和琴
弦以语言,正像拉斐尔画的音乐女神赛西尔在聆听她的天使们面前演奏那样。可是,
伯爵夫人待到签字的墨迹一干,便不再让他演奏下去。她将期票塞进手笼,用手拍
拍施模克的肩头,把她那容光焕发的老师从他翱翔其间的苍穹中拉了回来。
“我的好施模克,”她说。
“怎么?已经要走了?”他无可奈何地说,“那么您丝(是)为什么来的呢?”
他毫无怨言,像一条忠心耿耿的家犬立起身来听伯爵夫人讲话。
“我的好施模克,”她接着说,“这是一件生命攸关的事,争取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少流点血和泪。”
“还丝(是)老脾气,”他说,“去吧,天寺(使),去擦干别人的眼泪吧!
您要自(知)滔(道),可练(怜)的施模克把你们的来访看得比你们给他的年金
更重。”
“我们还会见面的,”伯爵夫人说,“以后每星期日您来弹奏乐曲,并且和我
一起吃晚饭,免得我们吵架。这个星期日我等您。”
“正(真)的?”
“请您一定来,我妹妹肯定也会定好日子请您去的。”
“那么我再幸福也没有了,”他说,“因为,以前只有当您的车子经过爱丽舍
田园大滔(道)司(时)我才能见到您,真不容易啊!”
说到这里,他抑制住在眼眶里滚动的泪水,把手臂伸给他美貌的学生,她感觉
到老人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这么说,您一直在想着我们?”她问道。
“总丝(是)在慈(吃)面包的司(时)候,”他说,“首先想到你们是我的
恩人,然后想到你们是最值得我爱的两位姑娘!”
伯爵夫人不敢再说什么:施模克的话里含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充满敬意的庄严,
一种忠实、虔诚的庄严。这个烟雾弥漫、满地碎屑的房间是敬奉两位女神的圣殿。
房间主人的崇拜感情与时俱增,而引起这种感情的被崇拜者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儿有人在爱着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她想。
老施模克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伯爵夫人上了车,伯爵夫人也同样激动,她用指
尖给他送了个优雅的飞吻,就是女人之间远远表示问好而互送的那种飞吻。施模克
见后,久久地站立在那里,直到车子已消失在远方还一动也不动。不一会儿,伯爵
夫人已进了纽沁根公馆的院子。男爵夫人还未起床,但是为了不让一位显贵的女人
久等,她披上一条披肩,套了件晨衣就出来了。
“夫人,这关系到一件善举,”伯爵夫人说,“办得愈快愈好,不然我是不会
这么早来打扰您的。”
“哪儿的话,我太高兴了,”银行家的妻子说,一面从伯爵夫人手里接过四张
期票和她的保证书。她打铃叫来贴身女仆。“泰蕾丝,告诉出纳,叫他本人马上给
我送四万法郎来。”
然后,她把德·旺德奈斯夫人写的担保书加了封,锁到桌子抽屉里。
“您的房间很雅致,”伯爵夫人说。
“纽沁根先生马上不让我住这儿了,他正叫人造一座新宅子。”
“您大概要把这一所给您的女儿啰?听说她要和拉斯蒂涅先生结婚了。”
纽沁根夫人正要回答,出纳来了,她收下钞票,把四张期票交给出纳。
“正好两相抵销。”男爵夫人对出纳说。
“还差跌(贴)现,”出纳说,然后看着签字,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施模克
丝(是)安斯巴赫的一位音乐家。”'注'他的话使伯爵夫人有点胆战心惊。
“难道我在做生意不成?!”纽沁根夫人用高傲的目光怒视着出纳说,“这是
我的事。”
出纳偷眼瞟瞟伯爵夫人,又瞟瞟男爵夫人,只见她们都板着脸。
“您可以走了,”男爵夫人对他说,然后又转向伯爵夫人:“请您再留片刻,
别让人家以为这场交易与您有关。”
“您真是乐于助人,我求您再行个好,为我保守秘密。”
“既然是为了一件善举,我当然会保守秘密的,”男爵夫人微笑着说,“我马
上叫人把您的空车调到花园那头去,然后我们一起穿过花园。不会有人看到您从我
家出去的,否则就无法向别人解释了。”
“您像一个受过苦的人那样待人宽厚,”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待人宽厚,可是我确实受过苦,”男爵夫人说,“但愿您的
善举使您付出的代价要小些。”
吩咐完毕后,男爵夫人取来毛皮拖鞋和披肩,把伯爵夫人送到花园的小门口。
当一个人像杜·蒂耶坑害拿当那样策划了一个阴谋,他是对谁也不会透露的。
纽沁根略知一二,他的妻子却与这些不择手段的计谋毫无关系。不过,男爵夫人知
道拉乌尔手头拮据,当然不会被两姐妹蒙骗,她完全猜得出这些钱将转到谁的手里。
她很乐意帮伯爵夫人的忙,再说,她对这种困境也深感同情。拉斯蒂涅所处的地位
使他对两个银行家的诡计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天他来和纽沁根夫人共进午餐。但斐
纳和拉斯蒂涅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她把她和伯爵夫人之间的一幕告诉了他。拉
斯蒂涅想不到男爵夫人会参与这件事,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是他
很多手段中的一种。于是他向男爵夫人指出,她可能已经打破了杜·蒂耶竞选的希
望,使他整整一年中所搞的种种骗术和所作的种种牺牲付之东流。拉斯蒂涅把事情
的底细告诉了男爵夫人,并且嘱咐她对刚才的错误只字别提。
“但愿出纳不要把这事告诉纽沁根,”她说。
中午时分,杜·蒂耶正在用午餐,仆人通报羊腿子到。
“请他进来,”银行家说,也不管他妻子在场,“怎么样,夏洛克'注'老兄,
那个人进监牢了没有?”
“没有。”
“怎么?我不是跟您说过,槌球场大街,旅馆是……”
“他已经付清了,”羊腿子边说边从公文包中抽出四十张钞票。杜·蒂耶脸上
显出失望的神情。
“对钱永远不能表示不欢迎的态度,不然会招来晦气的。”杜·蒂耶的伙伴不
动声色地说。
“太太,您是从哪儿弄来这些钱的?”银行家问妻子,一面扫了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