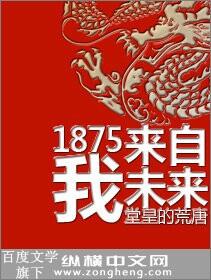5775-清代衙门图说(选载)-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就是说,清朝针对书吏所进行的立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事实上,地方各衙门几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设置书吏的,滥设的情况比比皆是,有的州县要超出法定吏额的几十倍,其中的原因既有规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也有利益的驱动使得制度的不合理无限放大的因素。
清廷允许地方衙门在人手不足时突破法定人数多设书吏,这种变通的办法成为书吏队伍膨胀的催化剂。在非经制吏中,有许多被称为“贴写”、“帮役”、“白役”的人员。从理论上讲,书吏五年役满,会从贴写、帮役中选择淳朴谨慎的人留下来,作为经制吏的补充,这也是对候补人员的一种鼓励,约束他们不得为非作歹,但结果却不是这样。盘踞在州县衙门的几十号上百号贴写、白役,为非作歹,比起经制吏来丝毫也不逊色。有的案件尚未审结,而家财已耗尽在他们之手,花户应缴纳的额粮尚未交上来,而加征的浮费已经耗去十分之二三,其他如株连无辜,贿纵要犯等事,大多数也是贴写、白役所为。州县官们对此睁一眼闭一眼,以至于乾隆帝说他们“不爱百姓而爱吏役”。当然,胥吏之害,不仅仅在州县衙门。比如凡是征解钱粮的时候,上司书吏要向州县书吏索取费用,因而州县书吏假借司费、纸张等名目,向纳税户摊派。又如司院衙门,凡遇到州县申详事件,必先发交各房书吏拟批送签,而在一迟一速、一准一驳之间,他们得以上下其手。所谓书吏之害,“自上及下,正不自州县始也”。
如果向上追查的话,症结所在就更为清楚了。中央各衙门的书吏因供职机构不同称谓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供事和经承两种,经承中又有堂吏、都吏、书吏、知印、门吏、火房、狱典等称呼,一般多称其为部吏、书吏。其各衙门的书吏也有定额,如户部是大部,定额书吏有238人,总计各衙门书吏在1200人以上。同地方书吏一样,不在册的书吏远远超出经制吏的数目,如户部书吏多达1000人以上,因为几乎每个在册的书吏后面都跟着不计其数的非经制吏。中央书吏有无薪水,文献记载多语焉不详。《清朝文献通考·职役一》记述清初“按季给以工食银两,其后屡经裁减”,但主要讲的是地方书吏,中央书吏并无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后者的收入主要靠索要地方陋规。这也是“需索链”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连接得天衣无缝的原因所在。
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运行中,部院书吏无疑掌握了相当的“裁量权”乃至处置权,因此外省有一件事到部,一定要预先派人与各部院书吏讲好价钱,出陋规多少,“能饱其欲,则引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书吏不是有司官监督吗?但这正是大玩猫鼠同眠的时机,司官岂能放弃。庸懦的司官,往往为其愚弄,不能自律的正好从中分一杯羹。司官之上不是还有堂官吗?他们实在太忙,由于事务繁多,一时也就难以觉察,而且既然看见地方有事情被驳回,也就不再产生怀疑,结果是“事件之成否,悉操于书吏之手,而若辈肆行无忌矣”。
乾隆初年,清朝政府考虑到地方和部吏的这种“交易”在京城难于查出,于是下令先从督抚开始清查,因为在这每一笔“交易”中,某件事用了多少钱,是何人经手,督抚没有不知情的。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督抚藩臬也有他们的算盘:京官本来就穷,一想起封疆大吏每年几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装入腰包,心中的气就来了,没事还要找事,何况地方官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那么经得起推敲?况且,今朝在外,明日就可能回到朝中做官,书吏得的好处,堂官、司官一样有份,断了人家的财路,日后的麻烦说不上会有多大。再者说来,这些钱在封疆大吏的眼里还真算不得什么,既然所费不多,又何必与书吏计较;图的是经过“陋规”这种特殊的润滑剂使案件早日完结,乐于应付还来不及,又岂能上报!说到底,这也不是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来,就便宜了那些奸胥猾吏,他们有恃无恐,“以诈骗为得计”,根本不把国法放在眼里。
这种自上而下的书吏“需索链”,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到最下面:部吏向督抚索要,督抚书吏索之司道,司道书吏索之府县,“层累而降”,最终的受害者,还是老百姓。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师爷与书吏之间的“猫鼠游戏”(1)
师爷与书吏之间的“猫鼠游戏”
“清官难逃猾吏手”。书吏的品性“奸猾如油”,因而,即使官清如水,也难逃猾吏之手。从法律上讲,州县官负有监督书吏之责,但从州县衙门实际的运行看,县太爷一般都把监督书吏的职责交给了幕友。尽管制度上是以官统吏,但官员事务繁重,不可能对所有的书吏一一监督,而幕友各有所司,“可以查吏之弊”。
汪辉祖提出:“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何以如此呢?按照州县体制的预设,州县官在组建自己的班底时,依照信任的程度依次是长随家人、幕友、书吏。如果从正面来理解,三者之间职能不同,但前者对后者有监督的作用。从幕友与书吏的关系来讲,幕友有监督书吏的职能。汪辉祖讲道,因为六房书吏尤其是刑书、户书所经管的事情,大多数州县官都不十分熟悉,因此“惟幕友是倚”,“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
事情都有两重性,如果幕友与书吏勾结作弊,不但监督失灵,而且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从清朝地方衙门的实际运行来看,幕友和书吏都隐然是一种职业,因此,其逐利的属性就会发挥作用,也就足以破坏本来没有更多保障的制度预设。雍正帝曾经说过:“从来任用书吏,不过藉其谙练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之幕客,诸事娴熟,可资商酌,不使书吏得操其权,自无可作之弊。”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利益的驱使,两者互为倚重,也互为利用,建立一种“猫鼠同眠”的合作关系。所谓“官一幕二衙门三”的民间谚语,说明分赃的主要是幕友和书役。乾隆十二年,有一位监察御史奏报说,各省幕友,大多数聚集省会,他们与全省上下各衙门书吏往来结识,因而掌握了所有衙门的内幕。有时他们也以同乡亲族的名义,投帖拜会书吏,彼此互相照应。每当州县有事向上请示时,省城的书吏就多方刁难,批驳不已。各州县书吏没有办法,不得不来到省会,访求与上司内幕熟识的幕友,厚礼重金相聘。书吏与幕友因此“彼此串合”。
书吏们也不甘心在衙门里“等生意做”,他们通常会主动与幕友接洽。嘉庆时期,书吏在衙门左近地方,设立“私馆”,专门用来传递消息,各省的名目也各有不同,比如广东省有外马放光、收光渡期等名目。衙门里的刑钱幕友,“交通书吏”,习以为常。
而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纷纷派家人到宫中探听消息,有的书吏以此作为捞取好处的捷径,连皇帝每天召见几次大臣,召见的是什么人,谁到地方去任官,谁出了事,都摸得一清二楚。甘肃省一向有类似幕友会的组织,加入者被称为“省友”。每当州县官上任时,他们通过各自与衙门的关系,向州县官推荐幕友,有的为经济条件差或者急需钱物的州县官借贷盘费、赊取财物,州县官也通过“省友”“周转通挪、延订为友,常驻省垣探听信息”。“省友”不会垄断这些事情,他们一般要同衙门里的书吏一起分享,以便互相照应,好事情大家都要有份。
长随有时也加入到这种游戏中来。嘉庆时期广东省以开设赌局为名,衙门长随和吏役互相勾结,买卖消息。赌局名曰“番摊馆”,实际是匪盗勾通兵役探听消息的场所。据说,省城关厢内外就不下二百处,主持开局的人,大多是各衙门的长随和吏役。如果有缉捕之类的行动,盗匪能够最准确最迅速的得到消息。
书吏把持衙门:“官去吏不去”
熟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升迁调补,以原位不动为大耻,当官的总希望自己的职位流动起来;但吏恰恰相反,希望像铁打的一样,长期把持衙门。
明代书吏长期盘踞某个衙门的现象,已经颇为严重。顾炎武在谈到州县弊政时,就指出“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顾亭林诗文集》卷一)。
有了前朝之鉴,清朝对书吏很早就注意防范。《钦颁州县事宜》有“防胥吏”一条,提到胥吏蒙骗主官的几十种伎俩。乾隆八年,有作为的江西巡抚陈宏谋鉴于该省吏役不下数千人,约束不易,还专门写了一部劝吏胥为善的书,取名《在官法戒录》,共308条,颁给全省各州县的吏役们。从国家立法的角度讲,清朝还构建了一套从法律到规章制度等至少表面上看来完善的约束机制,如《大清律例》、《钦定吏部则例》等针对吏役的条例有数十条之多,但这些法条对书吏而言,恰恰成为其手中的工具,因为他们每天都与这些条例打交道,练就的最大本事就是舞文弄法。就拿供职不得超过五年来说,他们应付的办法有许多,通常是“役满之后,每复改换姓名,窜入别部,舞文作弊”。还有的为逃避五年役满必须回籍的规定,每当将到五年之时,先行告退,即可不在役满之限,几个月后,重新充役。还有的干脆改名捐一笔钱,得一个小职位,然后以候选为名,得以潜留京中。而最令官府头痛的是,吏役居然将他的役缺视为自己的产业,以“缺主”之类名目,长期把持衙门,如果有人出了一笔钱,就将役缺暂时让出去,但他仍然可以控制这个缺位,甚至也不必亲自去衙门,也可以找个人顶替,但都不能改变他对衙门事务的把持。因而形成书吏长期把持衙门的局面,以致有“官转吏不转”“官去吏不去”的谚语。面对这些连连拆招的猾吏,连乾隆帝都无奈地说:“常言官更而吏不易,足为政治之害。”由于地方官调动频繁,而前任之吏,复留于后任,事权之重,反而比本官还大。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师爷与书吏之间的“猫鼠游戏”(2)
京中各衙门的工作,也完全听命于书吏。而书吏的武器仍是则例,是律以外的例案,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发家谋私之所能。乾、嘉时期曾多年充当幕友的洪亮吉估计,十分财物“入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胥已十之五矣”,他们“子以传子,孙以传孙,其营私舞弊之术益工,则守令闾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浅”(《意言·吏胥篇》)。
与科举出身的官员不同,书吏没有背负“经邦体国”的政治责任,而专以规避朝廷功令为能事,他们为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把持一方。冯桂芬说,尽管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歧视,但其“权势之盛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而“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他估计吏、户、兵、工四大部财政外的收入每年不下一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不下二千万。而这些巨额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进了书吏个人的腰包(《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信然。
“曾庆”如何变成“王曾庆”?
从立法的用意来讲,对命、盗等与民众切身相关的案件定有严格处分,体现了立法者良好的愿望,但在执行中往往适得其反。如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为二参,再展一年为三参,再展一年为四参。也就是说,一件盗案的最后结案期是三年零四个月,在此期间抓获案犯,官吏都可以免降级。尤其是盗案初、二、三参的处分只是住俸(停发薪水)、降留之类,对州县官仕途影响不大。即使到四参降一级调用时,如果有加级或者有级还可以抵消,因而只有很少情况才实降一级。知县是掌印官,典史为捕官,都是责任人,因此知县、典史平时必须“挣加级”,即先预备加级,用来四参抵消。
据《春明梦录》记载,四川某县有一位典史,任内有四参的案件三起,而他的加级也有三次,恰好可以抵消。但吏部作为四案处分,因他少一个加级,议定实降一级,即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请四川总督咨部。吏部立即开出各次案的详单,包括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回复。典史一看,部中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四川并没有这个案件,又禀请总督向吏部声明。吏部经“详细”核查,才知道前单所开“王曾庆”是“曾庆”的“误写”,因为部中抵消加级时,只由书吏写一个浮签挂起来,写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与原稿封册核对无误,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个红点,就算了事。本来典史费了力气挣来三个加级,恰好够抵消三案,但书吏故意将“事主”的“主”字写作“王”字,因此“曾庆”一案又衍生出“王曾庆”一案。尽管这是看册司员糊涂,但也是因为案牍太多,书吏巧于作弊,防不胜防。书吏本想通过这个案子让典史掏银子了事,但典史自恃有加级正好抵消,不肯花钱,书吏才设计陷害。因为各部案件太多,不能一一盖印,大多数情况是凭司官的红点为准。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但不敢捏造红点。因为书吏们迷信,说一捏造红点,就一定会破案。
书吏舞弊凭的就是例案繁多,一般人无法熟悉。书吏往往在稿尾挑剔几句话,一面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写信给地方官,吓诈钱财。外省官员尤其是州县官不熟悉例案,也抱着花钱消灾的心理,自愿出银子了事。在吏部当差十几年的何德刚说他当掌印时,凭着自己对例案熟悉,年纪又轻,每天能够处理例稿四五百件,凡是遇到这类稿尾查笔,就全部勾销,书吏们也经常拿着条文来争,何就对他们说:“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如何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所以在他做掌印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