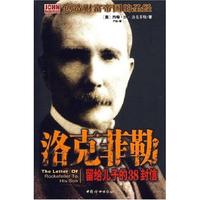3859-得不到 已失去-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在调频道的时候对妻子说,想和你说件事。她笑着坐到他身边来,倚着他,顷刻间一切寂灭。
儿子在外面发出了稚嫩而惊慌的声音,爸爸爸爸。
他急忙拂开妻子,跑出去,在一片黑暗中他摸索着找到了工具,去换保险丝。
当光明降临时,他眼睛有些睁不开,儿子还是伏在桌上写作业,妻子背对着他看无聊的广告。时钟滴答行走,水龙头没有关紧,他走过去拧了下,用足了力气水滴还是坚强不屈地往下淌,一小滴一小滴地诉说着流逝。
他把手放在水龙头下面,看着镜中的自己疲倦的一张脸,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磨平了棱角,成了照常行走的时钟,在有序的生活里荒芜一片。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一边脱衣一边问他,你刚才有事情和我说?他看着妻子淡黄色的文胸,随手拈了件事打发掉。妻子依偎着他沉沉睡去,他的眼睛在黑夜里一直亮着,不甘心就此成眠。
他的到来是不彻底的,站在自己的土壤上来探视我。类似于狗尾续貂,但他深邃的眼神让我无法洞悉到底。
我彬彬有礼地递了杯茉莉香片给他,他的沉默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压迫。记得当年上课时他冷峻的神情与坚硬的语气,他让我站着我便不敢坐,让我面壁我就一直与白色的墙壁相对,让我背课文我就必须把一字一句镶嵌入脑。这一切浮于表面的权威被一个悠久的抚摸一笔抹杀,从细长的脖子到瘦小的臀。教室里只剩下背不出课文的我和沉默的他,夕阳挣扎完最后一缕凄艳,远远地传来校工锁门的声音。我想象他用力关上每一扇门的乏味,想象他完成同一动作的机械,想象他在空荡荡的楼层里看到我们时刹那的惊诧。
我的老师拉着我往另一个方向下楼去,他的手掌如此有力脚步如此匆忙,以至于我有些趔趄。到了僻静的小径他毫无预兆地停下来,俯身清晰地夺走了我的初吻。
第一部分 再吃一颗糖小关(4)
我圆睁着眼睛,来不及整理连绵不绝此起彼伏的暧昧。空气里有桂花的清香,他的嘴里有浓重的烟味。
我喜欢男人嘴里的烟味。后来常常讨好地帮他点烟,在他抽烟时欢欢喜喜扑到他怀里索吻。我折磨他的身体,我置之不理。
我好奇,自私,而歹毒。他亦是如此。
我很快就悟透了他的用心,以及找到了对策。这一切与喜欢并无冲突,喜欢是轻描淡写的微蓝,就像天空纯粹的颜色,他无法将别的色泽强加于我。
1994年,我喜欢看他筋疲力尽的样子,喜欢他低低的恳求和懊恼,喜欢他无可奈何却不得不承认我还是孩子时的深深自责。
他知道我稠密的心思,却不能穿针引线一一化解,他陷在我的天真烂漫里无从释放。我总是大声尖叫,哭喊,他如履薄冰,满盘皆输。
我喜欢他,恐惧他。他喜欢我,恐惧我。
这样的招式一再重复,失去了光华与诱惑。有时他命令我坐得远一点,我委委屈屈坐在沙发边缘,隔不了多久他就忍不住挪过身来。我们搂抱,我们在搂抱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慵懒假期。
我去忠平南路接他,雨渐渐大起来。他再度拥抱我,于我的发间轻声念道,犹恐相逢如一场梦。我犹豫着推开他,编织出客气的微笑。
他何必折回,何必惊扰早已平复的过去呢。
我去衣橱里翻找宽大的衣服想给他换上,一双手像5年前那样从背后伸过来,我浑身一冷,急忙转过身来,他靠近我,把我的头抵在柔软的衣服上,像过去那样潮湿地亲吻我。
这个故事到此转折一下,因为我的情绪出现了波动。那些流利的娓娓动听哑然,我只消告诉你们,我死于两年前。
在他强行进入时我举起床边的台灯用力往下砸,他吃痛,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我们俩都有些失控,我说过我是一个激烈的女子。而他呢,他出现于一个不适合的时间,如果早一些,晚一些,天色暗蓝城市繁华,我们的寂寞可以一拍即合。
我为这个耳光而狂怒,猛然拉开床头的抽屉,抓起那把寒光闪闪的水果刀从他背后捅进去,进去,出来,我血液里隐藏的愤怒与力量被刺激得淋漓尽致。我已经不知道这些力量来自于何处,我又哭又笑,像孩子一定要得到那颗糖,像做爱不到高潮誓不罢休。
他厉声惨叫,摔落在床下,我赤裸着扑到他身上去,对他笑,刀子继续捅进去,麻木而机械地重复着拔进拔出的动作。
在血水飞溅之中,我想到5年前黄昏校工关上一扇又一扇门,想起阿潘抬起头任水滴盛开于身体的样子。这些意念稍纵即逝。我拼命的哭,破坏他身体的同时,我知道自己罪不可恕。
他奄奄一息,眼睛勉强地睁着,地板上艳红一片。我把刀子远远的丢掉,趴在他身上说,我会和你一起走,我会的。
他的身体渐渐转凉,发硬。我抽出蓝色的被单,慢慢擦拭他的脸,手臂,五官,细心的擦拭犹如那时他细心的吻,老师,谢谢你陪伴我。
我还是那样的歹毒,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站起身,走到厨房里,拧开煤气,心满意足地泡了杯速溶咖啡,然后坐回他身边,席地而坐。
打开电脑里九九给我的网址,听那首伤感的音乐。
满地狼藉。我的心一片宁静,自从小关走后,我从来没有这样宁静过。
我不想说我和小关的故事。
我不能承受这样的告别,叛逃,离弃。我几度觅死,都不能积攒足够的勇气,多么像垂死挣扎的鱼,流不出泪水的鱼,不能灵动自如的鱼。
每过一天,离毁灭就近一步。我在忠平南路看到他。
在我死去的两年,我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或者我没有死,或者他也没有死,只不过是噩梦一场。有时候我会想,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他说爱我,于是我温柔而感伤地承受了他。心满意足的是他,他穿好衣物离去,回到B镇继续过平静温和的生活。
我死了没有?死的是灵魂还是肉体,或者兼而有之。我不敢和你走在阳光下,我怕你猛然发现我没有影子,对于这些我满含忌讳,小心而谨慎。
多年前在学校舞厅里,我和小关共舞恰恰。我笑语盈盈,眉飞色舞。
我恨小关,这种横冲直撞的恨意如雨点般落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交待完毕。
请让我留在这间房子里,让你一直生活在对面。
一直这样。
第一部分 再吃一颗糖再吃一颗糖(1)
我对自己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很小很暗,萎缩在一个洞穴里,我警告自己不要哭,不要软弱。
2003年我本命年,生活非常艰难,过着将近半年入不敷出的生活,存折上的数字越来越令人紧张。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失去。朱朱笑话我说,也许可以失身。我也笑,失身不算什么,如果失声才叫要命。
我不能失去声音,我是一个靠声音吃饭的女人,在电台做DJ,每天凌晨和一帮躲在电话线背后神经兮兮的声音,一起打发时间。
没有人需要我。一边接听各种各样的声音,一边在心里冷静地想,他们只是为了倾诉,为自己的心情找一个垃圾箱,他们甚至不需要我的意见,只是为了宣泄。
在一份工作重复了2000天后,我失去了耐心,变得麻木。恋爱也是如此。我和张家白早就应该分开了——两个人一起吃饭,可以不说一句话。端着碗筷去厨房,听着自来水哗哗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的心也被一遍遍冲洗着。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
谁来拯救我,我多么想打碎这堆碗,打破这死一般的平静。意识静静地疯,表面仍然平静,甚至还顺便洗了只苹果吃了起来。
有点甜。生活就是这样,为了细节的美好,继续隐忍。
我已经记不清和张家白是怎样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相识了四年,那时他喜欢另一个女孩子,追求未果,所以一脸失意的他,犹豫地搭上了恋他良久的我。
我知道,起先他是做给那个女孩子看,以为对方会有所触动,惊觉他的珍贵。可惜那个女孩子无动于衷,甚至还和我保持良好的邦交,和我一起坐在学校图书馆门口吃冰淇淋。
我笑的时候心是冷的,静静地看着张家白的惆怅。按我的猜测,他会很快看清楚我没有利用价值,然后飘然远去。可那个女孩子先走了一步,找了个外国人,嫁到法国去。
临别时笑盈盈地祝我和张家白天长地久。
张家白握着我的手,越握越紧,一手心的汗,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他是用手掌流泪的。
张家白再可怜,也算赢了我。这样一个冰雪聪明的我,怎么会蠢到把一身傲骨交给别人践踏,而且张家白的心上人根本比不上我。
这样让人无可奈何的一个食物链,使我心生苍凉。优秀有什么用,美丽有什么用,不爱就是不爱。
我等他提出分手。足足等了三个月,他都没有提。我想他是太忙了,忙于考英语六级,忙于递推荐表,忙于联系工作,忙于写毕业论文,忙于给自己在这个勾心斗角的现实社会找一个位置。
我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拿着圆珠笔一笔一画地写张家白三个字,写了满满一页。我是喜欢他的,从第一次在寝室楼前见到他就喜欢。当时他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样子虔诚得有点可笑。我朝他好奇地看了两眼,他也看我,然后请我给一个女孩子带句话。
我做了他的传话筒。对方根本没有兴趣,皱着眉头,跑到窗边,冲楼下大声喊,张家白,我不要,然后啪一声,关掉了窗子。
张家白的爱情被关在了外面。
姿势真是果断而决绝,我如果也能做到,该有多好。可惜喜欢一个人,就溃不成军。
张家白,我对他的好,真是罄竹难书,一争吵,我就像倒豆子一样,绵延不绝地说下去。你那时没有钱,是谁把一个月的生活费都给你。你找不到房子,是谁跑断腿,替你租的房子。你的脏衣服都堆在床下,是谁一声不响地拿去洗了。同事排挤你,上司冷落你,是谁天天买晚报,帮你留意好工作,还用红笔框出来,替你寄履历。你母亲住院,是谁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赶回去替你尽孝。
张家白沉默得如一座石雕。
后来朱朱教育我说,程尔,对他越好,越显得贱,如果他根本不打算感激你,把功劳都念叨在嘴上,只会招致反感。
谁说不是呢,所以后来我也死心了,在30平方米的房子里,两座石雕一起坐着看电视。
一边听着电话里听众的牢骚,一边虚弱地劝慰,一边还在心里想着自己的烦恼,我的心被割成了许多碎片,我常常闭着眼睛说话,陷入了一片昏暗。
每次回家都是打出租,张家白从来不接我,我也不要求。和这样一个从来不曾深爱自己的男人在一起,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吧,我想。
我无数次臆想自己突然开口对他说,张家白,我们分手吧,或者张家白,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可是话到嘴边统统咽下,因为我知道,言者比听者更伤心,而张家白也许已经等了很久,他只是不善于主动拒绝。
第一部分 再吃一颗糖再吃一颗糖(2)
我也幻想自己会爱上另一个男人,他的出现使张家白黯然失色,我可以谈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可是环顾四周,除了谢顶秃头的上司,就是夸夸其谈的同事,要不就是开出租的司机。世上所有的司机都沉默,坐在他们身后,看他们的后脑,所有的后脑都相差无几。
既然男人都大同小异,何必再满怀期待,重新找一个,不如苟延残喘。那么,就和张家白天长地久吧,虽然他对我的感情极有限,但炎樱说——枕头上,两个头好过一个头。
我是抵不过一室寂寞的,拉了拉披肩,我重新陷入了幻想,幻想这世上有一只后脑属于我,他为我开车,穿过茫茫夜色,带我去远方,到达天堂。
可是到了终点,后脑都会回过头,一张乏善可陈的脸,右手接过我的钱,然后我下车,他开车一溜烟地走了,再也遇不到。
我越来越喜欢吃奶糖,一颗接一颗,甜腻得喉间难受。常常像个游魂般,去超市买了一大堆回来,蜷在沙发上,漫无目的地吃着。
为了获得生活中的一抹甜,要忍受多少痛楚。只有食物带来的甜,易如反掌,如此廉价的甜,欺骗自己的胃。
我有胃病,读书时就这样,发作起来,就蹲下去,拼命地咬自己的指头。有好几次张家白就在我身边,可他只是微微俯身,无关痛痒地问一句,不要紧吧。听起来多么像一个正好路过的旁人。
不要紧,我忍着痛回答他,心里冷冷地跟了句,死不了。
那么灿烂的天气,我蹲在地上,我喜欢的男人俯看我翻腾汹涌的痛意。
恍恍惚惚地想,张家白之所以四年来不提分手,只是出于一种惯性。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静,最终摧毁了我的爱情。现在,我已经彻底碎了,一碰就落下细屑。我们之间的维系,以前是我爱他,现在,我们都在等一个契机,推翻目前的生活。
朱朱也这样说,程尔,与其暮气沉沉地和张家白一起,不如放彼此一条活路。我笑,是,一点也没错,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可是已经耗了四年,就不介意再耗下去。
朱朱是一个女人,开一家首饰店,打扮得极光鲜,妆化得很艳,但一眼就能让人看穿了底细。吃了很多男人的苦头,所以眼神里透出衰老的气息,从前过惯夜生活,眼黑明显。朱朱是我的听众,她在电话里说,程小姐,你的声音真好听。
做完了节目,她又打过来找我,说和我一个

![[蜘蛛侠]2359人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729.jpg)
![(西游同人)[1599-藕龙]邻家猴山二三事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84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