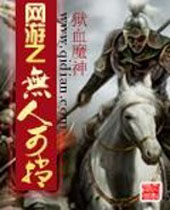无人处落下泪雨-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时候不用到场,免得一身臭气破坏了革命群众的情绪。那几年,龙马村的茅厕干干净净,夏天没有蛆虫,冬天,下脚的地方没有冻住的冰块,就连掏出的粪便都被晾晒好,积攒在一个背风的地方留作粪肥。人们对这个整天沉默不语的老右派甚至有了好感。
直到江小凡上大学那年,有一天一对坐着轿车的老夫妇来学校看她,在他们的再三解释下,江小凡才模模糊糊记起了一张面孔。老先生就是当年给龙马村掏了三年茅厕的“老尹”,这时已经是省盐业厅的书记。江小凡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半天问出一句:“您为什么要来看我?您不恨我父亲吗?他当年让您……”老尹握住了小凡的手:“当年如果不是你父亲给我安排了那样一件差事,我可能早就倒在批判台上了!我有心脏病,有一次开完批判会跌倒在回来的路上,疼得抖成一团。是你父亲发现了我,把我背回了老屋。他偷偷地去赤脚医生那里给我拿了很多药。他跟我说:只要你不嫌脏,我给你安排个活,保证你能健康地活着……你父亲,是个真正有胸襟的人啊,他分得清是非!他是冒着风险照顾了我呀……”小凡的眼睛一亮。是啊,父亲是个有胸襟的人,当年那个年轻的江队长为小村办了多少大事!他心里装下了多少东西……
那一年的春天,江一洲从县里领来了一群穿工装的男人,他们手上拿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工具,一来就忙个不停。有的挖坑,有的竖杆子,有的架线。社员们也干得欢喜,他们脖子上的手巾擦黑了,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身上。陈月秀一手牵着小凡,一手抱着小强,挤在看热闹的人群前面,骄傲地看着江一洲指挥劳动。木杆子上的黑线架完了,小凡望着几只燕子轻盈地落在黑线上面,可是那些穿工装的叔叔们顾不上听小燕子唱歌,他们挨家挨户地挂上一只只亮泡泡,像小瓜一样。江一洲纠正小凡的叫法,告诉她那叫电灯。他说只要一通电,那小灯泡就大放光明,让黑夜变得跟白天一样。江一洲是大队长,他的话让全村的人欢呼雀跃。那天的工程一直干到天黑,江一洲一声令下,电工合了闸,顿时,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光明之中。男人们互相擂着胸膛,提来整瓶的老酒对饮,女人们则把针线活拿到灯下,看着那细密匀称的针脚,看着绣花绷子上仿佛活了的金鱼、鸳鸯,合不拢嘴巴。小孩子们在饭桌前追追打打,他们能看清彼此脸上最细小的茸毛。那天,江小凡听见全村人都在唱歌,人们围坐在电灯底下彻夜不眠,连鸡鸭鹅们都扑腾着翅膀,飞到灯火通明的窗台上,咕咕嘎嘎地叫个不停。
后来江一洲不断地给小村领回一些稀奇古怪而又神奇非凡的人,他们给小村打好了深机井,建好了磨房,装好了一台台隆隆的机器,而陈月秀就蹲在灶前,挽起袖管,给那些人烙出一张又一张喷香的大饼,炒菜的香味漫散了整个村子。小凡偶尔听人说:“咱队长真傻,给村里办事不派公饭,天天磨自己家柜仓里那点粮食,看把个女人累的,锅都没个刷干净的时候!”可小凡没听过妈妈喊累,她整天不停脚,脸上却总是挂着笑,她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一洲才累哩,他心里装着整个村子……” 无人处落下泪雨 第一章(7) 冬春之交的时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江一洲把村里以江守业为首的老盐工们聚到一起,跟上他们,去了海边老滩。那一天,出现在江一洲眼前的,是苍黄一片的混混沌沌的荒滩和混混沌沌的海水,早年在海沿河口设置的简易扬水站早已不复存在:三间低矮的土坯泥屋变成了一堆黄土瘫在那里,四周是一片破碎的贝壳瓦砾,两架用来风力纳潮、扬水的帆布风车早变成了一堆碎木烂铁,帆布成了尘土,在一刻不停的海风吹动下灰飞烟灭……江一洲看见老父亲蹲在那一堆碎朽的木头中间,费力地翻找着什么,终于,头发花白的老埝头抖 抖索索地拣出两颗生锈的钉子,在手里掂了又掂,攥住了……江一洲想起小时候自己随着父亲住在那三间土坯房里纳潮制卤,一住就是一个春夏,他的眼睛被泪水浸湿了……
海边的风又冷又硬,半个多月跑下来,江一洲脸上冻得起了皮,整个人黑瘦得不行。他在每天四五点钟就爬起来,敲响村边上工的大钟,挥动着一双大手给男女社员分派任务。闲置了多年的盐田被社员们翻好了、晾晒了,拉着碌碡碾轧一新了,盐池里的地面光滑平整得照得见人影,听得见汗珠溅在上面的声音;旁边的排水沟里几尺深的黑色淤泥也被清除干净,走盐车的池棱全部整整齐齐铺上了青砖。海水解冻不久,靠海新建起的电力扬水站上机声震天,盐度极高的渤海海水一路翻滚着浪花,顺着清理好的排水沟流进了一个个贮水汪子。等海水蒸发浓缩到一定程度输入盐滩之后,有经验的盐场老埝头们便用木锨扬起沉淀好的卤水,细细观察卤花的颜色、起落的时间,由此测定出盐度,再把符合要求的上好卤水依次灌进田字形的结晶盐池,只等卤水进一步蒸发,盐池里便结出一层层雪白的盐粒。那些阳光强烈和无雨风高的日子人们穿上黑色的大胶鞋,扛着木制的盐耙子,推着独轮盐车,今天勾混,明天扒盐,今天吊盐、堆坨,明天准备苇箔苫码,不歇脚地一路忙下来。
看着在阳光下越堆越高、泛着白光的盐码,老盐工们眼里含了泪花。金明老汉说:“这才是咱的龙马村哩!没有这雪白的盐码,死了都闭不上眼!”
江守业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眼睛笑成了两道弯儿:“当年你老哥是咋说的?有俺家一洲在,不会看着这盐田没人管!这小子参军前就有志气,前前后后没少给咱村出力,要不是任家那丫头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参军,说不准,他早在村里干出点名堂来啦!不过,话说回来,在部队那几年没白干,这脑筋里的玩意儿就是不一样,你老哥都想不到啊,这叫啥?啊,快板里唱的:‘渤海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两个老汉“嘎嘎”的笑声惊起了一群正在水面上觅食的鱼鹰,扑棱棱地张开翅膀飞向远处。
更让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不久之后,龙马村年轻的队长又不知从哪里为队上买来一只机帆船,小凡坐在爸爸的肩膀上还够不到大船的船舷呢!大船开锚启航的那一天,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到几里外的河口,去为村里的新水手们送行。燃放鞭炮的红纸屑铺满了河口的航道。老掉牙的船老大金旺眼热得眼睛发蓝,沿着河沿儿追出去老远,还扯着铜管般的嗓门跟站在船头的队长搭话:“你可真敢干哩,队长!这一只大家伙就能养活咱一村的人!俺想年轻上二十岁,跟上你闯啊……”
那一年江一洲还带领着全村人再一次开荒造田。谁也记不清这已是第几次开荒了。早几年“以粮为纲”的大牌子还锈迹斑斑地立在田头,而那些社员们辛辛苦苦开出来的田地,却因为海边特有的盐碱和风沙长不出一块像样的庄稼。远远望去,东一块西一块稀稀拉拉的苗苗像是八十岁老婆婆的头发。江一洲带上队里所有的青壮劳力,赶上牛车马车、开上拖拉机去了几十里以外的农村,挖来一车车上好的红土,一层又一层铺在开出的田里。村里的老先生说:这换土造田,简直像古时候的“愚公移山”!社员们都说:这“愚公”队长江一洲在来回奔波的路上足足掉了二十斤肉哩。那一年的秋天,家家户户的锅里除了煮过毛蚶、海蟹,还常常飘出煮花生的香味、烀红薯的香味、炒芝麻的香味……小凡在大片绿得滴水的庄稼地里跑丢了两双鞋子……
3
恋爱的日子里,苏致远常常定定地望住小凡的眼睛,叹息般地对她耳语:“小凡,你的眼睛真美,只要它不起雾,它就像月亮照在我黑暗的心上。”
小凡的心咚咚地跳。她垂下眼睛:“看你,甜言蜜语的,又不是让你写诗。”
“难道你不喜欢诗吗?小凡,爱情本身就是诗,一个男人爱这个女孩有多深,他就会给她多好的赞美!据说,这是衡量爱情的尺度。”说着,苏致远伸出长长的胳膊把小凡拥进怀里,一下一下地吻她。他低语着:“这是一个爱人最好的赞美!小凡,好小凡,谢谢你,你让我感觉到活着有多好!” 无人处落下泪雨 第一章(8) 小凡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她像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一样,一心一意享受着阳光,暂时忘记了郁结在心中的阴影。
那时候,在江小凡的老家,凡是见了小凡的模样又熟悉小凡奶奶的老人们,无不当面夸奖她:“真好看呀,江家的女娃娃!活脱脱像死了你奶奶,叫人看了不想眨眼!” “啧啧,可比你奶奶有福!有吃有穿有人疼,还上了恁高的学堂,有出息哩!日后,定能寻个好女婿。你奶奶哟,可是提不得!”
“是哩,是哩,老姐姐,咱们年轻那时候苦啊,没赶上好光景。那个傻妹妹哟,更是提不得……”
老奶奶们往往说到这,就一下子打住了,眼里噙了泪花儿,提了屋外的小马扎儿消失在自家的门洞里。江小凡就会在闪烁不定的阳光里,愣上半天……
十七岁的江小凡对奶奶的经历越来越好奇,她千方百计地向那些掉了牙的老人们打听有关奶奶的一切,在她的头脑里,奶奶的形象模糊而神秘……
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同样是十七岁的明霞出落得像一朵迎风开放的野菊花。尽管穷得没吃过一顿细米白面,没穿过一件不打补丁的衣裳,没娘的孩子又整日整日地在地里割草砍柴,她的美还是让人惊讶:明霞的皮肤白得少见,像胡家豆腐坊刚刚出锅的豆乳;一双漆黑漆黑的大眼睛总像汪着一湖深水;两条粗黑的辫子梳得齐齐整整,一走一颠拍打着腰背;而那腰身修长窈窕得像棵小白杨树。她怕见人,不敢大声说话,见了人总是羞怯地一低头,走路连个声儿都没有。村里的老人都说:这要放在早先,明霞一准就给选进宫里做皇妃了,那可是一辈子穿金戴银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可这女娃生在刘满仓家,又赶上这战乱灾荒的年月,怕就没有好命喽!甚至有“法眼”的人当面去找满仓老汉,指天发誓地说:明霞是个“花姐”。这种“花姐”、“童子”的说法在那一带平原小村流传很广。“花姐”是指那些年轻漂亮却命运不济的女孩子,她们前生是伺候王母娘娘的仙女,犯了天条被罚到人间来转世受苦。这样的女孩都是不能嫁人的,一旦提及婚嫁就要死——因为王母还要再收她们回去做侍女,破了身是不行的,而且王母娘娘也不允许她们享受人间的欢乐,原本就是要处罚嘛。有“法眼”的人如此这般地对老汉解说一番,并说唯一保全孩子的办法,就是供了香火纸钱,请来“大仙”烧了写有女娃名字的符咒,再念经作法把一个画着女娃像的纸人一并焚烧,算是换了女娃的“真身”。这样女娃才能活得长久,能像别的女人一样婚嫁生育。
满仓老汉虽然清楚地知道他这从小没娘的孩子是如何的苦楚,却也是半信半疑:他听过关于“花姐”的说法,也看到过那些早亡的女娃,可真有这样的事让他遇上?更因为家徒四壁,实在是做不起法事。偏偏有神婆张吴氏几次三番来劝,又破天荒要借钱给老汉办事,说好明霞找下婆家过了彩礼再还她。
明霞当然不知道人们背后在做什么,她依旧天天挽了裤管儿,挥动着手里的镰刀,把小山一样的青草背回家。十七岁的姑娘,开始有心事了。她在忙累了一天之后,常常睁着眼睛直到深夜。等炕头上响起老爹响雷似的鼾声,她就悄悄坐起身,手托着两腮望着窗子发呆。那是一种很小的、有着密密的小格子的木窗,明霞常常在这狭小阴暗的土炕上,透过这扇年代古远的小窗向外张望。有月亮的晚上,月光会艰难地挤进这些木头格子,支离破碎地洒到土炕上,照着明霞破烂得要开花的枕头和老爹浓重枯瘦的侧影。
姑娘想的很多,思绪飘忽不定。有时候想到了不能让爹知道的女孩儿家的秘密,她就止不住脸红。哎,有娘该多好啊,娘会知道她的秘密会教她怎么做。可是,她连娘的面儿都没见过娘就扔下她和爹走啦。爹说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享福去了。爹说:苦命的女人苦命的娃儿,穷人没有一天是人过的日子,活着苦哇!只有到了那个世界的人,才不用担心没有收成,不用担心战乱兵匪,不用担心饿了病了!明霞想不出另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她怀疑真的有那么一个地方。她问老爹:“那个地方如果真有爹说的那样好,人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受苦呢?”老爹就告诉她:人来这个世上就是受苦的,前生的债就是这辈子来还,苦没有受完,是不能走的,人的一切,上天都安排好了,你想不这样也没用。老爹说:“人活着就得认命!咱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老爹的话让十七岁的姑娘更加酸楚。明霞有时候会想到几个一起割草的小姐妹。可是她们都嫁人了,很少回来,回来也都是哭,难得说上一两句话。肯定是婆家不好,又不敢说。那些男人,她们出嫁前见也没见过,谁知道是猫是狗。她们有的甚至怀了娃娃,枯黄得像根草棍儿。才十七八岁的女娃呀!明霞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像她们那样。婶子大娘就对她说:女人生在这个世上就是牛马、就是草棍儿,就得任人家使唤任人家用,这是命哩,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怕也没用!明霞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别人也不知道。她们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她们对明霞这样想感到吃惊。 无人处落下泪雨 第一章(9) 明霞便不再问。她依然害怕那种叫“命”的东西,她不知道明天“命”会对她怎样。那段时间她还会想起那个给她画过像的年轻人。小伙子长得干干净净,画她的时候一眼一眼看得很认真,不画她的时候,也总是把目光偷偷地瞄过来,那眼光让她心里敲着“咚咚”的小鼓,又情不自禁地想让他多看一看。他的手可真巧啊,把人画得那么像那么好看,仿佛吹口气就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