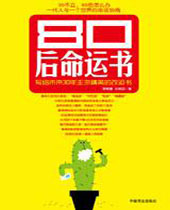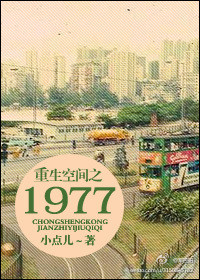5580-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份情意更是难以割舍。乡亲们一直把父亲送到山下,年轻的父亲不敢回头,他怕看到乡亲们惜别的目光。等到了县城他才回头望了一眼蒙山,心里叹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回建山公社了。 然而,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的一天,周伯背着一罐自己做的泡菜和豆瓣从名山步行了一天一夜到荥¾;来寻找父亲。父亲喜出望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从父亲与名山老乡间的情谊能够体会到当年红军与民众之间的故事。荥¾;农民收留红军伤员,就像今天影视作品里见到过的情景,在荥¾;真实地存在,为红军伤员早日康复,乡亲们为战士熬鸡汤,荥¾;砂锅起了不小作用。 在荥¾;严道的村里至今还流传着老乡收留红军的故事:女红军因连续行军作战,病倒了,只得离开部队,女红军便成为当地农民的“女儿”。主人上山采药用砂锅熬制偏方,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治疗调养,女红军终于治愈了。由于大部队已开拔,就留在当地开展工作,盼望着有朝一日重返前线。据统计:红军一、二、四方面军¾;过的长征路上有近万名红军伤病员留住民间。 荥¾;砂锅远近闻名。眼前这条还算宽敞的街面是六合(鹤)乡二组,它是荥¾;砂锅的正宗“作坊”。因为微雨刚过,地上没有灰尘扬起。大路两旁的房屋是二楼一底带卷帘门的那种固定格式,就连店招都全部采用花哨的喷绘美术字体,但各家门前摆着的砂锅式样却各不相同。路边那家挂着“宪锦砂器厂”招牌的房屋还没有完全竣工,它是当地农民曾宪锦的房子。他家的作坊在店后,标准的前店后坊。50多岁的曾宪锦搞砂器加工已有20多年,1985年前主要生产蜂窝煤炉子,之后便开始生产不同规格的砂锅和药罐,样式虽不够精美,却耐用,每年有1万多元的收入。他挣的钱除了使家里的日子过得顺畅外,还要供养孩子上学,如今大女儿已从雅安农校毕业找到了一份工作。曾宪锦带我们参观了街道后面“严道古城”文物遗址,在这四周是密密的砂器窑子,各种成品和半成品砂器堆积如山,准备运往各地销售。 一队的张定康老人今年60岁,他干这一行已有30多年。过去砂器作坊是集体的,改革开放后,各家各户有了自己的作坊。随着竞争的激烈,各家工艺技术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搞高烧的工艺技术,从选土、碎土、造型到最后的烧制等制作环节越来越讲究。张定康老人通过多年的实践,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烧制风格,开发了属于自己创作的产品,其中砂器花瓶最为出名,造型的式样不同于一般的花瓶,它带有唐代花瓶的风格,但它表面沾附的“二龙戏珠”又有汉代的遗韵。老人说这种全手工的花瓶工艺复杂,单说贴龙形的活,一天时间也只能制一件。他家房子里专门摆放了一张玻璃柜子,陈列着几件老人的精品之作。老伴拿出钥匙,十分谨慎地取出一件,小心拂去表面的灰尘,嘴里说有人曾出价2000元,老汉也舍不得卖掉。
《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 雄关漫道没有遗忘的城门关隘(图)
走过烟雨灵关 “过了桥就是宝兴了”,站在芦山县与宝兴交界的石板桥头听老乡这么说。这座桥是石桥,它在灵关,灵关是个很古老的名字。从芦山向宝兴而去,一路都在峡谷里穿行,而到了灵关峡谷就没了,河面一下子便开阔起来。如今的灵关与中国广大农村的小集镇一样,一条笔直的路穿过城镇,两旁两层楼的卷帘门铺面是统一的面孔和同样的商品。但是细看起来发现,由于灵关在历史上作为茶马古道上重要驿站的地位,至今还有一些古典的建筑遗迹,尽管这些遗迹已不被许多人重视,但是,文化研究者们看重灵关最后的遗存,它们才是灵关的灵气所在。 从灵关前往芦山之间的道路很Õ;,河道两旁是陡峭的悬崖。在古时灵关小道上许多路段完全是栈道,路是架于岩壁上的栈木,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险要,灵关一带的栈道、土路与石桥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峡谷中的这条河很奇特,因为地貌、水气的Ô;因,几乎每天下午5点钟左右水面会泛起一层薄雾。 1935年6月8日晚,薄雾罩住了河谷。抢渡大渡河的红军悄然占领灵关场。就在当天,杨É;部在雅安接到刘湘传来的蒋介石令,命他率部追击红一方面军,追击目的地为达维和懋功。 杨É;接令后,认为与红军距离不太远,完全可以完成追击的任务。杨É;遂以夏炯为纵队指挥,由飞仙关¾;芦山向宝兴发起追击;其他旅团和司令部在追击纵队后,以梯次前进。杨É;共率8个旅,25个团,近4万人向宝兴追击。 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严密监视天全、芦山方向的敌情,以掩护主力部队顺利·过夹金山。红九军团受命后,在灵关朱砂溪占领阵地,堵住川军追击。杨É;追击纵队于6月12日向灵关朱砂溪红军阵地发起进攻,战斗非常激烈。红军居高临下,扼守阵地;川军仰攻,又受地形限制,兵力展不开,一再被击退,伤亡惨重,战斗进入僵持状态。杨É;命令太平场周世英速派李树华走捷径·越龙岗山,迂回红军侧背,偷袭红军,配合灵关正面攻击。李树华接受任务后,于13日晨轻装出发,午后4时许前卫队爬上了龙岗山梁,饭后下山袭击宝兴,利用机枪、迫击炮轰击红军阵地并夺得两个山头。红军退居第二防线阻击进攻敌军,战斗至黄昏,双方停止交火。深夜,红军在朱砂溪、灵关已完成堵击任务,便撤出阵地向硗碛方向引退,宝兴城二线山头与敌军对峙的红军亦于14日黎明前撤走。 6月18日,杨É;的追击纵队被红军阻挡于夹金山以南,第一混成旅停住于硗碛,第六混成旅停住于宝兴,第二混成旅和司令部从宝兴西河尾追红一军团一师,也被迫停住于陇东、永兴一带。灵关之战是中央红军运动作战中形势估计较为充分的¾;典之战。红一方面军于6月12~18日,胜利·越夹金山。
《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 雄关漫道山道边的石刻标语(图)(1)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从来不谈自己年轻时代的事情,他们下放时代的青春模样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完成。所以有机会踩着他们当年的脚印,走在那条山道时,心中有份难以言表的感觉。 因为红军曾¾;从这条山道走过,它便成了英雄的路了。听说我要寻找红军的踪迹,父亲的老朋友周伯专程到名山县城接我。 上山的小路很Õ;像田坎,修了机耕道后小山路的入口只有当地人才认得,而且步行才能见到山腰的红军标语。我只有弃车步行,跟着周伯沿着那条小道向大山走去,他说当年我父亲就是从这条山路走上山去的。我知道那是1958年的一个下雨天,他与母亲当年2月才结婚,而3月份便被下放到了名山。当年崎岖湿滑的山路让他摔了好几个跤子。 背着沉重的相机设备走上山坡小路却丝毫没有受累的感觉,因为每走一段山路眼前的景致总是出奇的美。也许是心情的缘故,大山的坡度成了一种动人的柔缓。Õ;Õ;的山路引着我走过迂回曲折的山林,走向山里清µ;而缓慢的日子。 周伯已是60岁的老人,步伐却很轻盈,没走多远我已赶不上他的速度了,那一刻我想到了当年的父亲,走过这条山道时他的心里一定会有万千感慨。下放干部对未来的前程肯定充满了迷茫,而那个年代是火热的,他必须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切美好的期待只能悄悄隐藏在这条弯弯的红军小道,不能对前途的艰险有半点绝望。 果然,一年后父亲从山腰的村子里抽调到邻近的另一个叫荥¾;的县城,继续从事他财会工作的老本行。但奇怪的是,只生活了短短一年的小山村,却在父亲的生命里烙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几十年光阴过后仍旧不能割舍。1958年父亲第一次上山时,老乡们没有告诉他这条路是红军走过的路。也记不清多长时间汽车颠簸到达了名山县,所有的下放干部被集中起来再分配时,一个叫建山公社的陌生名字与父亲连在了一起。各个公社接人的干部们领着“自己的人”连夜踏上了归途。 下放干部们开始了全新的工作,他们白天到田里干农活晚上还要组织社员学习。父亲对劳动的苦没啥,就是离我母亲太远,两人只能用书信来讲述各自的情况。在父亲下放名山的两个月后,母亲也接到了下放的通知,她去的地方是当年灌县的虹口公社。从此天各一方的生活便在两人之间开始了。 弯弯的山道虽陡峭也算好走,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节了,人们正忙着采摘茶叶,这座山与蒙顶山同属一脉。种山茶本应是蒙山的特点,但在“农业学大寨”的年月里开荒山建农田¾;营粮食收成是农村的主要模式,“以粮为纲”的观念从父亲下放的年月一直持续下来。好在蒙山天生就是适宜茶树生长的地方,房前屋后的闲地里依然有老茶树在生长。 父亲第一次知道此山是红军当年作战的地方是在一次田间劳动中发现的。当年的他只有20多岁,生产队要按工时把他当强劳力对待,一对挑担发给他跟着大家上山去挑粪,但父亲却没有什么怨言。他当年的想法很朴素,毕竟自己是拿行政23级工资的农民,Ô;单位总会准时把工资汇到公社信用社。一天,挑累了担子的他在小道边歇气时,发现了路旁石块上异样的凹凸,他转过身用手拂去表面的尘土,几排刚劲的石刻文字呈现出来:“反蒋打刘湘¡;¡;”老乡说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攻克名山途¾;此地时留下的。这些红军石碑是在向荒山要粮田时重见天日的。父亲在山里劳动的一年里还发现了许多处红军刻下的文字。听老人们说,当年红军所到之处会派出专门的宣传人员,留下革命的火种。刻下的文字有的简洁,比如“革命”二字,有的文字很长,完全是一篇演讲词。雕刻的地方很随意,有牌坊、墓碑、山岩路边的石块,只要显眼就行。刻字前先由红军中的识字先生用笔写下文字内容,再请石匠用自己的工具凿上。名山宝兴一带Ô;本产石料,石匠们手艺精湛,石匠人数众多,所以名山的红军石刻标语特别多特别好。 走了1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父亲当年也曾见过的石刻标语,周伯上前用手拂去上面的泥尘,他说因为我要来拍摄红军遗迹,他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对沿途仅存的红军标语进行了清理,用刀砍掉了石块旁边的杂树野草,用锄头把掩埋入土的碑文石刻重新进行了整理。看他用手拂土的认真模样,不由想起当年田地里劳动的父亲,他面对这些悄无声息的红色石刻标语时想到了什么?我在此刻仿佛看到石刻标语边站满了红军战士,同时感叹红军这种宣传方式的独特创意。
《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 雄关漫道山道边的石刻标语(图)(2)
长征是播种机,撒落于山间小道的星火一定可以燎Ô;。 周伯的家在山腰,现在的详细地址是名山县建山乡,山村里仍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上他家弯弯扭扭的山道很Õ;,以至于倾斜的油菜花枝挡住了去路,周伯在前面一束束地扶起,我跟在他后面不急不慢地走着,尽管如此裤腿上还是被菜花抹上了一层黄色的花粉。山间待耕的田地浸泡着浅水,水影里有洁白的云彩倒映其间。转过一个坡地,见到浑身是泥的水牛被农人驱赶着,在小道边的水田里来回地跋涉着,空气中夹杂着菜花、梨花和新泥的芬芳。 登上山冈览尽众山景致,我想在这个菜花碎黄的季节里,空气中一定泛着当年的味道。当年父母过的日子太悠缓而相见的日子又太匆忙。就是眼前这片金黄的土地,这条山野小道母亲也曾走过,母亲走在这条山道时她是父亲的新娘。父母在那一年之中的境遇变迁里,既是始料不及却又充满无奈。好在组织还算对父亲母亲照顾,给了母亲3天假期,她登上了去名山的长途客车,然后沿着这条小道向父亲走去。而见面就意味着将要分别,母亲在花香的季节里见到了父亲一面,她是知足的,幸福的了。没有言说中的那种温情浪漫,就那么远远地赶来,然后匆匆离别,名山这弯弯的山道在母亲心中同样留下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记。 去之前父亲就告诉过我山里缺水,周伯还是给我端来了一大盆热水,一张崭新的毛巾浸泡在盆里。我知道这盆水对他家来讲也算“来之不易”,真是不忍使用,周伯却笑着说,没事的,山里人力气大,上山挑水快得很。我很感动,像当年的父亲一样感动。 可以想象当年父亲来到山村时,被分在周伯家搭伙吃饭,得到周家人的最细微的关照。 突然间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赶紧用毛巾擦抹双眼,不知为什么,却始终擦不干眼里的湿润¡;¡;重游父母生命过程中曾¾;¾;历过的重要地方,一下子仿佛体察到了当年父母的心境,尤其是父亲对待自己的苦心。在天高月µ;的夜空下,面对窗外的山影轮廓发呆。那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沧海桑田的感叹与千般柔美的追忆¡;¡; 周伯的两个儿子老三、老四比我稍小一些,多年前我家第一次搬新房前的装修曾从乡下请过两兄弟来帮忙,那个时候他两人还没有恋爱,在城里来帮忙之时也长了见识。老三会泥匠活,老四学的是木匠,后来他俩都结婚育子,之后忙着干活挣钱,我已¾;很久没见到他俩。 通向大山的土路是前年动的工,土路其实就是把从前很Õ;的机耕道弄得稍宽一些,修这条路所需的¾;费是由国家、集体出大头,各家各户按人头集资。若是哪家为了方便可额外花钱请推土机相助把土路修到自家的院房门前,只是增加的路段存在着土地的调整问题,因为自家门前的田地并不一定是自家的责任田,所以要拿出自家的土地换给占用的人家。这种换去换来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