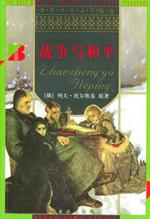战争杂碎-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羊城前段时间总是出现怪事。张司令刚到羊城那天,他放下行李,就骑着牛在羊城巡视,以示自己以天下为公时刻牢记人民的疾苦,但他还没走出多远,那头牛突然开口说话了:“整个天下将要出现战乱,我十分疲倦,你还要带着我向哪儿去?”张司令及其随从听见牛会说话,吓了一跳,大家都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我心里也非常恐慌,在遥远的二十世纪末,我曾在1998年第9期《读者文摘》第40页上见到一篇文章,上面说1988年时,苏联莫斯科有一只叫“唐斯科将军”的猫会说人话,能说100多个俄文单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愿望,比如它饿了,就会用俄语明确无误地说:“我想吃。”给了它一小块面包,它接了过来,会很有礼貌地说:“多谢。”吃过以后,它用爪子擦了擦嘴,像个绅士一样说:“我要出去走走。”有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果然没多久苏联帝国就土崩瓦解,庞大的帝国原来竟那么地虚弱不堪。这事张司令也听说过,所以他也很紧张,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忙低下头,对那头牛温柔地说:“你既然十分疲倦,我就让你回去,可你别再说人话吓唬我们了,求求你了!”张司令也顾不得再巡视羊城了,为了表达自己对这头牛的尊重,他立马掉头而去,牛也不骑了,主动地牵着缰绳,在前面给牛带路。但这头牛一点也不体谅他的良苦用心,一回到司令部,还没有卸下骑具,牛又抬头看着他,慢慢说道:“为啥回来这么早呢?”张司令听见牛仍然在说人话,心里很生气,牛说牛话,人说人话,井水不犯河水,放着好日子不过,却当妖精说人话,人又不会说牛话,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但张司令更多的是感到十分恐惧,最终恐惧战胜了生气,他立刻让我把精通占卜术的特异功能大师袁天罡找来。
袁天罡听了张司令讲的情况后,又去看了看那头牛,那头牛卧在草堆上,看到袁天罡,就像看到了多年没见过面的老朋友,眼睛里流出了一串混浊的泪水。袁天罡不由皱着眉头,仰天长叹:“这是天意啊,牛说将出现战乱,这是大凶的预兆,不仅仅是你张司令一家要遭受灾难,羊城即将出现战争,城内大多数人都逃不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啊。”张司令脸色苍白,尿都到鸡巴上,这才提着裤子到处到厕所,他急急地扭过头对我说:“南八,你快带领几名弟兄,穿上黄衣教的衣服,潜入黄衣教的领地,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
我现在是羊城守军的侦察队队长。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很不容易,大小也是个官,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好好地干下去,会有前途的。我很珍惜这个位置,立马按照张司令的指示,带着侦察队潜入了离我们最近的黄衣教左路军大本营陈家村。
张司令把我和袁天罡送走后,返回司令部,心惊肉跳,坐卧不安,茶饭不思,只好又跑去看那头牛。那头会说话的牛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地欺负人类,又学着人的模样,用后两条腿站着走路,还不好好走,走得歪歪扭扭的,还是外八字,出人类的洋相。虽然张司令果断地把这头牛关了起来,但这件事情还是很快在羊城传开了,老百姓们聚在司令部前,要求看看这头牛,并让张司令给个说法。
张司令很发愁,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他着急地对我的好朋友、征兵府郎将雷万春说:“这可怎么办?”
雷万春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没有经验,他也很发愁:“张司令,乡亲们要来看这头牛,我们黑衣教实行民主、自由,不能不让他们来看,也不能不给他们一个说法,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来看了以后,必定人心浮动,谣言四起,造成社会不稳啊。”
张司令长叹一声,忧心忡忡地说:“这个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我们是讲民主的,群众有知情权,我们又不能不让他们看,这就是民主的两难处境,民主是把双刃剑,几万年来,老祖宗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能在一夜之间就能解决吗?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雷万春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事说难也不难,我们先把那头牛杀掉,然后再牵出来一头别的牛,告诉乡亲们,牛会说话,纯属造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者就干脆说是黄衣教在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这就是给乡亲们的说法。然后我们就贴出布告,以后如果再听到谁传播类似谣言,一律枪毙!我们这样做,既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又维护了民主的严肃性,充分体现了我们黑衣教人民的智慧。”
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张司令也只好这么办了。张司令让人把牛牵到后花园,叫来了厨师疱丁,让他把这头唯恐天下不乱的牛杀掉。疱丁提着刀子过来了,牛又说话了:“你们现在杀我也好,反正早晚都免不了一死,早死早托生,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头好牛。只是苦了你们,唉,当个人还真他妈的不容易!”张司令再也受不了了,他用棉花塞进了耳朵里,又用双手捂着耳朵,厉声喝道:“杀掉,立即杀掉!”
疱丁提刀过来,动刀甚微,霍然已解,如土委地。疱丁提刀而立,为之踌躇满志。
张司令有点头晕,他捂着头,摇摇欲坠,卫兵们忙上前扶住了他,张司令无力地说:“扶我回屋吧。”
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没过几天,羊城又有小道消息传了出来,说是黄衣教就要全面发动战争了,天下即将大乱,羊城即将灭亡。消息是从一个道人那里传出来的,这个道人叫吴守澄,号孤去,他每年在城乡市镇像孤魂野鬼一样游来转去,饿了便讨点剩酒痛饮,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吃饭。方东五十三年元旦这天,孤去又喝人家的剩酒喝醉了,躺在羊城的大街上,斜眼看着来去匆匆的路人,不停地说 “他来了”、“我去了”。他从早上说到晚上,翻来覆去就是这两句话,但没有一个人理他,大家都知道他是孤魂野鬼。终于有一个二流子闲着没事,就捏着鼻子,趴在他耳朵边问他:“他来了,是什么人要来?他是谁?来干什么?”孤去躺在地上用胳膊支起脑袋,潇洒地斜了他一眼说:“天机不可泄露,我要走时再告诉你。”二流子往这里一停,人们都过来看热闹来了,有人就又问他:“你去了,要去什么地方?”肮脏的孤去仰望满天星斗,像抒情一样地说:“我准备去冥河星系逃性命。”
这几句断断续续的对话很快在羊城被人们传开了,经过人们口口相传,不断地损失,又不断地得到了增补,最后全城的人们都在议论着黄衣教军过几天就要过来攻打羊城了,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手里还有早已失传多年的BLU…82炸弹,一炸就是几公里。
张司令听说了这件事后,十分震怒,顾不得头疼,也不体谅民主的两难处境了,连发十二道金牌,让雷万春速去捕捉造谣惑众的孤去道人。雷万春带着士兵赶到羊城大街时,孤去道人依旧躺在那里自言自语。雷万春一把抓住孤去,想把他从地上拖起来,然后五花大绑地捆回去。但他的手抓过去时,觉得手里轻飘飘的,他再一看,手里只是一件破旧的道士穿的长袍,孤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雷万春把这件肮脏的长袍扔在地上,长袍居然化成了一堆灰烬,犹如一张白纸,上面画着许多穿着黄色衣服的人,手拿弓箭,打着杏黄旗,骑着膘悍的战马,飞驰而来,长袍的两只袖子成了两个大字:“保重”。
雷万春让人把这幅画画了下来,飞快地跑回羊城守备司令部,把这幅画呈给了张司令。张司令从床上支起身子,咳了几声,看完了这幅画,张司令叹了口气:“战争看来真要来了,我估计得没错啊,但我们兵力微薄,必须还得再征兵。雷将军,你再贴出一张告示,就说我已经派人去侦察黄衣教军的情况,不久就可以知道黄衣教军的虚实了。还要告诉他们,羊城已经加固了防御工事,黄衣教就是有十万人马,也休想攻破羊城,并且我们已经派人向驴城的方东教主求援,不久之后就将有援兵到达。城内居民不必惊慌,舞照跳,马照跑。黄衣教是专制、独裁、愚民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我们是正义之师,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并必将再次证明的!”
雷万春领命而去,布告贴出来之后,羊城安静了许多。
两个月后,我带着几名弟兄从黄衣教的领地赶回来,报告给了张司令一个惊人的消息:黄衣教已经扩黄了几十万人马,其中左路军总司令马臭蛋已带领十多万人马到达陈家村,时刻准备来攻打黑衣教了。
张司令像早已经料到了,他冲着我挥了挥手:“知道啦,回去吧,回去吧。”
我回到了自己的兵营,无力地靠在墙上。我带着弟兄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走了一个多月才进入陈家村,目睹了陈家村的“扩黄”和准备迎接东方教主的视察,陈家村已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他们磨刀霍霍,杀气腾腾,随时都有可能浩浩荡荡地向黑衣教领地杀来了。好在黄衣教和黑衣教之间有数千里无人区,黄衣教大军要赶到羊城,尚需一段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做好迎敌的准备。
我无力地靠在羊城的城墙边,心里像绑了一块铅一样沉沉的。春天已经来了,但今年这个春天也他妈的反常得出奇,三月还没过完,雨就像个爱唠叨的女人一样下个没完没了,又像老爷林大申的外甥安公子写的那些很忧愁的古典诗歌一样,让人心里闷闷的。在潮湿的空气中,羊城的粮食开始发霉,麦子和高粱上长出了白色的绒毛,每个人的衣服上也都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就连御史中丞张巡大人的爱妾崔莺莺华丽的绸子衣服上也带有这种令人扫兴的味道,这和时常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艳格格不入。女孩子对自己身上的气味都很在意,她因此常常把自己关在香闺之中,长久地用香草熏着衣服,她把这当作了刺绣一样作为日常功课乐此不疲,我们常常看见一缕缕轻烟从她的楼阁中飘出,淡雅的香气能笼罩着我们长久不散,非常性感,让我们的心情和这雨天一样既兴奋又惆怅。我们的兵器也生出了一层锈斑,我们便常常在这熏衣的香气中磨着兵器或者拄着大刀倚着墙角睡觉。我不睡觉,我靠在羊城城墙边,我只思念小姐。我是小姐的爱情走狗。
我在思念中被一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惊醒,我忙跳了起来,这才发现雨已经停了,阳光灿烂刺疼了我们的眼睛。阳光照在地上的水洼上,水洼反着光,一闪一闪的。我揉了揉眼睛,再看看纯净的天空,我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骇得目瞪口呆。天空中万里无云,南北却各有一条彩虹悬在半空,它们色彩缤纷美丽异常犹如冷酷仙境。我张大嘴巴呆呆地看着它们,它们的绚丽和灿烂重重地压迫着我,我感到浑身冰冷。我像看着情人一样专心致志地忧郁地看着这两条彩虹,旁边喂马的少年韩愈看了半天,却并不觉得这两条彩虹有什么奇怪的,他不解地问我:“大哥,你在看什么呢?”
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说明一下,韩愈的确就是“唐宋八大家”的那个韩愈,但他现在只是黑衣教军的马夫而已,他是跟我一起从林家庄来当兵的。他本来想毛遂自荐在林家庄园里找个报社编辑或家庭教师的工作干干的。老爷林大申问他有什么作品,他从一个黑皮箱里拿出了一叠厚厚的稿子。老爷随便拿出了一篇,就是那篇著名的《马说》,韩愈虽然当时只是个少年,但文章写得十分老辣,全文如下: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老爷看完,拍着桌子叫道:“好文章啊,好文章啊!”然后对韩愈说:“先生对马这么有研究,我就充分发挥先生的才能,就在我们家当弼马温,给我们养马吧,给我们林家多培养出些千里马,到时重重有赏。”韩愈刚开始时还有点不愿意,他红着脸说:“老爷,我可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起码能当个大学教授!”老爷就笑着说:“先生你有所不知,现在时代不同啦,吃香的是后现代主义,先生知道什么是‘解构’,什么是‘反讽’吗?”韩愈茫然地摇了摇头。老爷说:“这不就得了,还是当弼马温吧,弼马温这个职业有前途,想当年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从弼马温干起,一直干到了‘无敌战佛’,相当于一品官。这里正好可以发挥你的专长,先生就从这里干起吧,只要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韩愈不服气,又偷偷地拿着作品剪贴本到处找工作,由于经济不景气,工作很难找,他转了一圈,只好又乖乖地回到了林家庄园里当了弼马温。
韩愈问我看什么,我喃喃地说:“虹、虹。”他笑了笑说:“挺美的,你看崔莺莺夫人多高兴啊。”我扭过头,崔莺莺在中丞大人张司令的身边又蹦又跳地向这两条彩虹指指点点,拍着小手喊着让大家看。她也看见我了,她说:“南八,你看你看!”我灰白着脸,按着宝剑,向她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她像鲜花一样风华正茂,我不愿意让她看到了我的不安和恐惧。
我很尊敬崔莺莺,她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的女子。她刚和张司令认识时,张司令还只是一个穷酸书生,连骨头带肉也卖不了俩钱。那还是在遥远的二十一世纪初,张巡那时叫张生,不叫张司令。他们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崔莺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