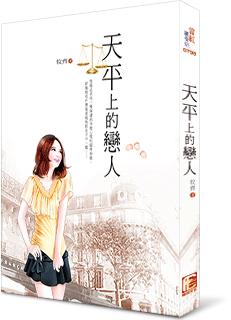味蕾上的南方-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飞去,响起如初夏远处的细雷。早晨清亮的阳光结束了一天初始的照耀,从六点到九点这一段时间。
《味蕾上的南方》 清凉之波清亮的阳光(图)(2)
看早晨的阳光,静静地坐在窗前,展开书,泡一杯清新绿茶。我新近买了两包绿茶,一包从西湖龙井村金小辫儿手上买的狮峰龙井,一包从八里桥茶市小彭手上买的信阳毛尖,我喜欢稍浓郁一点的绿茶,雨前茶。可以举起玻璃杯子,透过青嫩碧绿的茶汤看早晨,它会制造一种叠加的清新效果。已经很久不读诗了,漫长时间里的劳顿奔波,朝霞般的浪漫渐已褪去,惟想呵护一片朴实的清新。然依稀记得泰戈尔《吉檀加利》中一个诗句:永新的爱情。我则联想:永新的早晨,永新的晨光,永新的生活和永新的太阳。品着新鲜的绿茶,看早晨清亮的阳光,时间像一枚新绿的茶叶,它托着我看不见的露滴,那宝石般的晶莹,我只能以灵魂去感应,那嫩绿的光芒,永承爱意。 洗净了一夜的梦,心灵沐浴早晨清亮的阳光。我站起身,推开窗页,北国清晨的凉意悄然扑入,时光如水,渐渐注满心空,我忽然感觉到,我获得了一个清亮。像这样柔凉、稚嫩、新鲜、清亮的早晨,是阳光从容不迫地带来,它仿佛在诗歌与音乐之外,在遥远的本质和天真的地方带来。阳光来了,我在很久的时间仍会这样想。
《味蕾上的南方》 木鱼镇的腊蹄子段(图)
少时在乡村,知道做木器的叫木匠,织篾器的叫篾匠,打铁的叫铁匠,凿石磨的叫石匠,做房子的叫泥水匠,染衣服的叫染匠,缝衣服的叫裁缝匠,总之有手艺的人,才称得上匠,匠完全是一个褒义词,只到了更高雅的艺术圈,匠才含有一定的贬义,比如称一个作家为写字匠,他一辈子就无出头之日了。当然,匠还可以跃高一级,前头加一个巨字,比如科学巨匠,那又了不得了,千万不能在前面加小工二字,小工匠就全完了。乡村的匠人,且多半好吃,如铁匠喜欢炖汤,木匠喜欢爆炒,泥水匠喜欢焖红烧肉,好像还各有方便。 长大后,到了真正有小工的工厂里,却发现匠字都没有了,木匠改称了木工,泥水匠叫泥工,特别是那个铁匠,居然叫做锻工。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对锻工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叫铁工呢?既然木能木工,泥能泥工,铁就不能铁工而叫成锻工,锻工不是分明也在打铁么?我刚到地质队的时候,有一锻工学徒,不许我们叫他铁匠,好像铁匠是十分蔑视人的,我们就偏要叫他铁匠,弄得颇不愉快。 改了写作为生以后,研究字,发现锻真的就是打铁:锻,小冶也。——《说文》。按,熔铸金为冶,以金入火焠而椎之为小冶。原来锻工,是没有错的,铁匠的称呼,乃乡间民语,进入不了工业文明。锻,就是锻打,就是叮叮当当地举锤击打,打得火星四溅。以后,碰到了段,段也通锻,有“段脩”一词,读到段脩很纳闷,段脩是个什么东西呀?段脩是一个好东西,于常人来说,段脩是恐怕难以吃到了。段脩说的是古时候,人们在石板上面,搁了肉,再放上姜、桂皮等香料,用木棒敲打,打成肉饼,再晒干了,这就叫做段脩,段的本义就是在崖上的石头上敲打,甲骨文里面,殳是指兵器,手执兵器在石头上敲打就是段,这下明白了,那以前的兵器,也不过如此吧,是斧头或流星锤什么的。 不过,要讲段脩还是没有消失的,在温州保留有一种敲鱼,它可能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不过名为敲鱼罢了。敲鱼,就是将鲩鱼去骨,敲肉成饼。敲鱼的流程大致是这样,将新鲜鲩鱼去骨,再放淀粉,然后敲起来,一边敲一边放淀粉,敲呵敲呵敲!鱼肉与淀粉敲得越来越薄,饼越敲越大,再切了片。把鱼片和青菜心放入沸水锅中汆一下,捞起沥去水,倒入清汤炒锅中,放进鱼片、青菜心、精盐、料酒,用中火烧沸,撇去浮沫,再放入香菇丝、熟鸡脯丝、熟火腿丝、淋上熟鸡油,起锅盛入汤碗,名字叫三丝敲鱼,我到温州吃的敲鱼,是用黄鱼肉敲的,温州海里的黄鱼味道鲜美,选那鲜黄鱼,即鳞上泛起一层浅金黄色的黄鱼,初捞起来的黄鱼鳞上是银白的,过些时间,黄鱼就会由白泛黄,然后,又由黄泛白,再泛白的黄鱼就不好吃,早期白的黄鱼也不好吃,就要黄鱼泛黄那一段时间的做了好吃。敲鱼吃起来有韧性,而且鲜,这才能称之为传统美味佳肴。 除温州以外,福建有一种扁肉,也可称之为段肉。福建叫打为扁,就是用木棒将猪肉打成肉馅,包成馄饨,称之为扁肉,扁肉就是福建馄饨。扁肉的肉馅吃起来有脆,也是十分神奇。只有那个干的段脩,至今也没有吃到,是不是已经失传了呢?这不好说,以中国地面之大,人口之多,或在一些山里仍有制作段脩的传统也不好说,只有去真切地考察了,才能够判定有还是没有吧。段,跟美食有关,以前我也没有想到,且知道后,我忽然想做一个“段匠”,不为文时,去敲鱼为生也未尝不可么。
《味蕾上的南方》 木鱼镇的腊蹄子脍(图)
脍炙人口,指一种切细的烤肉,肉细易熟而嫩,可能是古人的哲学,现在的烤牛排,通常都切了小巴掌般的大,也不算薄,把牛肉用刀面拍一拍,搁在酒、黑胡椒、酱油、盐、糖、葱末等调料里腌1小时或30分钟,放到烤架上入烤箱里烤15分钟,再翻转烤10分钟,牛排就烤好了。也有裹嫩肉粉的,前天在通州台湖镇星湖园度假村吃的烤牛排,便裹了嫩肉粉,色泽紫酱,肉质香嫩,甜咸微辣。可是,现代人为何不承袭古人之脍炙人口的精细呢?大约可以推论,古代养牛,根本是自然放养,亚野生,肉质比较粗糙,今人养的食用肉牛,都一起生,一起长,一起屠宰,欧洲人的标准,食用肉牛的屠宰期是一岁半,牛肉的韧度与鲜嫩度,都由这个时间保证了。既然牛肉都很嫩,大块的嚼嫩肉,岂不更美乎?何必招惹细切的麻烦呢? 然而,就是老牛,今人也有不脍的,我国藏人养的牦牛,七岁时屠宰,这时牦牛肉质坚实,纤维粗壮,十分有嚼劲。我在甘肃的玛曲和青海的大通县都吃过牦牛肉,可以用野牛来称号它们,在纤尘不染的玛曲草原和青海湖畔长大的牦牛,可谓稀世珍品,惜之欧洲人因为一个口感问题,这么好的东西他们却不能欣赏。 谈得上脍的牛肉,庄园肥牛可以算,此肉切得薄如纸,光如绢,由于庄园肥牛用了一种饲料添加剂养,养得长瘦肉的地方长瘦肉,长肥肉的地方长肥肉,肥瘦相间的地方,呈大理石花纹,牛像按着设计图纸长的,养牛技术可说到了家了。然而,用添加剂养牛,终归令人有不爽之感觉。脍是脍了,在火锅里涮了吃,则也不是脍炙人口,《论语&;#8226;乡党》里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到了今时,似乎从物质生活升华到了精神层面,脍炙人口,就不再用来形容肉切得细,烤得香嫩的肉了,文学评论家拿它来形容好的诗歌,说《枫桥夜泊》脍炙人口,就是有很多人吟唱它,这么说,要把诗歌切细了来吟诵? 当然,即使在古时候,脍也是有其高雅之地位,据说有火食以来,汉族人也保留吃各种兽、禽、鱼、甲壳和贝类的生肉,现作现吃的这些肉类,叫做脍生。太凡帝王将相,贵族富豪的佳肴,宴饮中的珍馔,必有脍生。寻常百姓,可能少了耐心,大块肉大碗酒何曾不爽啊?脍生须选极新鲜的肉、鱼制作,切得薄的为轩,切的细的为脍,脍仍是肉丝,切脍时要用纸吸去残血。吃脍生须用芥末、醋等凉拌,尤讲究型和色。《礼记&;#8226;内则》:“脍,春用葱,秋用芥,春用韭,秋用蓼。”蓼如今未见再作调料了,在赣南,红蓼生于水边,称辣蓼,儿时将其采集,捣碎,到河滩的小水潭里闹鱼,不知可以佐食。然而,喜欢吃鲈鱼脍的,世间只有一人,那便是张瀚的莼鲈之思,典出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意,何羁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为了鲈鱼脍,便可以把官扔了不做,真是可敬可佩之至!现在,吃脍生的地方仍分布江浙一带,但是,偶尔在京城里也可以吃到,比如三纹鱼、龙虾等切的生片,应是继承了古代传统,只是搁了冰上面。我在温州吃过一回江蟹生,这与脍不怎么搭界,只是味道鲜极了。 脍不同于刽,刽是切断和砍断的意思,脍是把肉切细。上世纪末,我去神农架的房县,脍过一回。我上厨房点菜,看见一只大筲箕装着一堆纯净而偏红的瘦肉,我以为是牛肉,我说给我爆一个牛肉丝,厨师告诉我,是野猪肉,不是牛肉。那一段时间,总吃红焖果子狸,就想吃一次红爆牛肉了,听说是野猪肉,我来了劲,让厨师切成最细的肉丝,拌酱油抓芡,重油青蒜爆,那肉真是又韧又香啊,至今没有忘记。只可惜,现在去了人家绝不肯给动物野味吃,人家只让我吃野草,或野鱼虾。
《味蕾上的南方》 木鱼镇的腊蹄子鼎(图)
鼎这个炊具已经失传了,走遍大江南北,作为礼器的鼎也不复见,官府改用狮子镇守威严,雄狮踩个绣球,雌踩个小狮,礼器之鼎只在寺庙可以见到,作香炉用。从炊具到香炉,可谓从俗世到宗教,这段历程走得比较远,历史的烟尘也已经消散千年。 江南才子王勃作的《滕王阁序》,第二段有宏大景观:“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此间就有“钟鸣鼎食之家”,这家当然好大,大到的程度吃饭时要敲钟,有一大排鼎盛着各样肴馔,听起来,可以赶上一座军营。这样的家,是大家兼豪门了。《红楼梦》第二回里有这样一句感叹:“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细想之,鼎这玩意儿虽然有宏大气象,烧饭或者煨汤,都太不方便,搁在故宫院里做做样子,倒能摆出一鼎煮天下的气派!鸣钟吃饭,可休。现在饭前可发短信,多少人不论,群发。然而,注定汉民族的炊具起源于鼎,在仰韶文化(公元前500-公元前3000年)已经有陶土制鼎,那时估计没有人奢侈到用鼎来做礼器,陶鼎是那个时期的高科技,再往前的高科技,就到石器时代了。殷周时,中国人开始用青铜铸鼎,用于祭祀时炊煮及盛放供肉,先秦文献记载有夏铸九鼎,那时候鼎是王朝政权象征,周礼规定君臣依等级拥有不同数量的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有方形四足的,有圆柱形足或方形足的不等。周鼎身厚重,简纹饰,到了春秋战国,鼎越做越薄,重量也轻,想来铸造技术大有提高。 中国有一口最著名的青铜鼎,叫司母戊鼎,它是鼎王,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合金成份是:铜84.77%,锡11.64%,铅2.79%。司母戊鼎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饕餮是传说中一种好吃的野兽。饕餮?我们都是饕餮!哦,这是一头多么可爱的动物。 由一炊具发展到政权象征,说明炊具的重要意义,它容涵着中国原初的人文精神,没有一户之鼎哪有万户之国?我想,后来的砂锅,鼎罐还是继承了鼎的,去了足的原因应主要考虑加工及烧制的便利,这不用说了。不过,我在1990年代,还用过北京的老式铁锅,它就有三足,锅径小而深,可能是传说中的小型的镬。在广大的南方地区,鼎状的炊具仍能见到,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叔叔就买过一口鼎罐,他用白观音土造了一个炉子,外面用铁皮做了箍,用鼎罐煨排骨汤,烧木炭,总要我用大蒲扇扇火,我不厌其烦,把玩的时光都担误了。我出生的地方,产青铜的湖北大冶,则比较普遍使用鼎罐,这个鼎罐铸铁制造,圆锥形,有四耳,耳上有孔,穿8号铁丝做提梁,除了无足之外,与古时的圆鼎完全相同,现在偶尔还能在乡间见到,今夏去神农架,在大山人家里也看到了,他们叫锅吊子,终年吊在火塘上面,烧水或者煮肉。因为没有足,圆锥体的鼎罐在炉子或地上放不稳,所以还要做一个带足的圆架子支持它。 南方的铁匠铺也经常看得到鼎罐,铁匠喜欢把鼎罐吊在铁炉上,用黄豆煨猪脚,去年,我在黄石下陆区马家村见一位安徽宿松来的铁匠用鼎罐煨黄豆和猪脚,他工作时,用碳素钢叮叮当当打制割草的镰刀,以5元人民币一把的价格批发给日用百货商。在燃气灶时代,城镇人就很少用鼎罐当炊具了,首先它的傻大黑粗的形状不雅,热能转换方面也不如高压锅有优势,即使在过去的鼎罐时代,它也是被农户用来吊在灶口,借灶口的余热煨汤。但是,用鼎罐焖红薯或土豆饭却十分不错,因为平底锅主要是锅底取热,而圆锥体的鼎罐,热能一直可以抵达鼎罐的颈口,使焖制的食品最大范围地接触热能。或大约因此,古代道士炼丹煮药,都采用了鼎罐。 俱往矣!不论是西周的毛公鼎,还是商晚期的后姒康方鼎,它们都成为历史,只留下诸多以鼎结构的词语,比如定鼎,指的是建立新的王朝,定鼎中原如是,直白地说是到中原去熬粥喝。问鼎,大约是指图谋王位,而鼎革就大至相当今天的改革了,如鼎新革故。而鼎食,指的是贵族的奢侈生活。《周礼&;#8226;天官&;#8226;亨人》:“亨人共掌鼎镬,以给水火之齐。” 一大炊具,结构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设若周朝时起就有国徽,我相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