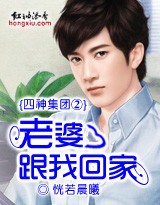回家 安顿-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见我们一起在家里看电视,也不说什么,叫一声阿姨就回到自己房间,也相安无事。我已经不企求她能接受这个继母、只要她们能和平相处就行了。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岁数不饶人,我一天比一天老了,将来小珍总要离开我,我也得有个伴儿啊,谁能说我这么想就是自私?我当时觉得小珍也自私,她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孤苦伶订地为她妈守后半辈子呢?
李强期待着我说些什么,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理解小珍,也理解他。
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种骨肉相联的关系,使得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理由来要求对方的接纳。
我告诉李强,其实在对待父母的再婚问题方面,小珍的反应还不算是最激烈的。
我的一个中年受访者曾经给我讲述他再婚的经历:他在和前妻离婚6年之后碰到了新的意中人,决定结婚,但是他的儿子坚决反对,从恶语相加到以死威胁,他始终坚持,结果,在他结婚的前一天,下班回家的他发现家里所有的电线全部被剪断了,被褥上面洒满了汽油。李强在这里接上了我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离婚还是丧偶的人,都有权重新开始生活。人和人真是不一样,我就听说过有儿女支持自己的父母再婚的,孩子再好,也代替不了老伴儿。
不过,我觉得在我和小珍之间,我确实也有责任,我关心她太少,她妈生前也一直是为我们这个家操持,没过什么好日子。所以她妈去世了,我又要跟别人结婚,她心里不平衡,也替她妈委屈。我理解。
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她出走前一天晚上,我们为这件事吵架。我才明白,她其实是把她妈出车祸这件事也归罪于我对家庭不负责任。她哭着跟我说:“你知道我妈为什么会出车祸吗?她每天下了班都是急急忙忙回家,就是为了早点儿给我和你买菜、做饭,从来没有人帮我妈。你要是能分担一些,她就用不着那么赶,她就能从容地往家走,用不着跑着过马路,她就不会死!你们现在凭什么在我妈弄得这么好的家里享清福?”
那天我也是不理智,我说:“没有我哪儿来的这个家?
再说你为什么不帮帮你妈?还要让她为你操心?,从那次在家里撞上我们之后,家里没少吵架,但是真正这么伤害还是头一次。她可能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吃了一惊。然后马上就收拾东西,说:“我走好了。”说实话我没当真,觉得她最多是闹闹脾气,出去一会儿就会回来。结果没想到她真的一走就彻底不回来了。
小珍的话让我现在想起来还特别难受。对我爱人,我的自责真的是从心底发出的。她过世之后,我看着小珍一天天越来越像她妈,心里特别难受。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我爱人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关心过她的生活,她喜欢什么颜色、爱吃什么、想要点儿什么我都不知道,也没问过。我老觉得还有时间呢,等我们老了,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一起出去旅行……但是……我这辈子怎么也不可能补偿她了。小珍这一走,我的心都提拉到嗓子眼儿了,她一个女孩子,真的出什么事我怎么跟她妈交代、我一辈子都要活在地狱里了。
我也难埃这几天到处找不到她,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小珍,孩子满脸都是眼泪,跟我说:“爸爸,我到哪儿都带着你,我不离开你,咱们就这么过一辈子,不好吗,?”
有时候我就想,等小珍回来,我们还是相依为命着过吧,我已经欠她和她妈妈那么多,就让我用后半辈子来还给她们吧。
前两天,我跟我那个女朋友说,我们还是算了吧,就算是报答孩子她妈给我的前半辈子,我也应该把我的后半辈子给她。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能让我不要我的女儿,只要小珍能回来,我什么都愿意依着她。
到这里,李强似乎就讲完了。
他沉默着吸烟。我问他,那个女朋友是什么态度,他咧了咧嘴,想笑而没有笑出来,“她能是什么态度啊?不过凭良心说,她对我、对小珍都不错。给小珍找工作那阵子,都是我联系好了她去跑,打通关系、送礼,约时间面试,都是她去办。
就连面试那天小珍穿的衣服,都是她给买的。当然,我就跟小珍说是我买的,我怕说出来她就不穿了。其实,我们俩还是挺合适的。这些天,她也一直跟着我着急,走到哪儿都不忘了跟人家说一句,如果你看见她,就告诉她,我们等她回家。她已经把我们三个人当成是一个家了李强不再说话。我惊异地发现,他在讲述他去世的爱人时的表情又一次浮现在脸上,有些朦胧、有些凄然。
我说,我会把他女朋友的这句话作为这篇“口述实录”的结尾,而且,我非常想告诉小珍,这个阿姨其实也会很爱她、关心她,尽管可能跟她妈妈爱她的方式不太一样。当然,她也会用她的方式来照顾用李强自己的话说是“一天比一天老”的爸爸。
李强在离开我的办公室的时候,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说:“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
7月27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对李强的采访整理成文,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的声音有点兴奋:“小珍回来了。这些天她其实就住在同学家。她说她想明白了,不应该阻止我选择自己的生活,她让我替她跟那个阿姨道歉,她说她爱她妈,同样也爱我,希望我不要像对她妈那样对这个阿姨……”我在电话这一头慢慢闭上眼睛,尽最大努力去想象,小珍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我无法压抑那种迫切的。想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愿望,我想知道,两个星期的时间,她走过了怎样一段艰难的历程。那应该算是一种成熟埃电话另一头,李强依然在自说自话:“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小珍一直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
第四章 你的肩是我一生的天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4日9:00AM采访地点:北京建国饭店
姓名:晨钟性别:男
年龄:39岁生于福建,一岁来京,1978年考入北京某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2年在同一学校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留校任教,1987年赴澳大利亚自费留学,1990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悉尼工作,结婚、生子,并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晨钟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个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把他培养成人的人,那个他每一想起就会万分牵挂的人,那个穷他一生所得无以为报的人,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家,更有一份人间的至爱亲情,不管他离开多久、走了多远,这个家始终在他心里最柔软的一个特别角落里珍藏着。知道了真相的晨钟时时会陷入一种莫名的自责,他的获得是以家人的一份牺牲为代价的,他的存在曾经决定着父母的很多取舍,他的幸福之中包含着一层更深的意义,那是一对担当着抚养他的责任的人的别无选择的道德追求。那是一种细腻的距离感,隔着道义的门槛,隔着用关怀做成的屏蔽,徘徊在一个家庭之外。我是在晨钟短期回国的间隙联络到他的,我和他以及他的家庭都曾经是很近的关系。从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开始,大约有将近12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邻居。我也是在他出国定居之后,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原来他不是他妈妈的亲生儿子,那个千辛万苦把他培养成人并且一直被他称为妈妈的老太太,其实是他的大舅妈。
1998年10月4日,中秋节的前一天,我如约来到建国饭店晨钟的房间。
穿过长长的走廊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忆着小时候那个被当作大楼里所有小朋友学习的榜样的晨钟哥哥,那时候他清瘦、颀长,永远是一副在思考问题的模样,每次父母在因为学习教育我的时候,总会说:“你看看人家晨钟。”我也曾因为害怕上动物解剖课而一再地间他,每次解剖之前是不是也会给那个将死的小动物打一针麻药;甚至在我第一次跟着大人出去吃西餐之前的那个中午,他用四根筷子比划着教我怎样摆弄刀叉……年少时的故事都已经在逐渐褪色的记忆里慢慢沉淀下来。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成熟、优雅、态度从容的男人。我们同时说“你好”,同时又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同时伸出手又同时没有相握——也许在经过了一段悠长的岁月之后,握手这种司空见惯的礼节还是显得太轻大轻了。
当我仰起脸来想把这个我少女时代的偶像看得再清楚一些的时候,晨钟重重地抓住我的双肩,用力一握,我的心也随之微微一沉。
酒店从来只是一个行人的驿站,尽管酒店的房间已经具备了一个简单的家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设施。但是,在这个打开所有的门、陈设都一样的地方,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归属感的。然而是不是只有在这样一个毫无情感色彩的地方,才更适合我们谈一个饱含感情的话题?
我在靠窗的沙发里坐下,旁边茶几上是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晨钟把一杯热茶放在我的手边,然后坐在我的对面。
其实很久以前,就在我刚刚知道有关我的身世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想给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留下一个纪念。而且,我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妈能看到。虽然我在国外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含蓄在我身上一点儿也没减少,最动感情的话,还是愿意写下来,说,是说不出口的。我要跟你说的话,其实已经打了不知道多少遍腹稿。
每当我想起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这些事情和这些话就会在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温习,但是,每当我准备要说给他们听的时候,就发现,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们之间的情结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我宁愿认为这是一种血缘深处的内容,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
我愿意告诉你,是因为你曾经亲眼看见在我家发生的一切,但是同时你又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大多数人在面对别人的生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才有了诸如猜测,怀疑和误会之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他对自己要说的一切已经了如指掌,还是他已经习惯了这样逻辑分明的说话,晨钟的语言是清晰、精到的,没有我插话的余地。
你最近见过我妈妈吗?
我告诉晨钟,最近一次见到他母亲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前,老太太精神很好,头发灰白,只是我发现她在买东西看价钱的时候要掏出眼镜来戴上,“到底也是快70岁的人了。”晨钟双眼平视,微微点一点头。我妈今年65岁,是有些见老了。
晨钟的眼神有些迷茫,一种似乎很遥远的东西充满在他的沉默之中。等他重新开始讲述的时候,我无论如何再也无法打断他了。
我的亲生父母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在我一岁的时候,他们一起死于一场事故。
之后,我的大舅舅,也就是你认识的我爸爸,到福建把我接到北京,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家里的老大。当时我妈妈还没有孩子。这些是我在澳大利亚准备结婚的时候才知道的,是我最小的妹妹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医生怀疑妈妈得了食道癌。她说:“大哥你一定要回来一次,要不,你一辈子都会后悔的。”后来她就说了这些事情,她说她也是在整理爸爸过去的一些信件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经常想,如果我小妹妹没有偶然知道这些,那么我的父母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不是我妈妈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想法,因为他们对我那么好,跟对我弟弟和两个妹妹一样好,甚至比对待他们还要好。
知道了这些之后,我把小时候的很多事情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原来不算什么的生活细节,在这种时候都有了特殊的含义,这些意义是我在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永远也不可能发现的。
其实,很小的时候,我从别人的眼神当中也看到过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有些大人会跟我逗着玩儿,说:“你是你妈的孩子,你弟弟、妹妹是你爸的孩子。”我回家问我妈,为什么我们四个孩子不姓一个姓。我妈给我讲了一个特别美丽的理由,到今天想起来,我都觉得那个理由真完美啊,我妈说,我是她和我爸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要姓我妈的姓,因为这个孩子是我爸送给我妈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在来北京之前就是叫现在这个名字的,我的生父刚好和我妈姓同一个姓,纯粹是一个巧合。但是,我妈给我讲的那个约定让我一直感到特别骄做,因为从这里我认定我是我妈最喜欢的孩子。我觉得在我的姓名问题上,我父母肯定是动了脑筋的,为了让我能跟别的孩子一样没有心事地长大,同时也能保留我生父的姓氏,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用心良苦。
她确实也是对我最好。我们小时候,各家的生活都不宽裕,孩子越多越是这样。可是,每年春节我都有新衣服穿,我弟弟就不一定有。他穿的都是我穿小了的。
我妈说,别人家也都是这样,一件衣服大的穿了小的穿,直到穿坏了为止。我记得有一年,我弟弟也要新衣服,我妈就把我穿过的一件修改了一下。一件蓝色的夹克衫,她把领子上缝了两个白色的斜条,像海军制服似的,然后又把两个方的兜拆下来,剪成船锚的样子重新缝上去,我弟弟穿上特别高兴。
那时候我也觉得我妈是偏心的,对我弟弟总是不像对我那样无微不至,所以我一直是在她的呵护下长大,我弟弟就不是,他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他比我小两岁多,可是在学校里,经常是他替我出头、打架。他为了保护我,把别人打了,人家找到家里来,我妈给人家道歉,之后再打我弟弟。我以为我妈最喜欢我,所以偏疼我,现在我明白了,恰恰因为我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她才会这样对我。
我应该怎么跟你说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小时候,有一次四个孩子一起得了甲型肝炎。肝炎是富贵病,营养很重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