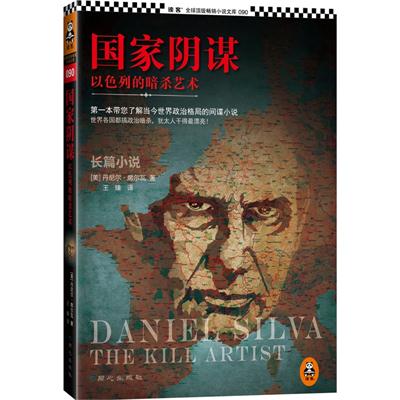艺术的梦与现实-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默然不拈笔杆么?。。因此,近年来,我写了几篇哀悼、回忆的散文,
如《我们不能忘记的人》、《悼聂绀弩》、《纪念一位大众文学创作家
——老舍先生》等。此外,我还写了一篇《成都去来》。它是我83 岁入
蜀,自成都回京后写的。这怕是我30 多年仅有的一篇游记文章了。
解放后,对散文作品虽然没有绝笔,但所写实在不多。从思想、风
格说,它跟解放前后期的作品没有太大区别。自然,所写的对象有些不
同;但作为一种创作,却没有什么跃进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找出些长处
或异点,似乎近年来所写的有些文章,情思较深挚,而风格也较为施展
自如,少些拘束罢了。
时光真如打闪。从20 年代前期开始学习散文小品,到现在已经60
多年了。它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许多年来,为了人世间的各种因缘,
断断续续地总算是在写作着(其中一个时期,对它还是那么亲热和眷
恋)。现在回头看来,虽然它们在内容上,多少抒发了各个时期个人的
思想、情趣,也没有忘记对民族、社会命运的关心(特别是后期的作品);
在艺术上,也随着时间的向前而有些进境;但是,严格说来,我的散文,
无论质或量都是比较薄弱的。过去有些文艺界的前辈和朋友,在这方面
曾经给予我以鼓励和祝愿。对于他们,我现在只能吟诵自己数年前所作
的一首七绝的末句以谢罪。那句诗就是——
“眼中人愧负先生!”时代在前进,散文小品的创作也在前进。今
天,我们文艺界已经有不少青壮年同志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作为一个
不争气的先行者,我只有向他们鼓掌,只有望着他们的背影致以虔诚的
祝福。希望他们能够远远超越我们这老一辈而绝尘狂奔!
【附记】
去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委托北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蔡清富同志编辑我的散文选
集。清富同志希望我对自己的散文说几句话。记得前些时候,《人民日报》第八版开辟了一个“我
与散文”专栏,我不但喜欢地读了那些相识者和不相识者的文章,而且欣赏那个栏目定得好。自
己也跃跃欲试,却终于没有执笔。现在,利用病余时间,匆匆赶成这篇小稿,一方面酬答清富同
志的好意,另一方面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1988 年4 月中旬,于北京友谊医院病房《文艺丛谈》自序
抗战前,约莫有近10 年的时光,我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费在民间文化
和原始文化的探索里。每天盘旋在我脑海里的,大都是那些很偏僻的问
题。踏进我书房里的人,看见四面架上那些书籍种类的繁杂及名称的古
怪,他们即使不好意思摇摇头,心里恐怕很少不感到“奇异”的。一个
最熟悉的也相当有学问的朋友,曾经当面告诉我,他不愿读我那些自以
为很用心写成的论文。因为他看到题目就觉得莫明其妙了。但是,这并
不是说,在那些年月里,我真能够完全和文艺绝缘。我常常读着《草叶
集》,甚至于《恶之花》,我也醉心着罗兰的《托尔斯泰传》以及法朗
士的《易匹鸠尔之园》,。。在写作《民间药物学》、《种族起源神话》、
《斗牛风俗的考察》等论文的另一面,也写着抒情的诗章或散文。在满
堆着赫顿、帕利、涂尔干、陀伊、松村武雄等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
书籍的桌子上,也混杂着荷累士、叔本华、罗斯金、奴尔道、居约、弗
里采等的美学或文艺学的著作。我并没有将文艺拉到生活圈外去,不过
已经失掉过去那种专一的亲昵罢了。虽然这样,但是现在想起来,如果
在那些时期里,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向着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兴味
的文学事业前进,纵然有种种不能够克服的限制,那结果总不至于像现
在这样荒凉罢。这是提起笔来给这个集子写序文的时候,不免要首先感
到的一点懊恨。
“抗战是轰雷!”在它巨力的震撼中,一切事物都改观了。正像别
的许多人一样,我也在这震撼中猛醒过来。不,我用了和从前大大不同
的姿势活动起来。我居然穿起戎装,出入枪尖炮架间。这决不是以前每
天呆在书房里的自己所能料到的。自然,在我少年时候所作的诗篇中,
也曾歌咏过投笔从戎的定远侯和那情愿马革裹尸还葬的伏波将军,在读
过拜伦卿的传记后,也曾热情地羡慕那位海盗诗人抛下游乐去为古希腊
战斗的豪侠。但是,那到底不过是一种罗曼的诗情罢了。轮到自己穿上
草青的军服来(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提枪的人),那就说是梦,也是颇
荒唐的梦罢。可是“现实”是不容易测度的魔术师。它使那“难能的”
成为“实在的”。那不是梦,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其实,在这样激变的
时代里,这种变化不过是一桩“平凡的故事”罢了。环境变动了,生活
变动了,精神自然不能再保持它的故态。学者的古铜色的梦已经烟消,
现实丰富的声音、状貌在耳边眼前跳跃着。我半闭着眼的文艺的魂跳荡
起来了。我写着诗,写着艺论。我尽量让自己感情的呼吸融合在时代的
大潮汐里。后来,脱下佩剑,再拿起熟悉的粉笔,我的生活暂时又回复
到往日的样子。但是,已经动荡过的心再也不能够完全平静了。而且,
这些时候自己虽然隐居在学院里,外面却仍然是火星四迸,炮声隆隆,
又怎能够叫这颗心再死沉在尘封的古井底呢?尽管热力减少了,在压不
住心跳的时候,我还是提起那管笔来——让它跟着情思的野马去驰骋一
回。这个集子里所收辑的短文,大多数就是在上述的情形下产生的。
我为什么要收辑起这些短文呢?要举述这理由是不很困难的。譬如
说,集印起来可以便利自己将来的回顾。或者说,人对于自己所产生的
东西多少不免有点溺爱。但是,在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比较重要的理
由,就是这些短文,尽管是急就章、未定草,尽管是怎样不成器的东西,
里面多少地反映着我个人从灰色的书堆里爬出来的新生灵魂的影子,里
面多少地流荡着我们这大时代里活跃的生命的气息。它不够深刻,不够
响亮,不够光华。它像蠕蠕爬行的小动物,像不能远彻遥空的燕雀声。
这是我的羞耻!(不用问,它是由于个人学识的浅薄,或写作条件的限
制。)但是,它到底是蠕动、是鸣声。它到底是摆脱了“死”,摆脱了
“喑哑”的生命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我就有勇气为它要求继续的生存
权。它标记了历史,标记了个人的和社会的历史(即使是有些迷糊),
因此,它就得存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
1947 年12 月10 日改定。
【附记】
本书编成后,曾交上海某书店,但因政局关系,终未能印出。部分文稿,后来陆续收入一些
散文集中,有一些,则收在现在这本书中。
1994 年2 月,于励耘红楼《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
——纪念该刊创刊七十周年
一
1922 年12 月24 日,这个日子,在我国一般人,甚至学界中人的眼
里,也许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是,它在我们这些从事民间文艺
学和民俗学工作的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等闲!它是一个饶有光彩、值
得纪念的节日!
70 年前的这个日子,一种16 开、每期只有8 个页码的小刊物在北京
诞生了。她就是《歌谣》周刊。她的前身,是几年前的《北大日刊》的
专栏《歌谣选》,不过后来她在内容和篇幅上都有所扩大了(从第1 号
至第24 号,她仍附在《日刊》上发行,以后才独立发卖)。她是两年前
成立的歌谣研究会的会刊,隶属当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歌谣》周刊,自1922 年末创刊,至1925 年6 月停刊,一共出版
了97 号。曾经陆续汇集为合订本四册。在发刊一周年时,还出了一册纪
念特刊。第97 号以后,因为内容并入《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就
不再单独刊行了。
《歌谣》周刊篇幅不长,但内容却相当充实。所载稿件、资料方面
前期以歌谣为主,后期扩大到兼收谚语、俗歌、故事、方言、唱本及民
俗记录。理论方面,除了探索、讨论的文字外,还有一些译文①。其特点
之一,是出了一些专号(如孟姜女、看见她、婚姻、腊八节及方言、方
言音标等专号)。这种作法,为后来中大的《民俗》周刊和杭州中国民
俗学会的《民间》月刊等所继承。
《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宣布自己的目的有二,一是学术的(民俗学
的),一是文艺的。关于民俗学的目的,据《发刊词》执笔者的说明是:
“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在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
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
关于文艺的目的,执笔者的说明是:“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
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
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
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
发展。”这种主张和说法,过去曾经长期引导着我们这方面活动的观点
和实践。现在看来,它不免有些粗略和狭隘,但基本上没有失去存在的
价值。
这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来,不免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却是
在当时文化界新潮怒涌的环境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作用的。她唤起
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感
情。一时响应她的活动遍于全国。许多省、市地方的日报、期刊,纷纷
搜集专集,刊载民间歌谣及其他口传文学作品。这方面的专集,也有一
些大都市书店或地方教育机关刊行了。有关歌谣、谚语、传说、故事(又
称“童话”)等的探讨文章和评述篇章也不断地在期刊上出现。
在《歌谣》周刊创刊后的那几年里,搜集出版和谈论民间文学,形
成了一股巨大汹涌的浪潮。这一段学术活动的经历,因此成为我国现代
文化史和学艺思潮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并且受到国外学者的注
意。他们已经对它开始了专题探讨,还写成了有一定分量的学术论著(例
如美籍学者洪长泰博士的《到民间去》等)。
①
1927 年,我曾选编该刊一部分论文为《歌谣论集》,于同年印行(北新书局)。
我国近年来学界在民间文艺和民俗学领域都有巨大进展,气象是十
分喜人的,尽管它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种伟大的、炫目的成
就,从它的形成阶段看,固然有它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如果我们
从学术自身发生、发展过程的规律看,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也不是跟我
国现代史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歌谣学的兴起和活动,正是它的密切相关
的部分)毫无关系的。换一句话说,《歌谣》周刊等的文化活动是对当
前这种新局面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因素。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
的,歌谣学等的发展,又何曾能例外呢?。。
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引导下走上新的学艺道路的。从我
的专业思想和实践的经历说,《歌谣》周刊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巨大而深
远的。当此《歌谣》周刊诞生70 周年的时候,不但在感情上要求我叙述
跟她那段亲密的学艺关系,而且在道义上也要求我有责任这样做。这种
关系不止是我个人的私事,她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史上这方面学术史的一
角。这样想来,我就不再顾虑其他,而欣然动笔来略述我们的那段关系
了。
二
事情过去已经70 年了。个人经历了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它的细节)
还不可能都记得清楚,何况我又是一向不大记日记的?尽管如此,大略
的情形还是能够记得的。因为它(我跟她的关系)是我学术史、乃至生
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何况眼前还有《歌谣》周刊里的记载可供参考呢?
我跟《歌谣》周刊发生关系的时期,正当我20 岁的前后。那时我在
故乡海丰的一些小市镇里教书。这种环境,在当时自己的心里,是对它
感到不快、甚至要给以诅咒的。因为它压抑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希望。它
叫我难以开拓广阔的眼界,不容易获得滋养的精神食粮。然而,天下间
的事情,往往是同时利害互见的。谁知那可诅咒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有
利于我学艺事业的活动呢?我正是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环境中,开始
接触到《歌谣》周刊,并且进行了对歌谣等的搜集、记录和思考活动的。
大概是1923~1924 年间,我开始读到《语丝》杂志。这当然大大激
起了我心灵的喜悦。可能正是从那个小刊物里得到的信息,我知道了有
《歌谣》周刊这种刊物的存在。也许是由于我的请求,那位与我有过通
信联系的北大文科教授,嘱咐管发行的同志(可能是常惠先生吧?),
给我陆续寄了《歌谣》。那大概已经是第48 号左右了(以前各号,我除
了得到该刊合订本第二册之外,后来又借阅了容肇祖先生所保存的、原
附在《北大日刊》上的那20 多号)。以后,我继续阅读该刊,直到她停
止刊行。她那册蓝底上有白色的镰月和许多星星封皮的周年纪念增刊,
我也荣幸地受赠过。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欢
喜”,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欢喜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
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
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
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
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也许是由于我的这
种向心力和积极寄稿的行动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吸收为歌谣研究
会的通讯会员了——记得那是由常惠先生办理并通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