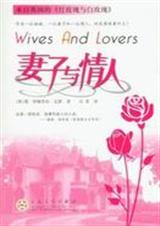铁屋子与窗户-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女骗子精通心理学。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人的脉博:国人对日本艳羡不已,对日货更是五体投地。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忘掉吧,战争赔款也一笔勾销,我们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使的女儿”谁不肃然起敬?谁还会想到“日本大使的女儿”是骗子?阿Q们总是对有钱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怕”。
不恨日本人,这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当以色列特工千里万里之外追捕昔日的纳粹余党的时候,中国人却嬉皮笑脸地向日本讨贷款。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看作天朝国民,把日本人看作倭人,但血就是血,债就是债。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日本罕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写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考证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这头禽兽是剑道高手,七十岁了还身体硬朗,那双扼死郁达夫的手保养得很好。战后他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也没有感到心灵的内疚,舒舒服服地活了半个世纪。
在日本,这样的畜生有几千、几万、几十万?
“日本大使的女儿”可以在北大骗十多名学生,这对北大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北大之为北大,乃是有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契机是反对日本占我青岛。那些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前辈们,知道他们的校友们一听到“日本大使的女儿”便像阿Q一样膝盖发软,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八百壮士的上海、血染征袍的上海,如今成了向日本输出廉价妓女的基地,这个“玩笑”,即使是昆德拉也承受不起啊!
日本凶焰高张,又图谋我钓鱼岛。北大只有几个学生站出来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后来便没有下文了。大部分人还是日本的“热爱者”,“有关部门”更是同别里科夫一样含叨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于是,一切作鸟兽散,连征集签名也成了空谷回音。
一个假的“日本大使的女儿”就能狐假虎威,那么真的“日本大使的女儿”驾临我校呢?我看过太多的良民们举着小旗子欢迎的镜头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反叛之后
一九九六年冬天,美国人再次选择克林顿当他们的总统。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的克林顿听到当选的消息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领袖,对于总统的宝座似乎心安理得。殊不知,二十八年以前,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反叛者”,最憎恶的恰恰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因为总统代表着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代表着金元和黑幕,代表着谎言和暴行。
六十年代,是反叛者的时代。在中国,数千万的红卫兵在串联的路上,社会是一口被他们掀翻的锅。在美国,“愤怒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阿克写下了他最著名的的小说《在路上》。是的,整整一代美国人都在路上:民主、反战、性和毒品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华盛顿进军,白宫和国会山庄成为人潮中的孤岛。一九六八年是“反叛者之年”。那一年,美军在越南兵败如山倒;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那一年,宁静的美国大学忽然成为风暴的中心,二十二岁的克林顿在大学的广场上向示威的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发誓要同反动的政府绝裂。全副武装的军警正准备开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堪称反叛的一代,一夜之间,他们就撕去了资产阶级二百年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一切反叛的基因和资源都被纠结在一起。这对上一代人来说,确实“难以置信”——这是美国吗?
二十八年之后,反叛者们仍然在路上,克林顿横穿美国,为竞选风尘仆仆地奔波,不过他已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激情犹在,反叛却荡然无存。克林顿的同龄人们,也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随着潮起潮落,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从政界要人到商界大亨,从学术精英到文化大腕,各个重要领域都被这群曾经愤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垄断。
反叛,成为回忆中的光荣和自豪。反叛之后,必然是对“反叛”长久的反叛。当现存秩序向反叛者们敞开母亲温暖的胸膛的时候,反叛者们灵魂深处的游子情绪扩散开来。于是,他们走下神的祭坛,走向人的真实与卑微。加缪认为,反叛的人是处于神圣之前或之后的人,他专心于求索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反叛者会发现一切,或一无所有。反叛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反叛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这位哲学家的死亡方式证明了他对自己的这一命题的捍卫——加缪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正当盛年的哲学家来不及创造更多的思想,便与汽车——二十世纪技术发明最辉煌的象征之一——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同归于尽。
我几乎不相信克林顿这个满脸漂浮着伪善伪真的笑容的家伙,当年曾是勇敢的反叛者。他反叛酗酒的继父,反叛去越南送死的命运,反叛厚厚的教科书,也反叛这个最富足也最强大的国度。这种反叛是对纯洁的怀念,是向生存发出的呼唤。怀念是忧伤的,呼唤是痛切的。而青年的克林顿是愤怒的。愤怒这种情绪属于青年,中年人是很难愤怒的。谁见过中年克林顿的愤怒——在俄城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在痛斥萨达姆的时候?在遭到多尔攻击的时候?这些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离心灵的愤怒已经很远了。愤怒的表情只是为了表演,愤怒心灵却是为了信仰。
反叛之后的平静,是老人们早已料到的,而新的一代青年却难以忍受。我想,当中老年人为克林顿的五十岁生日祝福时,也有青年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加缪说过:“在等待成功的同时,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前赴后继进行的反叛的总和”。那么,反叛是否并无前后,而为一条生生不息的,不知何所来,也不知何所往的河流?反叛是一种难于用价值标准界定的姿态,因为人们对丑恶和非正义的判断是迥异的。对于反叛者而言,惟有相反的观点才是真实的,这恰恰是反叛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叛自身就在这里遭到了屈辱的颠覆。
我所处的是一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一切反叛都纳入哈哈镜里,被扭曲变形。这个反叛之后只剩下精神废墟的时代,连几朵萧索的野百合花都见不到。这个时代的反叛者,已堕落为抢劫银行金库的亡命徒和纵欲过度的艾滋病患者。假如一个时代有令后人怀念的东西,必然是它的反叛者及其反叛的行动;但是,今天我所处的时代,反叛却头一次缺席。在一地飞舞的鸡毛里,思想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什么也砍不动的刀。
我们越来越心平气和,愤怒则成了一种危险的情绪。看到电视屏幕上演技高超的克林顿们,终于明白:这也许是反叛者的必然宿命,谁能抗拒成功的诱感力呢?即使是一名真诚的反叛者。反叛之后,回眸之时,这才知道,能发生的都已发生,不能发生的永远不能发生。当初的想法,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二百五十九票对二百一十四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三百四十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过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然而,牛津人自有牛津人的想法。牛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六个月内赚取五十万美元。所以,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牛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于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摩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国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荒原》、汤因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含义。“大学”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价值,使青少年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其本国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类消除成见,并奠定理智的基础。这样的大学,方成其为“大”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校长真正理解了大学之“大”,他发展了前校长严复的思想,“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进一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事机关”。
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多年后,教育界仿佛有人懂得什么叫“大学”了。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而真正的根柢——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文史哲、数理化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状况,教育官员们居然还拍手称快,其短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与牛津大学的“牛筋”脾气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态多少有点不堪入目。
美国加州的教育部门制定了这样的人才计划:要求中学毕业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学生,要培养成真正的专家和研究人才,所以这八之一的人可以进入加州大学;从八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学生,则进入加州州立大学,成为一般的律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最后,三分之一以下的学生就进入加州机械学院这类的学校,成为机械工、电工等技术人士。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综合性大学比专业学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两者相差超过二十倍。
然而,我们教育界有的人却糊涂到了连“大学”与“学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时间,“邮电大学”、“建工大学”、“体育大学”、“化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匆匆忙忙地摘掉“学院”的旧帽子。虽然有了新帽子,它却显得不伦不类:不具备学科的“广谱性”、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的设置,也算是“大学”?与其名不副实,不如实至名归。
牛津的执拗背后,是对现代教育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着制造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结果,教育趋向功利义务,教育所产生的“智识分子”逐渐沦为技术团体惟命是从的工具。教育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复是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伟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丧失了锐气的北大,正在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大步迈进。
牛津大学拒绝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某种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学生可以由贵族向平民转化,但牛津的精神绝不放弃“贵族化”的精髓。它为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贡献的,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精明能干的老板、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大师。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岂是金钱所能买到的?牛津人最可贵的是有牛脾气,因而能够坚守受到攻击的传统;北大人却学会了舍弃本就不多的传统,自以为能轻装上阵,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柳湘莲曾经说过,贾府里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干净,再没有别的干净东西了。我则发现,今日,北大除了门前一对石狮子沉重,再没有别的沉重的东西了。作为一名正随着大潮变得越来越卑琐的北大人,我只能对像“老牛筋”一样的牛津大学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后,我想起了杜威的一段名言:“在今日,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隔离,因为各种高尚的职业,倘若管理完善,必须在具有社会、道德与科学意义的环境中从事活动。”
“铁哥们”蒙博托?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的《环球时报》上,有一则短评《蒙博托不全坏》。作者郭天禄,从行文中看,大概是从事对外工作的人员。在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孤家寡人客死异乡之际,在世界传媒纷纷指责这个残暴贪婪的独裁者之际,郭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发出别样的声音:“蒙博托不全坏!”我一向对观点新颖的文章有兴趣,便仔细读了下去。
文章一开始,作者便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评价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物仅仅依靠经济有无成就和腐败严重与否为标准,难免失之偏颇。”此观点多少值得商榷:固然,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不一定能将经济杠杆操纵得游刃有余,但是弄到他的人民连粥也没得喝,便多少有些问题了。我看过画报上扎伊尔儿童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看不出孩子的具体年龄,他赤裸着上身,下身裹着一小块破布。他已瘦得不成“人”形,



![太子与妖僧[重生]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7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