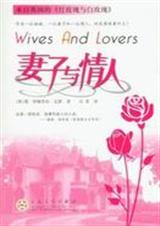铁屋子与窗户-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与季老的论点天然契合,但仔细一思考,却有质的差别。东坡认为,要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先得在庐山之中远近高低地认真观察,然后再跳到庐山之外,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透彻了悟庐山之真髓。“出乎其外”固然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入乎其内”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王国维所说的“人生三境”,乃是像登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走,先有“独上高楼”,才会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直到第三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手到擒来”的前提乃是“铁鞋踏破”,天上是不可能掉下馅饼来的。
世上没有空中楼阁,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季老却在这上面稀里糊涂。“偶尔也能搔到痒处,谈到点子上。”真的如此么?倘若一个人仅仅是站在门外,他能仅靠幻想就准确地洞悉室内的一切吗?我想,还是该老老实实地到门内走一走、看一看,从兵器库里取出十八船兵器,然后一路杀将出来,方能成圣成佛。否则,墙上芦苇的日子可不好过,一阵风来便东倒西歪。季老又说,“但我其他的工作毕竟还是太多,太杂、太急。没有能读完全书,被迫放下。”就连所要论及的著作都没有读完,一切议论岂不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不过,武侠小说中一流的高手能以“内力”伤人,隔空打物,想必像季老这样学富五车者,或许拥有此等本领。
谁失语啦?
“失语”是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的感受。我们已难于描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难于对当下的问题发言,我们拥有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被悬空了。具体到文学批评界,“失语”的感受更有切肤之痛。批评的缺席和批评家的焦灼,已然是一个令批评界难堪的事实。
但季老自有的他的高论,“一读到中国文学,我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此语堪称石破天惊。
首先,“中国文学”是指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抑或两者都包括?若是古代文学,自然可以用古代文论来批评。但古代文论已是用钝的武器,要有新的研究成果,必须引进西方文论方能庖丁解牛——例如有的研究者引进西方心理学来分析《红楼梦》,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十分锐利。关键是看如何使用,而不是“能不能用”。倘若挂羊头卖狗肉,自然是“失语”,但“失语”之罪过,难道能推到西方文论身上吗?倘若做到水乳交融,未尝不会别开生面,新瓶装旧酒。再看现当代文学,它的质地与古代文学已有天壤之别。我想给季老出个难题:您不妨用古代文论的一套语言,如“风骨”、“气象”等来阐释一下极具先锋性的现代汉诗,若能解释得通,我就接受您的理论。再举个例,如林白、海男、陈染等女性先锋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如何用古代文论阐释?可以想象,季老捧读这些年轻女子的小说时,眉头不知皱到怎样的地步。
季老说,“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不禁要反问:西方文论难道能偏激地看作“枷锁”吗?近代以来,几代文论家都在致力于引进西方文论,引进的西方文论在中国近、现代文论中一直在唱主角。迄今为止,它们已内化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二十世纪难道不也是无法回避的“传统”吗?),岂是能我们能够“彻底摆脱”的?这是邯郸学步的幼稚想法。季老的这段话中,“检查”、“阐释”、“术语”、“建构”、“话语体系”等名词显然是西方文论中的术语,可见他自己就没能“彻底摆脱”。有谁能搬起自己正坐在上面的那张椅子呢?即使是大力士参孙也不能。季老自以为没有“失语”,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古代文论家又听得懂几句呢?
分析与综合
季先生认为,中外文论的根本差异在思维方式上,“我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具体到文论上,中国古代文论虽然运用一系列玄之又玄的概念,但综合的能力却差劲得很,真正有点体系精神的两千年里只有一部《文心雕龙》。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有宏大体系的理论著作就层出不穷。
再看对待作品的态度。季先生把西方规定为“分析”,便认定西方文论家都像外科大夫一样,冷静地拿着解析刀,对作品进行严谨科学的解剖。但是,倘若读几本西方文论巨著,我便发现全不是那回事。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以及歌德的谈话录等,都把文学及文学家看作一个浑然天成的独特世界,具有相当高明的整体观照的眼光。西方的现代当代文论,更是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成为一门“综合学科”。相反,中国的小说评点,反倒更像季先生所说的“分析”——对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的品评,鉴赏和体味,有时到了入迷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吗?
文化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若硬要用一两个词概括东西文化的差异,那么必然带来谬误与偏差。这种极为危险的做法,稍有头脑的学人都“远观而不亵玩焉。”倘在两种文明接触之初,作如此简单、明了、青菜豆腐一目了然的区分,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对自我和他者都未能充分认识,只好匆匆抓住一些浮在表面的东西。但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已经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季老还作这样的区分,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我以为只有初中学生才会这样思考。看来,老人的思路确乎“返老还童”,回到童年时代去了。
此“混沌”与彼“混沌”
季先生从“混沌学”中为自己找到了立论的支撑点。本世纪以来,混沌学和模糊学在西方成为显学,这似乎足以证明东方早已领先于西方,因为中国早就有了混沌学。季文援引了《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条目,如形容嵇康的几句名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样描述一个的容貌气质,比起西方作家不遗余力地从头发写到鞋子来,不是混沌又是什么呢?
因此,季先生理直气壮地得出如下结论:“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宣布真理在握的老人,把玻璃珠当珍珠,还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季先生的这段豪言壮语,比之乾隆皇帝当年训斥英国使者的话毫不逊色。“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连“混沌”我们也早就玩腻了,你们还来拾我们的牙慧。
季先生自己说,“可惜我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微。我读过上面说到的几本书,也是生吞活剥,不甚了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搞懂以后再发言,没搞懂之前先保持沉默。季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只能从最大的宏观上来体会这几部书和这两门新学科的意义。”这就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在“生吞活剥、不甚了了”的前提下,能够达到“宏观把握”的高度吗?
正因为“生吞活剥、不甚了了”,幻觉便出现了:季先生将“此混沌”与“彼混沌”混为一谈,干脆将两种“混沌”煮成一锅“馄饨”吃。其实,“此混沌”与“彼混沌”的差别有如波音飞机与明朝时万户自制的木头“飞机”之间的差别。不过,国粹派硬要把万户视为飞机的发明者,为他申请专利,我也没有办法阻拦。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在向东方靠拢,他们也不过是向《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时代靠拢,向我们的老祖宗靠拢,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创造了什么?季先生没有谈“当下”的问题。这是老人的聪明,在回忆中总能找到慰藉。这也是阿Q的愚昧,因为他说“我爷爷比你阔多了”的时候,总是他被欺辱的时候。
拿来与送去
文章的最后,季先生又愤愤不平地提起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中国无一人获奖,这是一个让每个爱国心高涨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现实。症结何在呢?季先生认为,“简单明了地说一句话:这出于西方某一些,特别是主其事者的瑞典某些汉学家等人的偏见。时至今日,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显露之际,竟还有一些西方人把枕头垫得高高地做着甜美的‘天子之梦’,对中国毫不了解,而且也根本不想了解,相对而言,中国虽不能说没有崇洋媚外者流,但是连一般老百姓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了解欧美情况。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西方做不到。将来一旦有事,优劣之势立见,这是我敢断言的。”
中国了解西方,西方不了解中国,季先生将其归结到道德评判上。本来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足以让西方了解的程度,而西方则已经民主富强到中国非得了解不可的程度。但季先生巧妙地一转换,居然成了中国人比西方人心胸宽广、富于智慧的论据。当年的阿Q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因为阿Q是文盲,季老是国学大师。
怎样在世界文论中发出声音?季老开出的药方是:大力宏扬“送出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那么,季先生今天拿什么送出去呢?拿《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兼八股?拿它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打个落花流水?
回到当代文学上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和实绩,稍微对其有点关注的人都一清二楚:没有一位大师级的作家、也没有一部不朽的巨著,尽管有的侃爷宣称“一不小心写出《红楼梦》”,有的大腕说“五十个鲁迅还了得!”既然如此,何必对诺贝尔奖耿耿于怀?季先生对当代文学有几分了解?您能点出哪位作家哪部作品能获奖,比那些西方的“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家”优秀?
最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把落后当作进步;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无知的权威者。读完《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我感慨万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保持心灵的自由、进行理性的思考、追求纯粹的知识?睁着眼睛说瞎话,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学风,何日方休?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知·行·游
——重读杨绛
并非逍遥的“逍遥游”
久被埋没的钱钟书、杨绛伉俪,近年来如当代文化中的一对名剑,受到世人瞩目。有论者称:“钱钟书如英气流动的雄剑,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胡河清语)杨绛以《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几本不大的书展示了她对东方佛道境界的高深体认,其雍容自若的风格令饮同一源文化之水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然而,当我换一种心境重读这些书时,却发现在这智者的逍遥游中也有着并不逍遥的一面。逍遥的极致,其实也正是矛盾的极致。
马尔库塞说:“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能,是一种综合,即把在被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断残迹加以收集汇总的一种综合。”杨绛的散文、小说几乎都是以残存的回忆为素材。《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很难表述的时代——文革究竟是一幕怎样的悲剧?杨绛深味庄禅之道,自然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用“丙午丁未年”而不用公元纪年,也颇值得读者玩味,是为突出故事的发生地是“中国”这一文化空间,还是为了在时间上造成一种历史间离的效果?然而,无论怎样陌生化,目的都是把时代背景处理成庄子所谓的“羿之彀”,作者自己则“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俨然以一种“游”的姿态严阵以待。
在《将饮茶·隐身衣》一文中,杨绛总结出这样一条生存之道:“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正是凭借这件隐身宝衣,杨绛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中,游刃有余,荣辱不惊,仿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人。在《记事》中有这样一处微言大义的细节:“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里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暴晒,窗帘已经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人撤下。”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智慧——“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这是杨绛对庄周“逍遥游”所做的现代阐释。一道帘之隔,使得她心安理得地在帘内看帘外的世界,一切芸芸众生悲欢离合,一切龙争虎斗刀光剑影都与我无涉,于是,眼前“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被派遣去打扫厕所,作为一个出身名门、留学英伦、执教清华的全国第一流知识分子,杨绛并没有同一阶层的人士普遍的、难以忍受的屈辱感。她认为在整个世界都已颠倒过来的时候,人生的苦乐并不取决于现实世界的蹇迫或宽容,而取决于自己“心游”境界的高低。“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连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



![太子与妖僧[重生]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7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