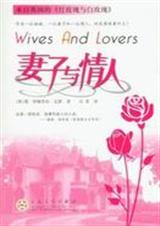铁屋子与窗户-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重要。
唐主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为此,我尊重他。
一百九十一
闽主曦嫁其女,取班薄阅视之;朝上有不贺者十二人,皆杖之于朝堂。
贿赂制度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五代时,闽主还处在低级阶段,用暴力来强迫行贿,未免太赤裸裸了。而到了如今,则已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在官场上,官僚们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若下属不向上级“表示”,则立刻被穿上“小鞋”,寸步难行。就像武侠高手,遥遥一指,你立即身中内伤,非得拿他的解药才能保命。神不知,鬼不觉。而下级往往抓住这些难得的机会,以“人情往来”为借口大肆实行贿赂,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一百九十二
后晋为契丹所灭。契丹主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世故”是一种极厉害的病毒,连和尚也逃避不了。人们最善于忘却的,是他人给与的恩惠。所以我们在给予他人的时候,先要警告自己:不要存在收取回报之心。否则,不必给予。
一百九十三
麻苔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灵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左右前后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
在李约瑟博士的眼里,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美不胜收的国度。但我居心叵测地想:假如这位大思想家落到麻苔手里,他还能这样思想吗?
汉学家看中国的事情,常常如同醉中看花看得模模糊糊。中国人却往往将那些赞美的话语拿来为我所用。
一百九十四
南汉主作离宫千余间,饰以珠宝,设镬汤、铁床、刳剔等刑,号“生地狱”。尝醉,戏以瓜置乐工之颈试剑,遂断其头。
把人间变成地狱,这是帝王们的实践;认为地狱比天堂还美好,这是帝王们的理论。权力让他们成为“非人”。假如南汉主自己的人头被他人拿来试剑,他还会觉得好玩吗?
一百九十五
史弘肇尤恶文土,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
极端的自卑导致盲目的仇恨。盗寇最爱做的事情便是屠杀知识分子。张献忠时代,“卒”们屠刀挥舞,“士”们人头落地。暴力的掌握者,不能容忍话语权力的掌握者。于是,流氓与士兵最喜欢杀戮知识分子。
一百九十六
军阀赵恩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其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豸法。
前些年,有评论家指责《红高粱》中剥罗汉大爷人皮的情节,认为它太血腥了。他们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然而,我们的史书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多如牛毛的、比这更残暴的事件。
恐血症的病人想方设法躲开鲜血,真能躲开吗?
我们必须面对那些血腥的历史,我们必须否定那些血腥的历史。对血腥气味的自觉,是我们恢复人性健全的前提。
一百九十七
军阀刘铢、李洪建与郭威征战,郭威获胜之后,刘铢、李洪建及其党皆枭首于市,而赦其家。郭威谓公卿曰:“刘铢屠吾家,吾复屠其家,怨仇反覆,庸有极乎!”由是数家获免。
郭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他自己全家被屠杀之后,尚能保持相当的理性与节制,令我为之折服。郭威在获得全面胜利之后,依然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杀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报仇并不是可以采用的惟一行动。鲜血流淌,终将沾上杀人者的脚;愤怒爆发,终将导致自我的毁灭。灭族是个绝对沉重的词汇,它是人性的反面、兽性的极致。郭威的所作所为,即便是一名现代人也难以做到。我衷心地向他致以一个甘地的信徒的敬意。
为抽屉而写作(代跋)为抽屉而写作(代跋)
我是个早慧的孩子,不到两岁,我便能区分十多种色彩。我有四个年轻美丽的姨妈,她们各自爱穿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衣服,我那时便叫她们“红姨妈”、“白姨妈”、“蓝姨妈”、“黄姨妈”。我通过色彩来区分她们,这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观察世界的方式——不愿执著于“本质”,而沉浸在经验世界那些鲜活的色彩里。因此,“颜色”变得比“姨妈”更加重要。母亲说,从那时起她便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孩子。
我出奇的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老师在称赞我学习成绩的同时,给我的学生手册上“缺点”一栏千篇一律地写上“不合群”三个字。那时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不合群”恰恰是从事写作的先决条件。“不合群”的我发现了蕴藏在落叶、流水、黑夜、灯光以及小方块字里的魅力,那种魅力既遥远又触手可及。
小时候,北大对我来说是一处海市蜃楼般的地方,北大人个个是无所不能的伟人。外公家“成份”是地主,被扫地出门,我对垂泪的外婆说:“我要考北大,以后给外婆修一幢好大好大的房子!”(小孩的想法是无遮无掩的)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被北大所接纳。北大是一座孤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岛屿,被潮水咬得遍体鳞伤的岛屿。成千上万的书籍堆砌为城池,构成“内”与“外”的分野。这座颓败的校园依然奉行不干涉主义。湖光塔影之间,“不合群”与优缺点无关。这就足够了。李卓吾说:“大丈夫喜则清风明月,怒则迅雷呼风。”我虽不能活得如此自在,却也无须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无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这是孤独给我的惟一的回报。
周围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写作了。我的写作却得以绵延不绝,从一九九三年到今,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先后编选了四本没有公开出版的小册子:《行者手记》、《明天》、《远方》、《思人》。许多寂寞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像前的草地上时,“为何写作”一直是痛苦我的“鸡肋”。
按照乐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未来而写作;按照悲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抽屉而写作。一叠叠的稿子被陆陆续续地塞进抽屉。抽屉里爬满令人厌恶的蟑螂,让自己的某一部分鲜活的生命与蟑螂为伴,这不是一种幽默的举动。
小小的抽屉像鲸鱼的巨嘴,不露牙齿地吞噬着我的文章。我,如同奴隶一样劳动,金色的谷穗却无一例外地要上交。而抽屉却对我说:这是惟一的接纳与憩居之地,除了此处,等待你的是铜墙铁壁,你撞破了头也不会有一声凛冽的回音。
为抽屉而写作是我自己的选择。命运选择了我,我选择了写作的方式。为抽屉而写作,意味着一块砖头从金字塔浩大的工程中剥离出来,尽管这块砖头的反抗对金字塔本身毫无影响,但砖头却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为抽屉而写作,必然自绝于外界的肯定。如果说戏剧上演的目的是呼应着绵延的掌声,那么我的写作仅仅是一只小蜜蜂为自己酿蜜。难以忍受孤独和使我筋疲力尽的方块字,昭示着写作的艰难。在那些身心交瘁的日子,年纪轻轻的我窥见了窗口死神宁静而恬美的笑容。我想抽身而去,可是笔拉住我,要我填满雪白的方格。我自己宣判:“你终身苦役!”
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身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和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文学已然堕落为枷锁和断头台的颂歌,是朦胧的月光,为黑暗横行张目。那些肯定性的写作,为什么也肯定不了,惟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可耻和无价值。因此,我坚持否定性的写作,诚如加缪所说:“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于我们悲悯而高尚的生活表达了敬意。”
我的本科时代,过着清教徒式的刻苦谨严的生活,真有些辜负了未名湖的一池春水。我为被冷落的命运而感到幸福。“早无能事谐流辈,只有伤心胜古人”,我在旁人指认的“愚昧”中寻觅一种动人的诗意。这种诗意与那些吓人的真理无关,它仅仅是一些混浊不明的声音,它在沙漠的深处不抱任何乐观的情绪地呼唤着水源。它在我快要放弃的紧要关头匆匆赶来支援我。
那道闸门还在。鲁迅说:“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放孩子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我所做的,不仅没有比先生前进几步,反倒退却了几步——我必须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却无须放孩子们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不是我不愿意放,而是孩子们并不愿意跑。孩子们说,哪里都一样快乐。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见证》中曾形象地描述“鸡的心理”——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见眼前的那粒谷子,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对鲁迅而言,肩住闸门既是行动也是目的。我要做的,仅仅是肩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我无暇考虑。角落里,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手挽着手,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在说我的坏话的时候,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家伙才会显得如此亲热。
我的学长孔庆东在送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肩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明白学长幽默背后的机锋,可我不能像禅宗所说的那样“背不动,就放下”。
作品能够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仍将坚持为抽屉而写作的方式,这一写作方式由三只鼎立之足来支撑: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和边缘的姿态。为抽屉而写作,也就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而写作。自由是人类投身写作行为惟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写作及生活的目的只能是增加每个人身上和整个地球上都可能发现的自由和责任的总量。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在结尾给每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了某种内在的自由。
这样做,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我整理完这本书稿的时候,我真切地听见我的牙齿啃我的骨头的声音。
冠盖满京华,思人独憔悴。
自诩为思人的我,为抽屉而写作的我,走我自己的路。有朋友愿意同行,我不拒绝



![太子与妖僧[重生]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7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