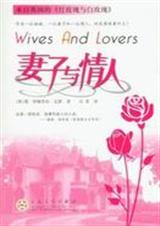铁屋子与窗户-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如光明的定义只有在黑夜中活了一辈子的海伦才能给出,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们所熟悉的光明黯然失色;美的定义也只有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这里没有烟火色、没有暴戾心、没有铜臭味、没有血腥气的文字,如冬日的阳光春日的雨。写作之于史铁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光荣,也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与残缺一样,是一种命运。
老子说:“大成若缺”。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这四个字的注释。
第一辑·口吃的人赤足之美
那一夜,在遥远的东京,在异乡的客栈,从绍兴来的少年客,偶然瞥见了奉茶的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足。从此,这名唤作乾荣子的十五岁少女轻盈而白净的赤足,像一片幽香扑鼻的茶叶,溶解在这个中国人心中。那一瞬间,意乱情迷的少年周作人朦胧地意识到,那是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那是一种纯朴率真的文化,那是一种活泼丰盈的生命,那是一种澄澈宁静的意境,那也正是祖国曾拥有过,却又不知为什么失去了的东西。若干年后,两鬓斑白、历尽沧桑的知堂老人依然动情地写道:“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船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中国女子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脚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代殊不可多得……”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变态的部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却没有学习中国缠足的文明,所以日本女性保存了天足。
重读知堂文集的今天,缠足的陋习已成为记忆之外的记忆,然而女子的天足又被塞进一双双又短又窄又高的高跟鞋里。大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总是一串串骄傲而艰难的步伐。象征着现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时尚的高跟鞋,再次留给女性一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爱恨交织的尴尬。步步生莲的梦想与“哒哒”的脚步声,与夜晚双脚麻木疼痛纠结成无法斩断的情结。在男性一次次绅士风度十足地回首里,赤足的美丽对于穿高跟鞋的女子而言,陌生得像一双檀木制成的书签,寂寞地夹在一本盛唐时代的线装诗集里。
其实,真正的美丽源于自然,真正的优美得于天成,真正的高雅源于天真。哲学拒绝权威的枷锁,艺术拒绝金钱的包裹,生活拒绝物质的栅栏;同样,天生之足也有理由拒绝装饰它、约束它、囚禁它、折磨它的或精致、或华丽、或玲珑、或绚烂的鞋与袜。“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千载而下,屈子兴之所至,赤足戏水的姿态,犹在眼前。这是一种生命张扬的人才有的情致,这是一种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声音,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生存状态。当云南边陲的一群傣家少女,穿着短短的筒裙,拎着小小的水桶,扭着细细的腰肢,赤着白白的天足,一溜烟穿行在小溪畔的石板路竹林间时,如画、如诗、如酒、如歌。任何一个巴黎的时装大师看见了,恐怕也无法进入这赤足的氛围中吧?
为美丽而制造的美丽,就好像没有灵魂浇灌的音乐,没有香味萦绕的鲜花,没有露水滋润的绿叶。而被财富奴隶的美丽,就好像古时候那位卖柑者筐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子。好多女孩把自己当作丑小鸭,以为有一双昂贵的高跟鞋以后,才能变成天鹅,她们却没有反过来想想:自己原本就是天鹅,何须以高跟鞋作为标签来命名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有设计师设计出了镶嵌满钻石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高跟鞋,谁有“福气”穿呢?)有个女孩说:“只有穿上高跟鞋,我和男朋友一样高时,我才有信心面对他和面对自己。否则,我觉得,在自己的心中和在对方的心中我都少了几分美丽。”有这样想法的女孩决不在少数,散步时走得气喘吁吁地咬紧牙关,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美其名曰:为美丽受难。
然而,因受难而产生的美丽仅仅是一个苍白的外壳。当一个男孩称赞你,“你的高跟鞋真漂亮”时,单纯的女孩你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了:他是因物而爱人还是因人而爱物呢?这双鞋穿在另一个人脚上,他会不会同样称赞呢?当你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时,你就找到了发现自己的窗户:只有自己才是世间最美丽那一部分啊!一双少女健美的天足,优美柔和的足弓、润泽的血脉、洁白的肤色、敏感的神经,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一件艺术品。
赤足之美,如池塘中亭亭的芙蓉,如竹林里悠悠的琴声,如陶壶内淡淡的茶香,如黄昏时柔柔的光晕。赤足之美,在春则为鹅黄的柳芽,在夏则为润泽的梅子,在秋则为静谧的弯月,在冬则为轻盈的白雪。赤足之美,却又在这一切比喻之上,连艺术大师罗丹也头痛地说:“塑像时,女性的赤足几乎令我无法复现万分之一的美丽。”因为每个青春女性的身体,都集中了山水的灵气、自然的精华、神灵的挚爱,而天足恰恰是长期被遮蔽的却又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一粒沙里见天堂,半瓣花上说人情”,知堂老人确实有颗慧心,有双慧眼,独辟蹊径地在一双赤足里找到了身体的神韵。一向温文尔雅的他,之所以辞严色厉地反对裹脚,斥之为恶习之源、贬之为民族之耻,这与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审美体系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那位年仅十五岁便开始辛勤地操持家务,既天真可爱又善解人意的日本女孩,可曾想到自己那双在榻榻米上款款而行的赤足,居然成了那位惶惑而弱小的坐在几案边的少年一生珍藏的财富?
最美的东西往往被过分聪明的我们忽视、遗弃或者加工、雕琢,而加工、雕琢得面目全非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苦苦向往的却常常是美的反面。手术刀下出现的双眼皮、嘴唇上如鲜血淋漓的口红、比皮肤还厚的脂粉,以及挂着沉重的耳环的耳垂,佩着金光灿灿的项链的脖子、戴着晶莹的玉镯的手腕,这一切都是时尚给“美女”一词所下的定义。然而,“时髦”究竟是美丽的近义词还是美丽的反义词呢?女性对高跟鞋的执著究竟是一种勇敢还是一种软弱呢?对那些穿着高跟鞋艰苦地在人流里穿梭的女性,男性又该负多少责任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了,于是,我们就像一只鲜艳的气球,在半空中为自己的美丽洋洋自得,却不知道自己占据的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空洞。在这样一个包装泛滥的时代里,不管是穿高跟鞋的女性,还是不穿高跟鞋的男性,都该读读知堂老人的那些一天天被忘却的文章。
感谢冰清玉洁宛如出水芙蓉的乾荣子姑娘,她留给知堂老人那代人的,绝不仅仅是一双“白如霜雪,不著鸦头袜”的天足。
第一辑·口吃的人九种武器(1)
古龙在名著《七种武器》中说,真正的武器其实并不是杀人的兵刃,而是诸如微笑、诚实、信心、爱情这些生命质素。我同意古龙的这一说法,我也有自己的“九种武器”。
——题 记
天 真
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佳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那种淡得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三分。阿佳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她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三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的、不施粉黛的阿佳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和儿子的意见。显然,三口之家口味不同,阿佳妮便建议“我们举手表决吧。”表决前她与儿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二比一胜利了,做母亲的她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起来。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佳妮艺术魅力之所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认为,国内的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天真”。如刘晓庆、巩利、姜文等人的表演,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与记者聊点家常话,他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
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望“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灵魂飞翔的翅膀。我很少读中国的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斐雯的诗,顿时被她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
为了让你相信!
我们真的可以拥有
一座地球花园
请原谅
我不让你摘花。
——《地球花园》
我也喜欢鸟
不过
比你贪心一点
总共拥有几万几千几百零几只
统统养在天空里
——《养鸟须知》
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
都在送医途中
不治而亡了
——《失眠》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斐雯是一个天真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带着执拗和倔强。在《地球花园中》,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诗句,而不是竖着大煞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鸟时甭提有多自豪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失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斐雯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
诗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缪斯便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履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的人间。
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曾经摘译过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的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的一面,而忽略了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出“活的中国”来。鲁迅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往往有一股温热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惘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引用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鱼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触角,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



![太子与妖僧[重生]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7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