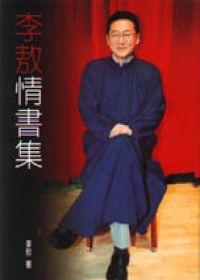838-李敖这个人-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寄款预约订书。李敖在9月13日给同学的信中说:“我这阵子收到的读者来信也不知有多少,几乎封封都提到牛肉面如何如何,几乎投资或帮忙我卖面的人,比要买我的书的人还多。真令人啼笑皆非,惊喜交集也!”在《文星》时代与李敖来往甚多的著名作家余光中亦在信中给李敖打气: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面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惟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面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①
李敖的《告别文坛十书》自然又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新上任的《文星》总编胡汝森(军方人物)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瑾中校多次会面磋商对策。
在广告登出后,接着就是印刷出书。印刷“十书”的装订厂不断遭到警方的干扰,装订好和未装订好的书籍相继被警方查禁、抢走,眼看“十书”无望,1966年11月15日,李敖在悲愤之中向约订读者发出“敬启”:
敬启者:
“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出版经过,奉陈如下:
第一号“乌鸦又叫了”
第七号“孙悟空和我”
两书已被查禁并扣留,不能发行。
第二号“两性问题及其他”
第四号“李敖写的信”
第五号“也有情书”
第一○号“不要叫罢”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4)
四书仍在处理中(发此信后,旋遭查扣,不能发行)。
第三号“妈离不了你”
第六号“传统下的独白”
第八号“大学后期日记甲集”
第九号“大学后期日记乙集”
四书已经发行(但受警察干扰)。
四书中有割页部分,并非装订错误,恕无法调换。
未出各书正依法处理中,一俟解决,即行奉上。总之,此次出书一再好事多磨,皆因情非得已。凡不细昧实际困难,而遽以“不准时”、“不守信”责怪李敖者,非知我者也。
李敖 敬上 1966年11月15日
就在四面楚歌、前路维艰之时,也有人想利用李敖的才气发财,依然向李敖拉稿,并要他化名写文章,李敖为之动气。他认为,这些人实在太不了解自己了。五年来,自己什么时候化名写过文章?大丈夫是从来“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的,自己反共也好,反法西斯也罢,乃至反义和团也行,从来不藏在后头放冷箭。自然,他拒而不应。
也就是在这时,他过去的论敌们依然未忘记他,胡秋原等人利用他们取得的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开始对李敖进一步围剿。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5)
1966年11月7日,胡秋原等邀约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30人,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李敖故友徐高阮因过去对李敖的一些做法不满,与李敖疏远,此次会议,他也参加了,并当场油印公布了李敖在新店山居时给胡适的信。因信中谈到了李敖与共党分子严侨的关系,徐高阮称李敖是“对敌人投降的叛逆分子”。
原来,李敖在给胡适的那封信中,透露了他与严侨的交往。由于信中还有评论胡适的文字,与严侨的信也写得非常感人,胡适便经常把信拿给别人看。当他把这信拿给“中央研究院”的徐高阮看时,徐高阮却将信扣在自己的手中。不久,胡适去世,此信遂归徐高阮所有。
徐高阮的这种做法后来受到许多朋友的谴责,说他“卖友求荣”、“借刀杀人”、手段“卑鄙”。但李敖的反应却很冷静,他说:“徐高阮等公布我的信,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信是我写的,我当然大丈夫敢做敢当。总之,我不怪他们公布我的信,我只是对他们公布的动机和目的,感到要吐口水而已。”“徐高阮等是变节的共产党,变节的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类……”①
不料,此信引起了政治嗅觉灵敏的胡秋原的重视。11月16日,声讨会后的第九天,胡秋原即在《中华》杂志第4卷第11号(总第40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徐高阮先生公布的胡适先生收到的一封信》,指控李敖是共产党的“间谍”,给李敖送上了一顶红帽子。于是,李敖致胡适的信,从论敌手中公之于世。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6)
警方和“司法机关”秉承当局的旨意借此机会迫害李敖。1966年底,由保安处魏宜智组长主持,警务机关开始约谈李敖,重点追查他18岁时想和老师严侨一起偷渡回大陆的事。严侨再度被捕,被关了30天,调查他同李敖的关系。不久,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指令侦办李敖,并以“妨害公务”罪名提起公诉。李敖被警备总部约谈,俨然一“匪谍”。约谈后由特务陪同,让李敖去找保,李敖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梁实秋。应该说,老牌的自由主义文人梁实秋对李敖是厚爱的。李敖的《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有《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对他十分捧场。文中说,“李敖的《胡适评传》不是属于亲切细腻的一类,而是属于证件充足(highly documented)的一类……像这样旁征博引的句句有来历的传记,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作”。②当时李敖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包括余光中、梁实秋无不称颂,多有文章在《文星》发表。与胡秋原论战时,梁曾以金门名酒两瓶赠送李敖。李敖也善解人意,特请萧孟能买了当时艺坛走红的柳腰明星华怡宝的专场入场券送梁,老先生欣然前往。谁知“文星”被封后,梁怯于官威,也与李敖划清了界限。当李敖找到梁实秋谈及作保之事时,梁实秋当着特务的面婉为谢绝,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最后,李敖在无奈之中又找到了他父亲的同学、“立委”王兆民,这位过去数次未帮上李敖“大忙”的善保“晚节”的前辈,终于有了一次“怀直气”的行动,他保了李敖。
当天晚上,梁实秋给余光中打电话,说未能保李敖感到很难过。李敖得知后,只是笑笑。他想,在自己身处逆境时,让正人君子援之以手,只是一种奢望而已。
其实,就梁实秋的处事原则和与李敖的非凡交情而言,他应该对李敖施以帮助。此次的婉拒,可能是他过坏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感到若出面作保,不仅难以保人,而且难以自保,故有此下策。李敖把梁实秋此举看作是软弱和爱惜羽毛,实在是冤枉梁实秋了。25年后,他从出版的《王世杰日记》中得知一段梁实秋为自己游说的秘辛:还是在他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时,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于是他未征得李敖同意也没有告诉李敖,便秘密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希望能任用李敖。王世杰在日记1965年12月20日条下写道: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7)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五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此言自然不对,因为李敖对此事根本不知。真正的原因倒是王世杰等人惧怕胡秋原。当时胡秋原正与李敖打着官司。在1963年9月10日日记中,王世杰曾写道:“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等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可见王世杰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是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说李敖“品行不端”只是一个假托而已。从这段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梁实秋的识才、惜才、荐才的气度。
由于李敖与严侨之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并且,负责调查的魏宜智精明能干,在调查中他搞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李敖,对官方不利,最后决定不了了之。徐高阮等人的阴谋才未得逞。
直到1967年,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部长郑彦亲自下令“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文侦办李敖。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李敖的行踪开始受到监视。
虽受监视,李敖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相反却在加紧备战积聚力量,以作下一轮的冲锋。他在给文友丁颍的信中说:“旧式文人,一遭困顿,即发之以长吁短叹;我们新时代的动笔杆朋友,却不可如此。鼻涕眼泪,唉声叹气,伤春悲秋、吟咏讴歌等等,都是狗屎。我们要形成的是力量,大力量。‘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清朝学者的老话,‘自大其身’就是制造力量,大力量。否则只是自怜而已,看水中的自己或女读者信中的自己又有何用?”①为此,他在1966年5月16日的日记里,给自己写下十条“我的信仰”: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8)
(一)我深信一种强者的哲学,我拒绝做弱者。
(二)强者的条件是智慧、力量和狠心肠。
(三)要有洞彻人际和知识上科际的智慧。
(四)要有打击坏人和恶势力的力量,要有散布智慧和善行的力量。
(五)这里面有一种“中间因素”,可叫做感情的干扰,它包括女人、亲情、朋友和世俗的道德标准,它们可能构成一种重大的阻力,阻止我发展我的强者哲学,我必要时铲除它们,所以我需要狠心肠。
(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七)“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讨个什么!”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八)“一个人为真理常常要牺牲朋友”,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九)深沉有力量,英气盖华场。这是强者的气势。
(十)“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我要求我在矛盾的关口,砍掉它们,义无反顾。强者不该是矛盾犹豫的人。
李敖以非凡的勇气迎接着黑暗的到来。
他预感到一张黑色的大网正一步一步地从天而降,笼罩住这个小岛。在这张无所不能的大网下,文星书店及其同仁自然难逃厄运。
第四部分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1)
二、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
在“文星”时期,由于主张“西化”的几名学者如李敖、许登源、居浩然、陆啸钊、李声庭、洪承完等人都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在台湾大学曾大力宣传、介绍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潮流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并且猛烈批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此,他便被反对西化的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想当然地指斥为西化派的总后台。
殷氏虽然并未介入这场中西文化论战,但他反专制、反独裁的立场和揭露国民党官局黑暗的文章却一步步惹恼了当局,加上他与爱因斯坦、罗素、费格、海耶克等世界第一流的大脑袋通信不断,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增大,他为狭隘的国民党所不容就在当然之中。尤其是李敖文笔犀利,咄咄逼人,颇与殷海光相近,在初出道时曾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殷海光的“化名”①,因此,从李敖身上往往能勾起官方的一系列接近联想。蒋介石在国民党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说:“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到‘反共复国基地’来后,完全变了。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这无异是对殷海光进行全面迫害的一个信号。
到“文星”后期,随着官方对殷海光打击力度的增强,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更是把殷海光和“文星”绑在了一起。前已述及的侯立朝在《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中列有一表:①
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毫无根据的罗织,把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新老自由主义文人摆在了一张平台上。以至文德先生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替殷海光抱屈说:“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敖与殷海光——这位同样狷介的学界前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已有述,李敖在大学阶段就与殷海光有过交往,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和李敖对殷海光认识的的转变而中断。
还是在1961年11月的一天,李敖独自徜徉于文学院中,与殷海光不期而遇。两人虽然多年不见,但这位自由主义大师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