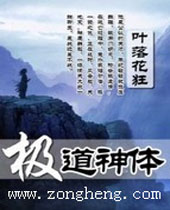时髦的身体-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塔兰特1994)。从这些文献中还涌现出文化与社会史的研究如布鲁瓦德(1994)、德·拉·哈耶(1988)以及霍兰德(1993,1994),他们的研究试图对时尚的文化语境作出一些分析,另外还有泰勒和威尔逊两人(1989),他们考察从维多利亚时代直到现代的衣着风格,主要兴趣在于研究“普通”人是怎样穿着的。有关时尚的文献的更进一步的分支包括对于时尚系统的经济与技术方面作出历史的和当代的勘察(参看利奥波德1992,法恩与利奥波德1993),还有查普吉斯和恩罗(1984)、科伊尔(1982)、埃尔森(1984)、菲泽科利(1990)、罗斯(1997)诸人的研究,他们的兴趣主要是考察时尚系统中那些从事血汗劳动的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文化研究还探讨当代的时尚系统(阿什和赖特1988,阿什和威尔逊1992,戴维斯1992,克雷克1993)。另一些人则研究时尚呈现的本质(布鲁克斯1989,伊文思和桑顿1989,刘易斯1996,尼克松1996)。这些研究工作一直由一些理论的视野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分析(利奥波德1992),结构主义(罗兰·巴特1985),语义学(海布迪基1979),精神分析学(弗吕格尔1930,刘易斯和罗莱1997,尼克松1996,西尔弗曼1986),社会心理学(所罗门1985,车龙1997)以及后结构主义(恩特维斯特尔1997a,1997b;尼克松1996,威尔逊1992)。
我想探讨的是这些学者在研究时尚时所采用的多样化的研究进路。超越这些文献所隐含的学科的界限,我们可以重点考虑三种研究进路,它们并不取决于学科的分野,而是取决于它们所提问题的类别以及他们所采用的理论策略与方法论取向。第一种进路是以提出诸如人为什么要穿衣服这类问题为出发点的,其实这种问题只能将人们引向过于简单的答案。上述文献中蕴涵的第二种研究进路则试图提出更加精密而周到的分析,其兴趣中心在于探索时尚与“现代性”的关系。尽管它们所研究的范围相当宽阔,但是上述两种研究进路并没有提供一种对于时尚在日常衣着中是如何“被经验到”以及如何“被实践”的那种具体的考虑。它们所提供的对于时尚的理论形态的探讨,结果只是对于作为实践活动的“衣着”的忽视。另外它们也没有考虑到时尚和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只是把时尚当作社会的与交流的现象来对待,而没有把时尚当作一种身体现象来认识。第三种研究进路更少考虑理论形态的解释而更多研究一种文化中的特殊的衣着实践。对于实践的关注可以从近来的一些人类学著作中看出来(巴恩斯和艾彻1992,弗里曼1993,胡德伐1991,韦纳和施尼德1991),这些作者研究的是文化蕴涵、意义以及围绕装饰品的衣着实践;也可以从一些社会心理学的著作中看出来(卡什1985,埃里克森和约瑟夫1985,车龙1992a,1997),他们考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他们的衣着打扮具体在干什么以及在表明什么意思。不过,它们在研究西方社会的时尚系统时,仍然只有有限的启发价值。
理论进路一:追问“为什么”以及它们的答案
对衣着和时尚早期的解释(也包括许多当代的考察),都倾向于以追问“为什么”为出发点:为什么我们要穿衣服?他们可能还要追问时尚的本质:为什么时尚系统要建立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基础上?时尚为什么这样变幻莫测?为什么在男人和女人的时尚之间会出现那么多的不同?对这种询问“为什么”的提问方式略加考察,我们就可以揭示出时尚是如何被纯粹理论化地把握的,也可以阐明关于时尚的思考是如何走向简单化道路的,“为什么”这种思考所提供的关于服装和时尚的理论在追求某种无所不包的解释时会无一例外地犯下过分简单化的毛病。这种追问“为什么”的思考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复杂的时尚系统简单化约为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导致过于决定论的和简单化的解释。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1节 对于衣着和装饰品的理论解释(1)
我们为什么要修饰自己?人类学对此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保护、羞耻、炫耀和交流,每一种解释都比前一个更加具有排他性。巴纳德(1996),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以及劳斯(1989)对这些不同的解释作了很好的概括,并且开始注意到19世纪后期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影响,马氏提出了一个更加狭隘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穿衣?一种回答是,人类有许多基本的需求,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是保护身体免受外物环境的侵害。不过,这个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并不穿衣服;而且诚如劳斯(1989)所指出的,没有那么多来自衣服的保护,许多人也能够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下来。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某种着衣方式都是可以见到的:比如,穿得很少(很暴露),目的是为了赶时髦,这些衣服的主人们很少顾及冰冷刺骨的气候。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以及罗斯(女)(1989)因此认为,“保护”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西方、传统以及非西方的文化中,都有许多着衣的风格是不实用的而且往往会导致身体的不适。
第二种解释是羞耻说:穿衣是为了遮盖性器官。不过,人类学的证据表明,并不存在普遍的羞耻观,感到羞耻与否,不同文化的情况很不相同,这就使羞耻感作为一个基本的解说大大地成问题。正如罗斯(女)(1989)所说,羞耻和害羞是和不同的社会语境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方面的文献也追问过我们为什么要穿衣并且已经运用心理学的实验来寻找答案。弗吕格尔的著作(1930)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他并不拒绝保护说与羞耻说,但是他认为第三种解释可能更加有意思,即穿衣是为了装饰和炫耀。衣着并不仅仅是发出性的信号而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加有性的吸引力。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弗吕格尔进一步提出,衣服表达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既是羞耻感的表现,又是炫耀欲的实现,他还认为衣着本身(比如男子的领带)就可能是性器官的象征。他认为衣服就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矛盾心理,这种解释又促使他认为“衣服的穿着在其心理学方面看来好像类似于神经病症状产生的过程”(弗吕格尔1930:20)。对于弗吕格尔来说,衣服就是“人性表面常年不退的羞红”(1930:21)。第四种解释是穿衣为了装饰,装饰欲来源于人类利用象征物来交流的一种普遍的天性,这种说法目前已经成为一种颇具势力的理论构架而为研究服装的人类学家和特别关心时尚的理论家们所接受。鉴于它的巨大的影响力,认为时尚/衣着是为了交流的说法,我们下面还要更加详细地加以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首先要考察几种解释时尚的理论。
对于时尚的理论解释
有许多研究时尚史的著作试图找到对于时尚的一种理论解释。这些文献试图将时尚解释成一种特别的衣着系统并试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衣着系统,它们可能还会提出时尚为什么会变动不居之类的问题。对于时尚问题喜欢追问“为什么”的习性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由19世纪晚期人类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著、1899年初版、1953年重新发行的《有闲阶级的理论》一书中尽显无遗。事实上在他的理论中含有两个“为什么”,第一个是:为什么会存在时尚系统?他的答案需要从特定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人们也许会说,他的回答所告诉我们的有关19世纪末的时尚远远多于有关今日时尚的意义。凡勃伦是从他认为特别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特征的角度来解释时尚的意义,他认为,新的中产阶级是把时尚当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手段来采用的。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惹人注目的消费、惹人注目的浪费以及同样惹人注目的闲暇来表示他们的富有。既然时尚没有什么实用性,这个阶级中的许多成员就拿时尚作为一种手段,来显示他们和处处讲究实用的那种比较低级的生活方式的距离:只有有钱又有闲的人才敢在衣服还没有穿旧之前就把它们扔了并且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衣着是表达金钱文化的一个最好的实例,因为“我们的外表总是容易被人家看见,而且总是向第一眼看到我们的那些观察者们透露有关我们的经济状况的消息”(凡勃伦1953:119)。凡勃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时尚总是那么不讲道理地变动不居?他认为人们对于惹人注目的消费与浪费的需要应该可以解释时尚为什么需要一刻不停地变化。不过,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答案既不能解释人们对于风格的变化的制造与接受,也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得不顺应时尚的变化。对此他并未作出什么更好的解释,反而进一步认为铺张浪费是人类的天性所不喜欢的,这就使得时尚的不实用和昂贵的代价令人讨厌,让人们不觉其美,反觉其丑。因此他主张,可以把时尚运动以及人们对于时尚的趋之若鹜解释为我们企图逃避时尚的无聊与丑陋,我们凭借每一个受欢迎的新的风格来逃脱此前的花样翻新,而在此过程中时尚变化所包含的无益和浪费,也受到了拒绝。
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女性的服装比男子的服装更加展示了这种时尚演变的动力机制,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所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显示她的主人的购买力,以及他的足以把她从工作场所整个儿解脱出来的经济力量。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考察实际上把妇女看成是这个阶级的从属的成员(他比较了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和家庭仆佣的角色之异同);她们只被动的存在或者是“‘男人’的动产”,而她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则是这种角色身份的最好的证明。女性的服装和时尚联系得最紧密,因而也就是中产阶级可以用来大张旗鼓地消费和赶时髦地浪费的一种手段。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们的服装也是这种替代性的闲暇的重要证据。中产阶级女性的穿着打扮明显说明她们是不适宜于工作的——做工考究的呢帽、沉重的裙裾、精致的皮鞋和包得严严实实的紧身胸衣——
这些都是她们远离生产劳动和有闲有钱的证明。凡勃伦谴责这些时髦的服装而提倡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服装,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使我们很容易想起许多服装改革者们的主要思想(这方面的概况参见牛顿1974)。
凡勃伦的理论也颇多可议之处。他考察时尚与时尚的变化是基于“仿效”的观念(下面以及在第三章将详细讨论这一理论的局限)。他分析中产阶级女性时完全抹杀了她们的主观能动性:时尚在他的表述中被想像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活中一种决定一切的否定性力量。与之相反,孔茨尔和斯蒂尔两人都提出了与凡勃伦很不相同的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与时尚之关系的见解,修正了将紧身胸衣看作是压抑女性的那种标准的有关时尚的故事(凡勃伦1953,罗伯茨1977)。斯蒂尔的研究开始注意到时尚中肉感炫耀的成分,她认为传统上关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只是在性与社会方面的受压抑者的想像“需要从根本上被修正”(1985:3)。相反,她坚持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时尚与当时的女性美的观念有关,在这种女性美的观念中,肉感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1985:3),因此在这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尚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认为的更多的延续性。孔茨尔(1982)比这种说法更进一步,他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穿紧身胸衣并非她们的奴从地位的象征,相反,那时候凡穿束紧腰围的外衣的女性都在性和社交方面具有强烈的自信。孔茨尔和斯蒂尔两人都把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看作是积极的主体并都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穿着为依据来佐证他们的观点(尽管斯蒂尔不赞同孔茨尔用束紧腰围的外衣来做例证从而将这种外衣和当时对紧身胸衣的盲目崇拜混为一谈,她认为孔茨尔在这里也同样犯了夸大性欲效应的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凡勃伦关于女性和服装之关系的考察,即使曾经盛行一时,现在也已经成为过去了。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那样(恩特维斯特尔1997a;1997b),随着女性进入职业领域,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生产/消费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也发生了转换,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和消费领域。随之而来的转换还有与女性衣着有关的事物。就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演员和拿工资的人一样,职业女性也已经不再是“‘男人’的财产”了,而她的衣着也不再和展览替代性的闲暇有关了。女性进入正式的职业领域,其结果就导致了另一种女性服装的出现:它也许“不合适”但确实是讲究“合理”,至少其主要目的是让女性能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不再为繁缛的故意强调女人味道的服装所牵累。
尽管凡勃伦的观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很好的例证,它的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其他一些研究时尚的理论家的著作中找到凡勃伦观点的痕迹。正如威尔逊(1985)所指出过的,一般说来,凡勃伦的论点很少受到来自其他的时尚研究者的挑战。这也许和如下的事实有关:凡勃伦毕竟是当时极少数几个认真对待时尚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对凡勃伦著作的一种同情的解读来自贝尔的著作(1976),尽管贝尔在他的分析中很少提供有关时尚的否定性描述,他也绝不谴责时尚是丑陋或非理性的。类似的论辩还可以在博德里德(1981)的著作中看到,博德里德说:
时尚在全然无视美的基础上不断地捏造着“美”,其方法就是把美化约为它在逻辑上的对等物即丑。时尚可以强迫人们相信那些最离奇、最无用、最荒唐的东西是最有特色的东西。这正是时尚的成功之处:它按照比理性更深刻的非理性的逻辑将非理性合法化并强加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