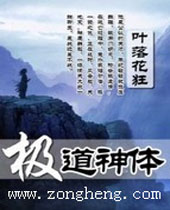时髦的身体-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于使衣着的线条更加流畅,身体的曲线也更加能够显露出来。
因为荷兰和法国逐渐成为互相制衡的超级强国,在法国宫廷与荷兰的布尔乔亚中间就分别出现了两条时尚演进的路线。荷兰把西班牙的黑白分明的天主教风格带进了下一个世纪——这种风格通过遗传作用渗透进了基督教新教、布尔乔亚和城市的风格,以适合加尔文教派的意识形态(斯蒂尔1988)。这种风格还延伸到19世纪,成为整个欧洲的布尔乔亚的“制服”,也是意在纠正贵族阶级铺张浪费的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荷兰的节俭严肃的风格继续统治着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在17世纪中期,法兰西宫廷却作为时尚的一股强劲势力出现了。路易十六宫廷将法兰西确立为欧洲显贵中间最高的时尚领导者,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期。路易十六虽然6岁登基,但是“当他成年时,他把整个法兰西引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豪奢辉煌的时期,巴黎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时尚的首都”(布拉德利1955:193)。豪华、奢靡、精致,以及面料和色彩的出色华美,造就了凡尔赛的风格,这不仅在出入宫廷的显贵们在衣着上体现出来,而且凡尔赛宫本身的建筑与内部装潢就是最好的说明。因其刻有太阳与蛇的徽章而得名的“太阳之王”路易十六,使人们意识到了衣着的象征意义。早在1665年,他就认识到时尚对于法国工业的重要性:他千方百计保护法国的纺织业免受在争奇斗妍的时尚工业上足以与之匹敌的意大利和荷兰的冲击,他还特别鼓励法国的丝绸纺织业去和意大利的竞争(斯蒂尔1988);对外国进口的纺织品与贵重金属课以重税同时竭力帮助法国的制造业,这种政策倾斜无疑大大刺激了法国的时尚工业的发展(亚伍德1992)。不过,正如斯蒂尔所指出的:“单单经济现象并不能解释当时国际化的西班牙式的凝重风格被法兰西的流行时尚所取代的原因。”(1988:23)斯蒂尔认为,比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法国宫廷的力量——因为1660年路易十六和西班牙公主玛利亚·特雷萨的结婚,法国宫廷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而带动了17、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的极度辉煌。与此同时,黑白分明的衣着风格仍然在欧洲其他地区——尤其在西班牙贵族以及荷兰与英国的清教徒中间——占据统治地位,路易十六宫廷发布的节制个人消费的法令也一直控制着时尚的蔓延,并且建立了各种复杂的仪礼法规:人们的衣服必须接受严格的限制和一定之规,比如,金和银的装饰品,只能由王室成员以及一部分受到特别宠幸的侍臣佩戴。尽管有这些严格的法规——
尽管这些法规事实上也的确放慢了时尚的变化的步伐——法国宫廷的风格还是被整个欧洲所模仿。在那些时尚杂志出现以前的年月里,时髦的纨NB345子弟们作为时尚的“使者”到处传播着最新的宫廷时尚。
宫廷的衣着风格过于精致,过于讲究形式,而且往往变化缓慢;与此不同,在巴黎城里出现了一种具有更加真正的现代气息的时尚潮流(斯蒂尔1988)。成千上百的裁缝日夜辛劳地为宫廷制作服装,但是到路易十六的统治行将结束的时候,年轻的小姐和贵妇人逐渐厌倦了宫廷风格而钟情于发源于巴黎的新风格。斯蒂尔记述了1715年的某一个场合,德奥林斯公爵夫人和德·孔蒂公主怎样向路易十六进献来自巴黎的最新时尚而获得了路易十六的首肯。在国王驾崩的那一年,时尚业已经发展到了由女士小姐个人和制衣匠们说了算的程度,而这就大大加快了时尚发展的步伐。不过,因为有德·蓬巴杜夫人、迪·巴里夫人和后来的玛丽·安托瓦妮特一直为法国宫廷以及其他欧洲宫廷的贵族衣着充任时尚的领军人物,法国宫廷还是保持了它的巨大影响力和惑人的魅力。法国,特别是巴黎的时尚,直到20世纪中期仍然保持
第三部分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第20节 18世纪的衣着,阶级和身份认同(1)
与16和17世纪的宫廷社会相比,19世纪的社会在风格上是不断的城市化。伦敦在想像与创造的领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非常自然地:“有十分之一的英国人生活在伦敦,有六分之一的英国人工作在这个大都会中。伦敦比英国其他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大10倍以上,它使英国所有的大都市都相形见绌——到了18世纪中期,伦敦的常住人口已经接近75万之众,是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布鲁尔1997:28)18世纪是一个社交活动异常发达的年代,那时候城市“发展出了不受宫廷控制的相对独立的社交网络,在这个社交网络中,你可以经常见到陌生的面孔”(森尼特1977:17)。你可以在巴黎和伦敦的游乐园里、在专门为步行者建造的新的街道上或者在星罗棋布的咖啡馆里,和别人会面。尤其在咖啡馆里,你可以消磨几个钟头,阅读、聊天或者只是看看别人。像闻名遐迩的伦敦辉格党人和文人经常聚集的基特·卡特俱乐部那样的咖啡吧俱乐部在1690年至1720年之间生意十分兴隆,这种俱乐部赞助关于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定期讨论会(布鲁尔1997:40)。约翰·布鲁尔注意到,“基特·卡特俱乐部代表了18世纪初期发生的从宫廷到社会、由艳俗的宫廷侍臣向彬彬有礼的城里人的转移”(1977:41)。这种转移可以从由戈弗雷·克内勒引进到英国的画像风格中看出来,他创作了许多基特·卡特俱乐部成员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你闻不到一点宫廷画像自我迷恋的味道;画家所画的都是一些忙于社交活动的男人。”(1997:41—42)
因为城市居民的数目和住在外省小城的高贵而有教养的中上层阶级一样急剧增加,“社交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众口谈论的对象。“社交界”的成员走出家门,可以去会见别人、散步兜风或者购物;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大,从公园、游乐场——比如伏克斯豪尔(Vauxhall)或拉内拉赫(Ranelagh)游乐园——到剧院、展览会、大商场或者在全国各地的礼堂会所举行的各种化装舞会与正式的盛大舞会。这些社交场所都有各自的“季节”——住在外省的中上阶层人士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交日程表在不同的时间访问伦敦与英格兰西南部著名的温泉城市巴思。尽管这些社交活动最早只是一小撮特权阶级关注的中心,像散步兜风这样的活动也一度只是精英人士的赏心乐事,但是在大城市却已经成了靠工资过活的劳动者的消遣节目;又比如剧院,曾经是少数人才能涉足的娱乐场所,但现在已经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的观众开放了(布鲁尔1997)。正如布鲁尔所留意到的,一个人参加这些文化活动的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他有没有钱购得一张入场券,而取决于他看上去是否“体面”。
随着财富的增长,消费模式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18世纪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布鲁尔1997,布鲁尔和波特1993,坎普贝尔1989,麦肯德里克和其他一些学者1983,斯莱特1997,韦瑟里尔1993,1996)。随着收入的增加,“似乎许多人都有可供任意支配的盈余;因为这种收入被转化成消费的需要,所以就刺激了制造业的生长”(波特1990:205—206)。大宗的商品购买似乎已经超出了必需的范围:亚麻布的桌布、银器、陶器、钟表和家具,以及个人装饰品如女用呢帽、女用阳伞、手帕、手套、香水、手表。消费品领域的扩大,加上“社交界”的扩张,就为个人向社会展示自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观众在公共场所“当众展示他们的财富、地位、社交与性的魅力”(布鲁尔1997:69),而新的耐用品的消费也成为传达这种魅力的最普遍的方式。
在这个时期,仿效说的理念被社会理论家们所采用并且由此成为他们在考虑18世纪的消费革命时经常依靠的解释模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请特别参见麦肯德里克等人的著作,1983)。仿效说认为,时尚最初发源于社会阶梯的最高层,然后才往下渗透,因为“下层”企图照搬或仿效他们的“较好的东西”而消费起精英阶层的时尚来。仿效被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道德家们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因为据说这种下层对上层的仿效打乱了自然的或宇宙的普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的社会地位是老天注定的。现代商业社会扫荡了旧的农村社会的秩序,并带来了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新的资源——人的地位不再靠继承土地的多少与血缘的贵贱,而是靠你所拥有的金钱的多寡了。
新的社会集团——商人、工业巨头、新的中产阶级——有钱去购买“超出他们的地位的”、以前只能为国王和贵族所独享受的那些奢华的东西。在守旧的传统主义者的眼里,这些都是“邪恶的化身、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正常秩序的反叛与蔑视,因而反映了道德、精神和政治的腐败”(斯莱特1997:69;另外请参看塞科拉1997)。对奢侈浪费的议论,对奢侈品消费的控制,说明当时的上流社会是在面对社会与时尚的变化时很想维护阶级与地位的原有界限。虽然整个社会的竞相仿效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是社会的邪恶现象,是社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但事实上现代人的情感基础却由此得以形成。亚当·斯密认为(见斯密著作1986)仿效是现代美德发生的源泉,因为正是通过现代人对于财富和地位的自私自利的追求,全民的财富才得以增长。而且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仿效还在人民中间激发了更大的同情和更加活跃的社交。
各种各样的仿效说一直就是许多关于18世纪消费革命的讨论的理论支柱,而且它们也一直是人们理解18世纪以后的时尚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框架。对斯莱特来说,仿效并不单单是一种理论,它还是现代性语汇的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一种先入之见”(1997:157)。仿效的理念还作为“滴入说”的理论模式而广为人知,许多不同理论背景的理论家们都提出这种理论模式来解释18和19世纪时尚的急剧扩张现象(麦肯德里克等人1983,麦克拉肯1985,凡勃伦1953),布罗代尔(1981)甚至还把它和时尚在14世纪的起源联系起来。凡勃伦(1953)和西美尔(1971)是最常被引用的这个理论框架的提倡者,而他们在各自的理论研究中都喜欢以时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仿效说因为提供了关于时尚与时尚的变化的一种简单明了的理论说明而流行至今。然而,作为一个概念,“仿效”一词是很成问题的。问题之一在于,这个理论把太多的假说建立在太少的乃至根本就没有的事实根据之上。(何谓“人的天性”而且我们又如何能够把仿效认定为人的“天性”?)有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把仿效确立为消费冲动的根据是多么的困难,许多社会评论家们都喜欢引用这个“事实”来支持仿效说:年轻的女用人穿了她的女主人的华丽的服装。有些论者抓住这个现象不放,他们把穿着华丽服装的女佣看成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女佣想往上爬或者希望别人把她错当作一个阔太太的野心。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年轻的伺侯别人的小姑娘穿了华贵的衣服,也可能并不像18世纪那些社会评论家们想像的那样,是她的仿效其女主人的愿望的表现。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对当时的一些女主人来说,把“无用的衣服”扔给女用人是常有的事,而且这些礼物也可以看作是她付给女用人的工资的一部分(法恩和利奥波德1993)。其次,按照法恩和利奥波德的说法(1993:126),事实上女佣们经常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已故的女主人遗赠给她们的衣服拿到可以赚钱的二手服装市场去变卖,“她们更喜欢拿到(变卖‘无用’)所得到的现钱,而不乐意保存或穿着女主人的旧衣裳”,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女佣们仿效女主人的冲动实在是微乎其微”。柯林·坎普贝尔则认为,甚至当女佣们保存或穿着从主人那儿得来的衣服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这视为她们刻意仿效女主人的证据;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从她们仅仅穿了好看的衣服这一事实中臆测她们并没有表现出来的动机。坎普贝尔说,就算她们的动机在于仿效她们的女主人,我们也不能知道她们究竟在仿效女主人的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仿效。换言之,“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称一种行为是‘仿效性的’时,那仅仅是我们的理解过程的一个开始”(坎普贝尔1993:41)。正如坎普贝尔所指出的,一个女佣穿她的女主人的衣服,理由可能有许多种:
女用人要想在她的衣着的风格与豪华方面和女主人一争高低的动机,是否仅仅出于一种和女主人争着追赶时尚的愿望呢?或者这种动机是起于要和女主人在社会地位上平起平坐的野心呢?通过这种仿效性的行为,她是否要引起同样做用人的小姐妹们、她的家庭与朋友们、她的女主人、她在大街上随便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或者就是她自己的注意呢?这种竭力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的想法,是否对她的女主人的羡慕、想提高她自己的自重自爱的感情,或者仅仅起于她的赤裸裸地往上爬的社会野心呢?(1993:41)
在坎普贝尔看来,仿效说的漏洞在于它把动机和结果弄混淆了。上面这个例子还说明当我们从由一种理论所设定的一定的距离之外去解读别人的衣着时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论述的,各种有关时尚的理论都很容易将时尚从社会语境中抽象出来,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关于时尚/衣着的普泛性论述,而未能把这些论述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换言之,它们都是简单化的:在太少的证据的基础上作出了太多的假设。在这样的理论的把握中,时尚、衣着与复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身体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衣着实践的联系都被人为地割断了。其他对仿效说的批评则指出它对于社会阶级与社会地位的机械论的把握(斯莱特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