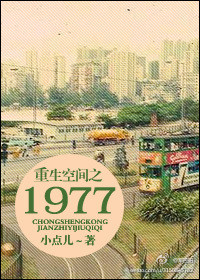4498-李宗仁回忆录(精选)-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于该团的历史,此地且略为补叙一下。原来在抗战开始之后,平、津、京、沪学校泰半停办。青年人请缨心切,纷纷投入军旅报效。我于1937年11月抵徐时,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学男女学生、教授、教员不下数千人。无不热情兴奋,希望有杀敌报国的机会。为收容这批知识青年,我便命令长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徐州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共有学员四五千人。但是当时中央没有这笔经费,我便商请广西绥靖公署汇款前来维持。经过短期训练后,毕业学员都分发至地方行政机构或各部队担任组训民众和宣传等政治工作,以提高军民抗敌情绪,成效颇著。徐州撤退时,在该团受训学员尚有两三千人,遂迁至潢川继续训练。各地青年来归的,仍络绎于途,朝气蓬勃,俱有志为抗战效死力。无奈为时不久,委员长忽有命令将该团停办。而陈诚所主持的“战干团”,那时却正开班招生,何以独独将潢川训练团停办,殊令人不解。然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办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训练机构,便无端夭折了。这批青年学生后来投效延安方面的为数甚多。
当长官部停留潢川期间,我原先撤往苏北的孙连仲、冯治安、张自忠、孙震、于学忠、李仙洲、庞炳勋等部,均已陆续越过津浦路,通过安徽,至豫东布防。敌军既陷徐州,即乘势大举西侵,因此也无暇顾及我撤往苏北的部队。因敌人的战略计划在于速战速决,企图西向席卷皖、豫产粮地区,同时掌握津浦、平汉两交通线,进而扫荡西南,逼我国作城下之盟。因此,敌人于6月5日陷开封后,便继续前进。6月9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于是,敌军改变进攻方向,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西进。6月下旬占我安庆,再陷潜山、太湖。敌人利用强大海军,旋又突破我马当要塞。再攻占我湖口、九江两据点后,乃兵分两路,一循南浔铁路攻马回岭;一在北岸小池口登陆,与太湖西进宿松之敌会合,陷黄梅,进攻广济。但鄂东地势南滨长江,北连大别山,无数河道由北向南,汇入长江。兼以其间遍地皆为稻田,地形又起伏纵横,形成天然的障碍防线,易守难攻。又兼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时向皖西和鄂东猛烈出击,截断敌军交通线,威胁敌军后方,逼使敌人屡进屡退,一筹莫展。敌我双方遂成胶着的状态。敌军为排除其战术上的困难,以达成其迅速占领武汉的目的,乃改变战略,另出奇兵两路,由大别山的北麓平原西进。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的固始、潢川、罗山、信阳攻击,企图于截断平汉铁路后,再南下攻击武胜关及平静关;另一路则由合肥攻入六安,然后直捣商城,再南向威胁麻城,与鄂东之敌相呼应,对武汉构成大包围的态势。在敌军发动新攻势前,我已向中央建议:自大别山北麓乘敌人防务空虚之时主动出击,威胁南路敌人的后方。无奈中央置若罔闻,致有后来之失,下章当再详叙。
《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武汉保卫战(2)
正当敌军溯长江西上陷落安庆之时,我右颊上于讨龙济光战役所受的枪伤突然发作。这一创伤自1916年以来,并未完全治愈。时有轻性发炎,旋又消肿,并无大碍。而此次发作则为最厉害的一次,右脸红肿,右目失明。不得已乃请假赴武汉就医,并将指挥职责交请白崇禧暂代。我由友人介绍,住于武昌有名的东湖疗养院内。此医院的资产,大半为张学良所捐赠,规模宏大,设备新颖。院长兼外科主任为一美国人,医道甚好。我即由他施手术,自口腔上腭内取出一撮黑色碎骨,肿痛遂霍然而愈。
东湖为武昌风景区之一。我出去散步时,常在路上碰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大家握手寒暄而已,听说他们的住宅就在附近。此疗养院环境清静,风景宜人。时值夏季,湖中荷花盛开,清香扑鼻。武汉三镇,热气蒸人,东湖疗养院实为唯一避暑胜地。因此李济深、黄绍竑、方振武也来院居住。这三人都和我有莫逆的友谊,现在朝夕聚首,或谈论国事,或下围棋,或雇扁舟遨游于荷花之中,戏水钓鱼,真有世外桃源之乐。而亲朋故旧前来慰问的更不绝于途,以致引起中统和军统特务的注意,派了一王姓女士来暗中监视。某次,陈诚来院访问,见我等数人正围坐聊天,彼半开玩笑地说:“诸公是否开秘密会议,可得与闻否?”大家相顾愕然,苦笑了之。由此可见中央当局庸人自扰的一斑。
我在东湖住了二十多天,鄂东、豫东战事已至最紧张阶段。第五战区长官部早已自潢川迁往蕲水,此时再由蕲水迁至宋埠。宋埠为黄陂县属一小镇,长官部即设于镇外一小庙中。我回到宋埠不及一旬,委员长曾亲来视察,为表示与前线将士共甘苦,并在小庙中住宿一宵。我只好将床铺让出,自己在庙中正厅办公桌上放一门板而卧。入夜蚊子太多,不能入睡,蒋先生睡在我的床上,虽有蚊帐,但也为蚊虫所扰,不能入睡,时时呼唤侍从人员入室将帐里的蚊子赶掉。可是越赶越多,整整一夜我们二人都未好好睡觉。
武汉外围保卫战发展至10月初旬,北线敌军已迫近信阳,另一部敌军已占领麻城,威胁宋埠。江北敌军正进逼黄陂,江南敌军也已迫近湘鄂边境。我五战区长官部乃自宋埠北迁至黄安属的夏店。
10月12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平汉路正面既让开,武胜关瞬亦弃守。战局至此,我预料平汉路以东的正规战已告结束。中央旋即明令,除大别山据点保留为游击基地外,所有五战区部队应悉数向鄂北撤退。为商讨据守大别山问题,我乃在夏店召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开紧急军事会议。我告诉廖、李二人说:“中央有令要保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你们二位中谁愿意留在敌后打游击呢?”李品仙默不作声,似乎不大愿意。我本人也觉得廖磊为人笃实持重,比较适宜于这项艰苦工作。我便问廖磊说:“燕农,你有没有兴趣留在大别山内打游击呢?”
廖磊说:“好得很呀!我愿意在大别山打游击!”
我遂派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内打游击。最初在我们想像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不久,中央又任命廖磊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当我任皖主席时,早已罗致了抗战前所谓“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财政厅厅长,整顿税务,颇见成效。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哪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1939年10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我乃呈请中央调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继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兼安徽省省主席,驻节立煌。至于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遗缺,则呈请调黄琪翔充任。
《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武汉保卫战(3)
10月中旬,我长官部复自夏店西撤至平汉线上花园站以西约十里的陈村。当我尚在夏店时,平汉路正面之胡宗南已不知去向,乃檄调西进至应城附近的覃连芳八十四军和刘汝明六十八军赶赴武胜关、平静关一带择要固守。不料我甫抵陈村,长官部的无线电台与刘汝明已失去联络。八十四军也被敌压迫,退守应城。该军与刘部虽相去不远,然亦不知其确切所在地。我绕室彷徨,焦灼万状,辗转反侧,至午夜犹不能入睡。忽然心血来潮,惊觉战况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通知长官部同人速即整装,向西移动。这时徐参谋长祖贻等都在梦中,忽被叫醒,都感到很突兀。祖贻问我道:“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我说:“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
众人也未多问,遂整队西撤。黎明后,行抵安陆县境,众人就地休息,忽发现陈村附近居民竟尾随我长官部之后,如潮涌而至。问明原委,始知在我们离开陈村后约两小时,敌骑兵千余人便窜入陈村。这批敌军的快速部队是否因为得到情报,知我长官部驻在陈村,特来抄袭,不得而知。但是当晚我如果不是因为心血来潮,临时决定离开陈村,则后果不堪设想了。当时我长官部同人得到陈村难民的报告后,无不鼓掌大叫。徐参谋长也把手一拍说:“昨晚要不是长官心血来潮,就糟了!”
这件小事使我想到中国史书上常常记载有某一重要事件,由于当事人一时“心血来潮”或“耳鸣眼跳”等所引起的奇迹,似乎也非完全捏造。
我们退到安陆后,武汉三镇也于10月26日为敌人窜入。武汉既失,抗战形势又进入另一阶段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1)
第五十五章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与随枣会战
武汉撤退后,我方主力部队都退往西南山区,抗战乃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不过,敌人因深入我内地,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势。故无力对我作全面进攻,只有对各战区不时作间歇性的战斗,但每次作战时期亦不能超过一月以上,真所谓势穷力竭、捉襟见肘了。
1938年11月间,我偕五战区长官部退至枣阳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该处,与我会商防务。李部所辖的第八十四军在应城一带突破敌人包围圈,到达随县。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自左翼退下,同时到达。我便命令两军在随县布防,以待敌军来袭。我长官部则暂设于樊城。因按军令部于武汉失守后的新规划,本战区现辖防地,计包括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向则敌后的大别山和皖北、皖西、鄂东各县也在本战区防地之内。故樊城实为指挥本战区内战事的最适中地点。
长官部到樊城后,我遂将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残了的部队约十余万,加以整顿,重行部署,准备向武汉反攻。这一时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能。
敌人固亦深知我方战略的重心所在,故视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为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大,日军四面受敌,暂时无足够兵力来扫荡我五战区,我们因而有充分时间来重行部署。而1938年岁暮,我们在樊城也能从容过年,未受敌军骚扰。
孰知正当敌人陷入泥淖,攻势日弱之时,我方阵营的悲观论者却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战,开始做投降的活动。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兆铭突然秘密离渝飞滇,前往越南的河内,并发表反对抗战、诬蔑抗战将士的文告。
汪兆铭的叛国虽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对抗战,我实早已亲自领教过。我在上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专诚去拜望汪先生,见汪氏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
我说:“汪先生,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是我们自动地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们抗战呀!我们不打,难道等着亡国吗?”汪氏遂未多言。也许他已认定我是好战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时汪派反抗战人士已组织一个“低调俱乐部”,当前方抗战最紧张、后方民气最沸腾时,这批悲观分子却打着“低调”旗号,在后方泄气,实是可恨。直至武汉失守,全国精华地区全部沦陷,他们悲观到了绝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顾一切,掉头投敌,当起汉奸来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汪氏投敌后,五战区中袍泽虽亦纷纷议论,然究以敌忾同仇之心甚切,士气未受丝毫影响。
1939年初,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师,自平汉路东大别山区潜至路西。原来在武汉保卫战初期,在安徽太湖、潜山一带作战的,为徐部和川军杨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川军王缵绪部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武汉吃紧时,杨、王两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则奉命入大别山,协同廖磊部在该山区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