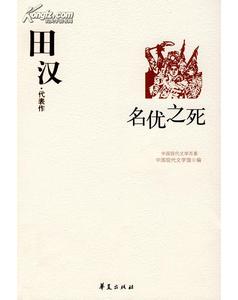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作品中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我”所讲述的苑氏家族一家三代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恋人,不管出场早晚,无论笔墨多少,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心灵冲击以致令人震撼。“我”的母亲柏香茗和姑姑苑菁,曾经是威震一方的抗日双侠“白莲”、“红霞”;谁能想到,不是由于敌人的围剿追杀而受难,却是因为一位暂时替代红霞角色的男警卫员“影子红霞”曹迪的被捕叛变,让红霞身背恶名,人人侧目,假红霞戏弄了真红霞,毁灭了真红霞;在乡亲们和同志们的误解、仇视和追杀中,负伤休养的真红霞难以再存活下去,在绝望中莫名地死去,也让白莲最终被逼得远走延安,并且要接受漫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审查交代。“我”的爷爷心如居士,作为一个开明而进步的地方士绅,在投身抗战中与子女一样加入共产党,传递情报;因遭受牢狱之灾,接到上级的指示保存实力自首出狱,可是,走出牢房后,却无法证明履行自首手续的指示来自何人,此后便只能以叛徒的身份苟活于人间。“我”的哥哥苑凯,一位意气风发、多才多艺的青年人,先是苦于父亲的残暴管束,逼出他的叛逆性格,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岁月中,又因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不合时宜的爱情,被迫走向了死亡,他用来自杀的,竟然是当年用来给他接生的那把手术刀,“我”父亲的珍藏之物,从生到死的距离,不过是一把几寸长的手术刀!还有那位邹大伦,和“我”的父母亲当年一道走向革命的老同学老战友,本来有着骄人的革命经历,又人如其名地恪守中国文人的伦理品格,一路风尘仆仆地护送战友之妻抵达延安,忠实于朋友的情谊而大义灭亲,不顾自身的困窘处境而长期接济心如居士;可是,他先是被审干运动逼得断指明志,后来又在战斗中负伤而脱离革命队伍,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寄身于戏剧表演的草台班子,以擅演丑角而著称,让人分不清是时势嘲弄人,还是喜剧嘲弄现实。还有姚耀,柏涛,夏天庚们,每一个人物都不佩有美好的生活,每一个人物都饱经命运的蹂躏。历史的残酷,天地的不仁,果真是以万物为刍狗吗?
如果说,这些人物的无可奈何的没落和死亡,构成了作品的沉郁悲剧氛围,那么,作品中的“我”的父亲苑志豪,母亲柏香茗、他们数十年间的恩恩怨怨,母亲死后留下的遗书和日记,就更加显得触目惊心。既是作品中的也是苑氏一家人中的男主人公的苑志豪,从战争风云中走过来的革命干部,一方面充满了奇思妙想、闲情逸致和浓郁的生活情趣,体现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修养,一方面又是家中的混世魔王,为所欲为,肆意横行,摧残子女,虐待妻子,以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一方面,在人生数十年的浮浮沉沉中,他饱尝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也失去了同甘共苦的伙伴,一方面,他又对在险风恶浪中先后落难的父亲心如居士和老战友邹大伦,以反目无情、斩尽杀绝的冷酷,这种冷酷,远远超出了自我保护的需要;一方面,他是廉洁奉公、决不用任何权利为子女亲友谋取利益,乃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无父无子,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方面,这般铁石心肠的人,又会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雷厉风行,为那些为支援三线建设而离开上海的人们主持公道,解决返沪问题,进而演绎出一段可笑而又可叹的婚外情;他曾经对违背自己意愿的儿子苑凯深恶痛绝,不但自己拒绝承认这个正在遭受沉重迫害的“不肖”的儿子,还“除恶务尽”地断绝了他的战友们可能对苑凯提供的任何援救,可以说,苑凯的死亡,与他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在苑凯死后他都坚持与苑凯划清界限;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也确实流露过对儿子的伤痛之情——就在他表达对刚刚死去的儿子的尸体拒绝接收的同时,他却被这猝然打击惊骇地瘫在座椅上站不起来,在看到苑凯曾经参与演出的样板戏剧目广告时;他也曾黯然神伤。最为可叹的是,这位一生对书法、对笔墨纸砚充满激赏之情的苑志豪的文人情怀,却只能是经常地用训练有素的毛笔字书写自己的检查交代和斥责父亲和儿子的绝情书。母亲柏香茗,与他是“自由恋爱,革命伴侣”,数十年间一道走过了并不平静的人生历程。但是,在这金色的光环背后,却是几十年的含羞忍辱,创伤累累,如柏香茗后来总括的那样,“十七乃相识,七十不相知”。如果说,苑志豪是把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压抑和扭曲,转嫁到家庭内部,发泄在妻子儿女身上,柏香茗呢,在战争年代,曾经女扮男装,锄奸杀敌,曾经遭受过莫须有般的诛心有术的政治审查,除此之外,在漫漫人生中,她还遭受了女性所特有的人生苦难:在战火纷飞中生儿育女并抚养他们长大,而丈夫又往往不在身边,其困难可想而知;在家庭生活中蒙受丈夫对自己对儿女的残暴态度和冷漠无情,不但为自己、更为孩子们的遭遇椎心泣血;为了接济被苑志豪驱逐在外的儿子苑凯,她被丈夫剥夺了家庭经济大权,只能以自己的节衣缩食为孩子们提供有限帮助,自己却因为营养不良而致病;当她终于做出要与苑志豪离婚的决定,却遭到丈夫先发制人的屡次出走,再次蒙受耻辱。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可能和机会对抗自己的丈夫,她把积淀已久的怨恨倾诉在死后才为丈夫和家人得知的日记中,在自己身后给家庭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终于在漫长的对抗中赢了丈夫一局。在这里,我再一次感到了人生的荒谬,母亲最后一搏的“惨胜”,不也同时是一次彻底的惨败吗?
世事如烟,去日留痕,如烟散去的是什么,挥之不去而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如果人生都如《去日留痕》所描述这样不堪其沉重,那么,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的荒诞和悖谬,让我们难以想像更难以接受,那么,人们能否走出这种怪圈,抑或说,无望的人生,这干脆就是一种无解的死结呢?如果能够将具象的人物和场景生发到形而上的悲剧性思考,我们才不会辜负作家燕燕的煞费苦心,以血为书吧。去日留痕,留下的是淡淡的血痕,累累的伤痕啊。
(原载《文汇报》2004年11月29日)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27节 读季羡林的《清塘荷韵》
雷淑容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季羡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签,季羡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清塘荷韵》是季羡林的散文名篇,写他无意在楼前清塘中投几颗莲子,竟得满塘风荷举。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用它作书名,有以荷喻人,以荷喻文的用意,正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也。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外,兼容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吐火罗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厚,均可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唯“深情”二字,不读他的散文,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
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是,季羡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书中所收文章,最近的两篇,《清华梦忆》写于2000年11月7日,《九十述怀》写于同年12月20日——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全书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时的得意佳作,到耄耋之年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这已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敏感,修炼成散文大家。
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远大于欢意。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平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尤其《母与子》、《三个小女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夜来香开花的时候》、《重返哥根廷》,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羡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拾。季羡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季羡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
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自己的情感纠葛。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羡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年轻的季羡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打字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羡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好一对深情人。可惜了。这是题外话。季羡林先生文章一片真情,有口皆碑。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界,却可以品味,甚至妄加揣测。季羡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学问无大小,人生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获吧。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8月11日)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28节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读李辉的《和老人聊天》
汪凌
有时候不由感叹,人类得以延续至今,“健忘”大概是一个重要基因。将曾经的大苦大难从记忆中抹去,用忘却来甩掉包袱,保持前行的动力。也许正因此,人类才得以保持了一个基本健康的心态。只是偶然回首,历史中间的苦难,就像一枚针刺在指尖,渗出殷红的血滴:又因为十指连心,传到心上,心也会刺痛。
李辉的《和老人聊天》给我的感触即如此。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真相,在这个轻舞飞扬的时代,谁还能想像,二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国家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存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惨烈的肉体乃至灵魂的改造运动。
对过往的历史有所了解后,我不再像以前,总觉得有些事件像蒙了一层厚纱,虽然隐隐能看到一些蹊跷,却终是朦胧。如今,每当我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表现出某种费解的行为或变化,我都会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而且,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对事件和人,我不再仅仅只是同情、叹息,或鄙视、愤怒,我会顺着作者的思路去思考: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幸!为什么杜高所谓“‘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竟成了事实?
在书中,夏衍将周扬的前后变化上溯到延安时代,说何其芳、袁水拍在肃反、反右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什么样子?理论家、诗人变成了整人的人……可是当时情势下,知识分子不变成“另一个样子”,谁能过关!因此,当杜高面对失而复得的档案,尤其是他和朋友之间的互相检举揭发,心情一定难以形容。我没有见到发表的档案材料,但从李辉的访谈中能约略知道大概。以前看过《赵丹自述》里的交代和检讨,大体也能明白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在“聊天”中,杜高讲那些劳教日子里,肚里装满墨水的文化人是怎样一层层扒掉身上的遮羞布,终至沦为“走兽”;劳教的年轮是怎样一点一点压弯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
前几天看了两张旧碟——《钢琴师》和《鬼子来了》,恰好都是“二战”片,不约而同讲述了人类心中的暴行。令我纳罕的是,除了犹太群体的集体沉默和顺从,就是德国人的集体暴虐。说起来,德国也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和高度的社会文明,可是,何以会爆发出如此疯狂的杀戮潮?
也许,无论文明、文化、教育……怎样努力地褪去人身上的兽性,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