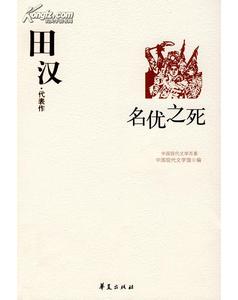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一个侧面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个不断被阐释不断被认同,逐渐建构、定型的中国古代诗歌传统。这显然是个艰巨而复杂的工程,我们该从何处下手呢?
朱易安首先是从作家评价的历史变化这一角度切入的。她发现李白研究中存在一个难点:“这位唐诗诗坛上的首席诗人,在迄今为止被勾画的唐诗发展流变画图中,没有找到他适当的位置”(页37)。“人们一面承认李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游离于他所属于的那个时代诗坛之外,一面又努力将其当做那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李白及其作品中去寻求盛唐的普遍特征”(页38)。她解决这个疑难,不是去寻求李白诗歌与盛唐的关联,而是探索李白诗中超越性的文化价值,她认为那就是人格的独立性、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异于流俗的价值观。在唐代士阶层的传统价值和地位的普遍失落感中,诗仙李白的这些品质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和典型意味。朱易安成功地以历代李白评价的变迁向我们证明:“李白身上积淀着中国士人的传统性格和特征,而李白形象又映衬了中国士人的传统性格和特征。士阶层按照自己的理想价值去寻找李白,重新塑造李白,也通过这种重新塑造来确立自我,获得心理上的满足。”(页55)这一结论是很给人启发的。《白居易与诗歌批评视野的嬗变》一章也取得类似成果,它的题旨准确地说是由白居易讽喻诗评价的变化看诗歌批评视野的嬗变。由辨析“元和体”概念的内涵入手,朱易安考察有关“广大教化主”、“白乐天体”的歧说,勾画出历来对元白诗歌主导倾向的认识、评价和接受的变迁,使白居易诗歌在文化、艺术上的多层内涵得到揭示。这番工作同样说明,“中国文学史上的白居易,是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思潮的嬗递变迁而闪现不同的光彩,最终是一个被后人用各类文学创作塑造起来的形象”(页110)。这一结论于唐诗学者未必很新颖,但它对评论史的梳理并揭示批评视野的嬗变之迹,却为批评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般来说,学术史研究有两个视角,客体的视角关注问题和成果,主体的视角关注学者本身参看笔者《学术史研究的两个视角》,载《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收入《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中。。二者的结合、互补构成学术史的完整景观。然而具体到每一位学者,由于知识结构和禀赋不同,兴趣就可能偏向某个方面。朱易安的研究显然倾向于后者,因为她理解的唐诗不只是诗歌史上一个辉煌的段落,而且是古典诗歌一个活的传统:“唐诗的价值,唐诗的魅力,全部体现在它的创造过程中。唐诗是我国传统诗歌发展中一次最完美的创造工程的完成。至此以后,历代的诗歌创作,总是不断地从唐诗中汲取营养。唐诗不是放在祭坛上的供品,而是流动的生命。后代的诗人崇尚唐诗,每一次都与自己时代的诗歌创作有关,这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赋予唐诗以新的生命力。”(页5)基于这种认识,朱易安考察了自唐至清历代诗论家对唐诗的态度和研究成果,对晚唐五代诗格、宋代理学家诗论及明代格调派这些在诗歌批评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诗论家、诗歌流派都做了认真的研究,尤其对明代格调派的唐诗学用功最深。而由各自的批评话语和批评方式推原、分析其诗学观念和文化背景,也成为《论稿》的重心所在。《〈钱注杜诗〉与20世纪的文化批评》一文指出,钱谦益注杜的指导思想也许是要“以诗证史”,但最终提供给后人的成果却是“以史证诗”,这种通过诗歌来解读历史,又通过历史来解读诗人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式,不仅开创了清代唐诗本文整理解释的严谨作风,也影响到20世纪唐诗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方式。这一高屋建瓴的结论,显出作者融贯古今的通识,这正是学术史研究最难得的素质。
《论稿》在主体视角的研究上固已成果斐然,但可贵的是它同时并未忽略客体视角的研究。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人们在将某一流派的创作主张与其唐诗观联系起来讨论时,往往只注意它受唐诗的影响,而忽略了它的唐诗批评。比如一提到明代格调派“诗必盛唐”的主张,便联想到前后七子的模拟作风,而很少从唐诗批评史的角度去考察他们对唐诗的研究。为此朱易安用三章的篇幅详细研究了明代格调派的唐诗观,不仅弄清明代格调派演变的三个阶段,而且裁量了他们研究唐诗的业绩。这一工作让我们看到。清人乃至今人提出的问题及结论,不少都源于格调派;而今人尚未涉及的问题,格调派也已提出了不少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事实上,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了解学术积累和前人提问题的方式,以确立当今的学术起点。读一读朱易安整理的有关材料,我们会深感现有的研究是多么肤浅,有多少问题可以开掘。起码我个人已有极大收获,对自己一向信心不足的中唐诗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许多可供开掘的问题。
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文学批评史的有力补充。这一点已为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所证实。《论稿》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学术史的这一功能。作者多年研究唐诗学史,曾与陈伯海先生合编《唐诗书录》,阅读了大量的唐诗学文献。学有所得,厚积薄发,不经意地陈述一些很概括的见解,也颇给人启发。比如她指出唐诗学的诗学形态大致是以如下线索展开的:
结集——感悟式的点评(具体作品或抽象的)——诗话
选诗——注释、评价(作家一作品一流派)——诗学总论
前者是唐宋时期的主要线索,后者是明清时期的主要线索。这结论看似简单,却非人所易道,需要具备闳通的史识。《理学方法与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一文指出,在以选本确立模拟范本的问题上,朱子《答巩仲至》论述诗选的原则、体制及“羽翼”之喻,对杨士宏《唐音》、高《唐诗品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也同样显出作者的独到见识。面对漫长的唐诗学史,面对见解纷纭的唐诗论著,朱易安注意到“每个人谈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使用的概念有时虽然相同,但却很难严格界定。有些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原先的意义了。所以在解释唐诗学的理论时,一方面要与历代的诗歌创作状况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要十分注意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页11),将审美标准、思维方法的变化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虑。这是《论稿》一以贯之的宗旨,已不需要一一举例。
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门艰难而需要多方面知识储备的学问。以当今的学术环境和知识积累,涉猎学术史对学者来说就意味着面临更艰险的挑战。作为通论历代唐诗学的著作,《论稿》涉及的知识和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悉臻精深境地是不太可能的。《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和《理学方法与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两篇,比其他篇章就略显浮泛。《后七子与明末诗人的唐诗观》论王世贞“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之说,认为他回避了“性情”或“诗本发乎情”的命题,而采用“诗有别才”的说法,似还可推敲。窃以为“才生思”云云是创作心理学,“性情”云云是诗歌本质和本源论,未可相提并论。当然,这都是细节问题,与我阅读全书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原载《文学评论》第5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1节 评《王渔洋事迹征略》
王小舒
上世纪90年代称得上是清诗研究的丰收期,其间有两部清代诗史著作问世,即朱则杰的《清诗史》和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另外,袁行云先生的遗作《清人诗集叙录》著录弘富,考镜源流,实也具史之价值。诗学理论方面则有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出版。至于诗人别集的整理刊行以及专题研究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与几十年前清诗领域的冷落境况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研究热潮不断升温的同时,如何更切合清代诗歌集历代大成,理论,创作同步繁荣的特点,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也成为学者酝酿、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在此时,蒋寅的两部著作《王渔洋事迹征略》与《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以下简称《征略》和《诗坛》)同时问世,它们为诗学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气象,成为目前清诗领域又一引人注目的成果。
王渔洋是清代前期的著名诗人,主持风骚数十年,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有卓著贡献,特别对诗歌创作风气的转移和清诗面貌的形成影响巨大。对这样一位作家,此前已有数种研究专著问世,但多数属作者本人的个案研究,未将王渔洋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总的创作状况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憾。蒋寅的研究则突破了这一格局,他站在史的高度,将王渔洋放到顺治、康熙这一大的创作流程当中,考察其与整个顺、康诗坛的互动、共进关系,这样做,一方面说明了渔洋诗歌风貌的成因和理论主张的内涵,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个点展示出清前期诗歌总体的流变脉络和演进轨迹。作者称此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它使得蒋寅具有了多重、立体的视角,并真正达到了点与面的动态统一。
《征略》和《诗坛》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著作,前者是作家的事迹编年,属年谱性质,后者则是文学史的专题研究,属论著性质。但二者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征略》一书是在大视野观照下的作者事迹编纂,它所展示的不仅是具多条逻辑线索的谱主生平履历,同时也是顺、康诗坛创作活动一个总的事迹编录;《诗坛》一书则是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出来的理论专题研究,它们一经一纬,一历史,一逻辑,达到了理论与文献的有机结合。
与一般年谱不同,蒋寅的《征略》专门注重于谱主文学活动的编纂,尤注意文学交游活动的考订,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学术眼光的体现。蒋寅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方法,凡所知与渔洋有关的文学家均无一遗漏地收入,涉及的作家达三百一十余人,对他们的生平—一加以考证。尤为可贵的是,凡言及渔洋的文学交往,蒋寅必同时征引对方文集中的材料以及其他文献予以佐证,为此,作者翻阅的文献达千种以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种艰辛的工作绝不是在搞无谓的资料堆积,相反,作者于材料的取舍处理上具研究眼光,在文献资料的排列中,读者能够隐然感觉到某种线索的存在。这里举几例说明之。首先是以文学活动为主线的治谱思路。众所周知,王渔洋一生与仕宦相始终,官一直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而且颇有政声。有人以为,这是渔洋人生的一个重要亮点,值得大肆张扬之。这实属肤浅的看法。王渔洋受家庭影响,确有勤政尽职的观念,蒋寅所引总集未收的《手镜录》一文已基本囊括了这种观念,但这仅仅是一种基本素质而已,身处明清鼎革之后、经历家国劫难的渔洋实际上并无在政治上锐进、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征略》一书已清楚展示出来。康熙三十七年,蒋书引渔洋《自撰年谱》云:“七月,迁都察院左御史。……退食谢客,焚香扫地,下帘读书,白一二韦布故交以风雅相质外,门雀可罗也。”康熙三十九年,再引《古欢录》自序云:“山人官御史大夫,世号雄峻,山人居之澹然,其门萧寂如退院僧。退食之暇,浏览诸史、《庄》、《列》,下逮稗官说部、山经海志之书,有当予心,辄掌录之。”事实上,谱主在最能有所作为的御史位置上无任何重要建树。笔者尝认为:“王家到士这一辈,在价值取舍、处世原则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虽谨于职守,而其实‘寄焉而已’,虽读书写作,而目标不在尽正统之道,却在于保全人格的独立。”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0页。此与蒋寅的《征略》恰相吻合。此种处世态度在当时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渔洋正是一个典型,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全部兴趣都投放在了文学活动中,文学成为他人生的真正亮点,这与唐宋时期的一些大作家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蒋寅才做出如此选择,此全由学术眼光所致。
蒋寅在著录谱主的文学活动方面特别繁富、详尽,如其本人所说“不惮详细”,这样做其实具有多重的价值和意义。过去人们理解的文学研究,一般是文本研究和作者生平遭遇研究,对于写作方式和传播手段则往往忽略之。蒋寅不同,他在《诗坛》一书中指出:“文学被视为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和批评,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就构成了文学史学。”可见,他是将文学交游视作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事实上,文学交往确是作家个人与创作群体、接受群体进行沟通、交流的一座桥梁,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一个时代文学活动的枢纽。回看顺、康期间,作家的聚会、酬唱实为一种十分普遍的交游形式,其中包括集体登览、友朋送迎、文酒之会、寓所夜话等多种方式,此外,书信交往也是一种很流行的交游行为。王渔洋处在诗坛的中心,雅好交友,又具朝廷官员的公开身份,所以交游活动就特别频繁,所谓“日招四方名流赋诗饮酒为乐”。从蒋书著录的诗人名单看,它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所有知名的作家,足见渔洋文坛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如进一步考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作家归属两大群体,一是由明入清的作家群,除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少数人外,大部分属于遗民,即渔洋说的“布衣交”。另一是清朝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他们多是与渔洋同样身份的朝廷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