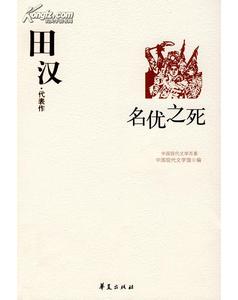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书的部分精彩章节。然而,他并没有表现出我所期待的感动,他甚至像在听我讲述与他关系不大的事情,在背别人写的书似的。我感到十分困惑:他真的是那个充满激情写英雄的作者吗?!他的平淡与我年深日久的激动是无法平衡的呀!我想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
五年后,我接到漓江出版社的年选书。书中选了我的报告文学《中国家庭:钢琴带来的喜与悲》。这是2001年的选本,翻开来,我眼前一亮:里面收录了金敬迈先生的一部新作《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于是,我一口气看完了这部书,其震撼程度绝不亚于当年的那部“欧阳海”!只不过,这一回英雄人物不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他就是因为当年写了《欧阳海之歌》一书而红遍大江南北,竟至遭到了江青的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而他在那个真正的监狱中所经历的故事简直令人怵目惊心。七年中,他关在阴森的大墙里边,只能见到一小块被切割的天和一个很大很凄惨的月亮。他的文字令我想到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掩卷深思,我想到了那个作代会上接受我拜访的白发长者。他那坚毅冷峻的面孔,他那过分冷静的反应,他那没有多余的寒暄并且一点也不为你受他书的影响而欣喜的样子。我弄明白了,如今的他,已经远不是当年写作欧阳海的青春沸腾的金敬迈了!他老了,他什么都经历过了,他什么都看透了。他对于生活的体验与认知,已经完完全全地陷入了宠辱不惊的状态中了。他那些年里阅读的天空是倾斜的,属于他的阅读范围是阴郁的凄惨的清冷的月亮。用他自己的话说,死在那个著名的监狱里面是正常的,而他能够活着出来甚至将他的真实经历付诸文字,这简直是奇迹。
在我阅读的天空中,如果说阅读《欧阳海之歌》是我少年时代的激情燃烧的彩虹的话,那么,现在读他的生死之作《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便是涂抹了凝重而沉郁的云霭。这两部书之间相隔了差不多有四十年。
四十年前的父亲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青年,那时候他一心只想着工作。四十年后的父亲已经垂垂老矣,他因糖尿病合并症而导致双目失明。他已经很久不再诉说他的自豪理由了。他习惯于沉默,他眼睛看不见时更加沉默。已有三年了。每当他茫然仰望时,我便意识到属于他的那片天空,不过是一张宣纸。在坚忍而持久的浸墨中,它已完全黑了,不会见到一丝光亮的。然而,我始终费解的是为什么他从来不在我面前承认他看不见,我每每要带他去看医生希望为他动手术时,他总是说他还能看到一点儿,他拒绝做手术。他是担心他那可怜的极微弱的视力被手术刀彻底破坏呢?还是因为他不愿花儿子的钱为自己治病呢?(父亲曾经对别人流露过没有钱为我买书看的沮丧)。无论是哪种理由,父亲的痛楚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是那么渴望着能够读到他的儿子的作品,但是,这种可能已经离他远去了。父亲不是作家,也从没有英雄气魄,他是个老实人,谁都说他老实了一辈子。现在让我评说年迈的父亲,我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自控力自律力都将赢得我永远的尊敬:无论是当年不曾贪污一分钱,还是现在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天空像一张宣纸被墨迹浸黑而不叫不闹,默默承受……
(原载2004年6月28日《北京日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7节 一个人的阅读史
戴来
我最近在看伊万·克里玛的东西,这位和米兰·昆德拉以及哈维尔被并称为捷克文坛三驾马车的作家,有20年时间其作品在捷克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据我所知,作品的翻译版权早在6年前就已购入;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今年年初才出版发行。我刚读完短篇卷《爱情对话》,纯粹的对话,充满不可能的爱情和神秘睿智的对话,没有任何景物或心理的描写。在缺乏沟通交流的人与人之间,我们寄希望于用爱情来打破隔绝和进行沟通;试图用爱来摆脱绝望失败的生活,但爱的神经是那么的脆弱,在没有出路的生活中,爱情同样没有出路。即使这样,我们还得爱着,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因为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我们已经停不下来了。
与此同时,我在重读法国作家让…菲利普·图森的《浴室…先生…照相机》。图森是比利时人,但他是在法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的语言很有质感,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几乎可以触摸。今年三月去巴黎参加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法国的读者在见面会上,提到了这位他们喜爱的作家和我的小说之间的共通的气息。我把这看作是一种褒奖。促使我重读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我的朋友吴玄大半年前在北大作了一次题为《关于无聊的小说和猫的游戏精神》的演讲,他说图森算不上一个大作家,但确实是新小说之后的一个重要作家。小说写到新小说那儿,文本内部的实验几乎已经被穷尽,先锋作家们快要迷路了,他觉得是图森找到了一个出口,小说不再在文本内部试验,又重新回到了关注人类存在的困境上。无聊和痛苦一样值得关注,如果说现代派是地狱时代的叙事,那么后现代就是天堂时代的叙事(这一段是原话,我本想消化一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但翻来换去说了几次,觉得还是吴玄老师说得精辟)。
1994、1995这两年,我反复阅读得最多的就是余华的作品。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写作,也没打算写东西,读小说对我来说就是读故事和消磨时光。其实余华早期的小说,故事性不强,它吸引我的是它文字里弥漫的危险、诡秘的气息。十年过去了,尽管这些年余华不怎么写小说,但他仍然是我比较偏爱的作家。他是个聪明的有写作天赋的作家,是个让读者能对其有所期待的作家。一个愿意尝试新东两、不断在寻求变化的作家是值得尊敬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再没有一位外国作家会像卡夫卡这样受到写作者普遍的推崇和更为普遍的阅读了。一个人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只让人怜悯又令人厌恶的甲壳虫,作品一开始就把人逼到了一个既无法前行又无法后退甚至不能转身的绝境,有点意思吧?《变形记》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新颖奇特,卡夫卡把人在困境中的内心感受表达得极其精确到位。说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点都不为过。
而那个一生做了很多与文化有关的事但只写过一部小说的钱钟书先生最牛了,且不说这些年来养活了多少做盗版书的“业内人士”,单是由这部小说演绎出来的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就有一大堆,听说,最近还有人打算重拍电视剧,我看就算了吧。《围城》是一本我读了十几年、至今还在读着、并且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有滋有味地读下去的好书。我想,一篇小说,当剔除了其时代背景后依然有着生命力的应该就是好小说了。
日子像书页,不知不觉翻过去了30来页,尽管指间还有和书页摩擦留下的细微的感觉;但书页是已经翻过去的了。20年的阅读,说长很长,说短就特别短,有些书已经被我彻底地翻了过去,我甚至不好意思和别人提及它们曾经是我少年时代阅读的全部,因为它带着特别明确的青春躁动的气息和灰暗颓废的阅读倾向,但它参与了我精神的成长,它给予我的已经渗透进了我的少年时代。
记忆中,我真正入迷地去阅读一本书是从三毛的作品开始的。三毛自闭别扭的少年生活,以及用文字营构出的那种独立、自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我陆续买全了她所有的书,读了一遍,两遍,无数遍。一个选择撒哈拉大沙漠居住的女人实在太与众不同了,尤其是她为了爱远走异国他乡的举动颇合我的胃口,甚至她后来的自缢都十分符合我当时的审美。那时候我十四五岁,外表随和,内心叛逆、激烈,精力旺盛,时常冒出些怪异乃至极端的念头,那是个危险的年龄段,看上去还算安静乖顺,其实特别脆弱和神经质。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我少女时代最能吸引我的文字都是有关流浪的,比如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被我放在枕头下面,睡觉的时候,我会把一只手搁在枕头和书之间,手心贴着书的封面,手背上压着枕头,某种隐秘的交流正在进行着。“流浪”这两个字在那时候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走出去,就是在路上,就是特立独行,就是漂泊,简而言之,就是浪漫。
若干年后,我也离开了家乡,并且一走就是十来年,并且至今还在路上。
(摘自《作品》2004年第12期)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
吴思
一;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路的那一股。当时我在山村插队,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可是,六年前我重读此书,竟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保尔的褊狭和自负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我当年的偶像吗?我竟然努力模仿这种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会向我女儿推荐这本书,我以后也不会再读。
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列、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不过,在描述人心的复杂和丰富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才称得上登峰造极。我觉得托尔斯泰很亲切,很对心思。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惊讶和敬畏的份了。
三;《唐诗三百首》。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国古典诗词,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元曲,《唐诗三百首》是他们的代表。这些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呼唤出我的“根本性焦虑”。人生短暂,年华易逝,这种感觉让人的心境深远厚重,超越蝇营狗苟,进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语寥落,欲说还休。
四;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超过各派心理学的作品。这本书,还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帮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动物的独有特性。十年前读毕此书,叹为观止,从此不再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五;《庄子》。苏东坡说:他小时候读庄子,觉得这人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完了。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苏东坡,深有同感。二十岁前后,《庄子》一度严重威胁了我的“革命理想”,反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有对抗《庄子》的意思。二十多年过去,我早已停止对抗庄子了,他描绘的人生和宇宙图景很精彩,可以把我们拔出自负和局促的泥潭,让我们面对那些最要紧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沉溺太深,忘记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实位置。
六;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1993年我听盛洪提到这门学科;表示没听说过,盛洪笑话我,说不知道就对了,经济学专业,岂能谁都懂?后来听了他们天则所的几次讲座;又读了一本介绍制度经济学的小册子,不禁神往。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七;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它的影响。至于写作深度,它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真到了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这不是嫉妒。
如果再提炼一下,超越专业或职业需要,上述诸书,《唐诗三百首》和《庄子》对我最为要紧,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书。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原载2005年1月1日《文艺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8节 我为什么不读畅销书
秦巴子
在我们这里,有畅销书这么档子事吗?说老实话,我很怀疑。我只知道,有些书在市场上是销得不错,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会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但那畅销的就算得上是畅销书吗?论销量,中小学课本大概在国内算是销量第一,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不算畅销书;排第二的应该是教参教辅类,也不能叫畅销书吧;很多年以前,语录本销量极大,算不算畅销书呢?国外的情形,好像是《圣经》的销量最大,但那不是在畅销书之属。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对畅销书似乎有些不太严格的定义,我们这里大概还没有,我们这里有的只是畅销的书——更多的是一种阅读时尚使然,所以我的不读畅销书可以转换成我不喜欢追赶那阅读时尚。
我之所以不愿意追赶阅读时尚,还有一种很私人的偏见:我一直以为,畅销的书是给不知道阅读什么的人准备的,而我知道我要读的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赶这个时髦呢?为投机的书商捐款的事情,我是很不情愿的,况且他们已经算是暴富,而我只是一介书生,断断没有让穷人施舍富人的道理吧。
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追赶阅读时尚会养成一种非常坏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像一头盲目的驴子,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轴在转圈儿。久而久之,就会患上一种我称之为阅读强迫症的病。我有一位同事,他的手一旦闲下来的时候,就会不停在搓纸蛋儿,他的脚下每天都会有一大堆被揉得像身上搓下来的污垢一样的纸屑,心理医生认为他患有强迫症。我觉得追赶阅读时尚就像没完没了地搓纸蛋儿,是一种强迫症患者的症状。当然他或者有揉搓的快感,但他获得的就只是一些成了垃圾的纸屑。我想,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阅读变成一种垃圾制造行为吧。
我们的传统中有一种阅读偏执,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