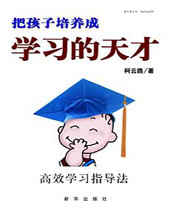擦肩的天使-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瑞没有说话;只是冷漠看着宿舍;看着室友们;就像第一天来时那样。阿瑞看到自己的床上堆满了各种杂物;仿佛这张床从来没有人住过;只是让大家放东西而已。阿瑞有些生气;但是他没有发作。阿瑞觉得和这些人发火不值得。所以他只是用眼神告诉那些东西的主人他的不满。
“阿瑞;回来啦!”老大从门外进来了;阿瑞的目光也变得温暖起来。
“嗯;刚刚到。来收拾东西。”
“这一段时间你躲哪去了?”老二正在把自己的东西从阿瑞的床上拿走。
阿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冷冷的说:快把你的东西拿走;要不我就给扔了。”老二碰了一鼻子灰;只能一边嘟囔着;一边抢救自己的垃圾。
“是啊;阿瑞;这一段你住哪了?”老大问道。
“我和一个朋友合租了一间房子。”阿瑞看到老大是唯一一个没有把东西堆在自己床上的人。
“哟;你还能和朋友合租房子啊!”老三故意把朋友两个字读得很重。
阿瑞白了他一眼;轻蔑的说:”我和朋友合租怎么了?你丫有意见?”
“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还真行!”老三赶快搜肠刮肚的找了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还真的是够烂。
“那个朋友我们认识吗?哪天介绍给我们啊!”老大正在忙着帮别人搬东西。
“哦;你们不认识她。介绍给你们可以;但是恐怕有些人会不屑啊!”阿瑞说着用眼睛瞥了一下其他人。其他人脸上都露出了难看的神情。
“不会吧;大家多个朋友总是好的。”老大赶快笑着出来圆场。但是尴尬的气氛并未因此而改变。每个人都默默的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没有人再说什么。宿舍陷入了一片沉静。
“阿瑞!”说话的是住在阿瑞对门的张凯;“那天和你一起去教堂的女生是谁啊?”
“哦?阿瑞,你交女朋友了?”老大看着阿瑞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没有,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和我合租房子的同学。”
“阿瑞!你怎么能……”老大惊讶的看着阿瑞,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怎么了?”阿瑞也惊异的看着老大。
“你怎么能和一个女生同居呢!”
“没有啊,我们只是租一间房子而已。”
“谁知道你们住在一起干什么了。”不知谁说了一句,声音很小,但是阿瑞肯定听见了。阿瑞没有说话,但老大开口了:“阿瑞,你这样做是在犯罪啊!”
“说什么呢!都跟你们说了,你们是不是有病啊!”阿瑞吼了起来。
“阿瑞,听我说……”老大的话没有说完,阿瑞转身离开了寝室。
这是帮什么人啊!阿瑞边走边想着。按照农历计算,早就已经立秋了。但是,北京似乎永远没有秋天,秋风扫落叶更是不可能。现在夏日的热气依然吹袭着阿瑞的脸庞。阿瑞此刻正在校园里走着。丛寝室里出来后,阿瑞非常的郁闷。并非因为被人冤枉了,被人冤枉与他而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郁闷主要来自老大,来自老大的不理解。在阿瑞的记忆中,这是他与老大的第一次冲突。他不明白为什么连老大都这么想他。
校园的路上,人来人往。人们匆匆的奔波着,麻木而快乐着。阿瑞站在这些忙碌的人中间,本来熟悉的校园竟一下子变得陌生了,似乎从没有来过这里一样。在明媚的阳光中,阿瑞第一次迷失了方向。这个时候,他只想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漠漠,只想到了一个可以发泄的地方——蒋卓的酒吧。
蒋卓的酒吧在半个月前就重新营业了,只是当时漠漠正在为蒋卓的离开而伤心欲绝,所以蒋卓没有邀请他们。阿瑞也从鸭子那里得知了酒吧开张的消息,只是当时不便开口。然而,就在阿瑞与老大冲突的当晚,他和漠漠竟出现在酒吧的歌台上唱着“Tomb of punk”。
这天,阿瑞从学校回来,进门后竟看到漠漠坐在他的床上摸着眼泪。她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抽噎。
“怎么了?”阿瑞忧郁的声音地问。漠漠没有回答,依然在默默地掉泪。
“嘿,怎么啦?”阿瑞又问了一遍,然而漠漠还是没有回答。
“你怎么啦!是不是蒋卓又说什么了?”阿瑞显得有些激动,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阿瑞想,一定是蒋卓又来说什么了!这孙子!
然而阿瑞看到的却是漠漠的破涕而笑。“我只是想哭!关人家蒋卓什么事?”漠漠一遍擦眼泪一遍说。
“你丫没事吧!闲的难受啊!”阿瑞本来就和很郁闷了,结果漠漠还耍他。
漠漠没有生气,只是笑着说:“我想在体会一下哭的滋味,我怕以后没机会哭了。”说着,她的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阿瑞,仿佛在说,你今后会让我哭吗?
阿瑞楞了一会,然后本能地避开了漠漠地眼神,因为他自己也一直在想,今后漠漠还会哭吗?
“走,去酒吧唱歌吧!”漠漠从卫生间洗脸出来,对阿瑞说。阿瑞先是一愣,问道:“哪……哪个酒吧?”
“废话,当然是卓……蒋卓地酒吧了!”尽管漠漠企图掩饰,但是她的脸色还是变了一遍。阿瑞没有反对。
当他们出现在蒋卓面前时蒋卓的表情大概就交惊讶了。
第三部分 漠漠第26节 浪人的死
“你们能来太好了!”
“现在好像很却人手啊。”漠漠环顾这四周,服务生地数量明显少了很多。
“是啊,刚刚开张,人手不够啊!”蒋卓名名是在回答漠漠地问题,眼睛却一只看着阿瑞。。
漠漠没有再继续追问,他拉着阿瑞走上了歌台,台下一片掌声。阿瑞和漠漠唱的是他们的代表作:“Tomb of punk”。阿瑞已经把这首歌的曲子练的很熟了,甚至在间奏部分还加入了一段即兴。漠漠的声音还是那种不入流的美。一曲唱罢,场下掌声骤起,很多常客喊着他俩的名字,不断的喝彩。
“阿瑞。”这是鸭子的声音。刚才在台上,阿瑞就看到鸭子了。
“鸭子!”阿瑞也向鸭子打了招呼,他们一起有坐到那个属于他们的角落的位子。
“听说你和漠漠住一起?”鸭子为阿瑞要了一杯“切·格瓦拉”,为自己要了一杯“夏威夷日出”。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阿瑞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也有些反感。
“噢,没有。我只是问问。我在想这世界上还有人能和那种女生合租一间房子吗?”
“深了!什么意思?”阿瑞没明白鸭子的话。
“我的意思是,漠漠那么辣,你还敢跟他在一个屋檐下?是不是经常被虐待啊?”鸭子说完,坏笑起来。但是他没有笑太久,因为他忽然发现,漠漠就在他身后,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你丫说谁呢!”没等鸭子解释,漠漠就爆扁了了鸭子一顿。
在鸭子地苦苦哀求下,漠漠才饶了他。“看你丫还乱说话!”
“你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鸭子小声嘀咕着。
“你说什么?”漠漠的耳音比鸭子想象的要好。
“没……没什么!”鸭子赶忙躲到了阿瑞的身后,“可别误伤了阿瑞。误伤了他可是有人会心疼的!哈哈哈哈!”
“心疼?谁心疼他呀!”漠漠的脸有些微红。
“还用说吗?”鸭子盯着漠漠说。
“你看我敢不敢误伤!”说着漠漠真的打了过来,大多数都打到了阿瑞的身上。
“喂!干什么?”阿瑞一边闪躲,一边喊着。
过了好一会,漠漠累了,他们才算安静下来。
“我渴了!”说着,漠漠起身去了吧台那边。
“你小子害死我了!”阿瑞不满的对鸭子说。
“得啦,你肯定没少被她欺负,这算什么!”鸭子坐在阿瑞的旁边。
“对了,最近有没有看到浪人?”
“他……”说到浪人,鸭子的脸色一下自变得很难看。阿瑞看到鸭子脸色的变化,忽然心里一惊:“怎么,莫非浪人出事了?事情严重吗?他现在在哪?”
“他……”浪人从来没有这么犹豫过。
“快说啊!”阿瑞有些焦急。
“他……去了广州,……回不来了!”鸭子缓缓地说。尽管他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逻辑,但阿瑞明白了:SARS,一定和SARS有关。但是,他还是不能相信,浪人会这么霉运。所以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和非典……”
“是的。”鸭子没有等阿瑞说完,就接着说到,“浪人感染了SARS,他没能挺住……”
阿瑞忽然感觉到呼吸很困难,他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个豁达乐观的浪人竟然就这么死了!死得无声无息,如同一片叶子落地一般!然而,那不是一片叶子,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年轻的生命!他本来是那么生机勃勃的,那么令人羡慕。然而他竟然就这么消逝了,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生命曾经存在过!
生命本该是多么伟大,可是现在它又是何等的脆弱和渺小!面对朋友的客死他乡,阿瑞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苦涩。他本来想找个方式宣泄,可是他居然没有找到。现在,任何方式的宣泄都无法减轻哪怕一点点他的痛苦。桐桐的离开,使他刻骨铭心;浪人的离开,却只能使他无奈。
“这个消息……漠漠知道吗?”阿瑞沉沉地说。
“不,她还不知道。”
“不要告诉她……”阿瑞的口气像是命令,但鸭子没有反对。鸭子缓缓的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CD,说:“这张Offspring现在还给你,我听过了,是张好碟,可惜浪人听不到了。”
阿瑞没有接鸭子递过来的CD,他冷冷地说:“这张CD我不能拿回去了,这是我欠浪人的。有机会把它埋到浪人的墓旁边吧。”
鸭子踌躇了好久,痛心地说:“可是,浪人没有墓……”
是啊,浪人独自身死异乡,谁会给他造墓呢?阿瑞的心在流血,一个人生前被人们排斥,被人们误解,在他死后竟也不能安然下葬。何等的悲哀!
“浪人就是浪人,他活着的时候居无定所,死后也就不应该让他待在一个地方。他说过,他是风,应该是自由。现在他真的是风了……”这些话是漠漠说的。
“你……你都听到了?”阿瑞惊讶的看着漠漠痛苦的脸。
“你们应该让我知道。浪人是我的朋友,活着是,死了也是……”漠漠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在这个喧闹的酒吧的角落,三个年轻人沉默的坐着。喧闹的世界此刻似乎已经与他们无关了。其实这个喧闹的世界与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大,百年之后,他们也都会无声无息的离开。不仅他们,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离开。后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我们。有人说人的一生只是宇宙的一瞬,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生命连一瞬都不是,至多是一粒小到可以忽略的微尘而已。生命的孤寂与无助让我们很多人麻木了,而阿瑞他们没有麻木。麻木的人是没有痛苦的,而阿瑞他们怎痛苦万分……
第二天,在香山的山顶,人们看到三个年轻人在迎着风唱歌,放音乐。人们纷纷看着这三个怪人,嘲笑他们是神经病。这三个人却根本没有理睬人们的意思,只是自顾自的做着祭奠一样的仪式。
“人类不能收留他,希望上帝可以收留他。”三个人中的那个女孩说。
“人们永远不愿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东西,未知的永远是可怕的禁区……”一个男孩说。人们听着他们的只言片语,更加坚信这些人脑子不正常,更加放肆的嘲笑、然而嘲笑往往是因为无知,无知的嘲笑反而更应该被嘲笑……
从那以后的半个月中,阿瑞和漠漠都一直再唱着怀念的歌曲。这些歌曲与酒吧的气氛不是很融合,对于招揽客人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好在客人大都是常客,他们和酒吧里的人或事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明白,阿瑞和漠漠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所以他们仍然照顾酒吧。
时间似乎真的可以模糊一切,一个月后,一切又趋于了平静——漠漠和阿瑞仍在唱歌,蒋卓依然辛苦经营着酒吧和家庭,鸭子依然用“鸭子嗓”强奸着听众的耳朵。似乎一切仍然继续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阿瑞和漠漠感觉到彼此在这一个月中都有了一些变化。
得知了浪人的死讯后,漠漠更加尖锐的看待着周围的一切。她似乎将一切的不幸都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人们的无知。她会责备人们对他们这些叛逆者的指责和唾骂,说人们这么做实在是非常的愚蠢。因为他们也许正在扼杀着下一个哥白尼或着曹雪芹。她会嘶吼地谴责人们的世故和虚伪。她甚至会恶狠狠的咒骂自己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要去学那些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的东西。这么说吧,漠漠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她把对周围人们排斥的恐惧转化为了自己的愤愤不平,把自己对命运的无奈转化为了对人生的斥责。
虽然浪人的死同样也让阿瑞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但是阿瑞却从中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阿瑞隐隐觉得,他和漠漠走的是一条正确但不幸的路。他们追求的自由也许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的。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阿瑞的父母因为阿瑞考试挂科而严厉的谴责了阿瑞,阿瑞的挚友老大因为他与漠漠合租房子而视他为罪人,阿瑞的其他朋友则都变成了阿瑞的敌人,阿瑞曾经拥有的头上的种种光环也都消逝不见了,随之而来的却是种种骂名。
在酒吧,或是在漠漠身边,阿瑞并不在乎这些。但是,阿瑞明白,他迟早要走上社会,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那时的他将必须依靠这些他不在乎,甚至是不屑理睬的东西度日糊口。如果是一个人,他可以学浪人一样四处流浪最后甚至客死他乡,但是现在他毕竟还爱着漠漠。他也知道,漠漠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