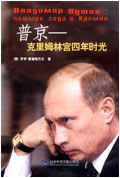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披着霞光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色呈现在你眼前。
啊,那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我们到过利文斯通,亲眼看到了四处游弋的鲤鱼,还有河马。旅途中,
我从沿途车站土著孩子的手中,花了三五便士买下了木刻的动物,带了回来。
这些小动物雕得栩栩如生:旋角羚羊,长颈鹿,河马,斑马——造型简单,
质朴,富于魅力和独特的韵味。
约翰内斯堡没留下什么印象,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那金碧辉煌的石柱倒
使我记忆犹新;后来到德班,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因为洗海澡竞得到海滩
上一个用网围起的圈内去。在开普省,最开心的要算是海水浴了。一旦能抽
出身来——或者说阿尔奇一有空——我们就登上火车去梅赞斯堡,跳上冲浪
板,一同在海上冲浪,南非的冲浪板选用又轻又薄的木板制做,容易驾驭,
不用多久,就能掌握诀窍,穿梭来往于浪峰之间。偶尔,嘴啃地式地倒栽下
去会感到疼痛难忍,但是这不失为简单易行的运动和有趣的娱乐。我们在沙
丘上野餐。我还记得那五彩摈纷的花丛。大概是在教堂或是在主教邸宅,我
们参加了一次舞会。那里有一个红花园,还有一个长满高大的蓝色花木的蓝
花园。这蓝花园因其满园的紫茉莉而显得娇艳无比。
在南非的费用没问题.这使我们心情畅快。差不多在每家旅馆我们都是
作为政府的贵客而受到优待,乘火车旅行也毋需掏钱——唯独去维多利亚大
瀑布的私人旅行破费了一大笔钱。
从南非启程,客轮驶向澳大利亚。那是一段相当乏味的长途旅行。船长
向我解释说去澳大利亚的捷径是取道南极然后再北上,这对我是个谜。他给
我画图解释才使我解开疑团,但是要记住地球是圆的,而极点是平的决非易
事。这是个地理学的事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理解它的含义所在。
总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任何国家总是被描绘得与你乍到时的印象大相径
庭。我对澳大利亚的粗略印象是数量惊人的袋鼠和莽莽荒漠。最使我感到诧
异的是当我们到达墨尔本时,树木的奇特风姿以及澳大利亚的桉树使景色具
有的异域风采。每到一地,树木总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抑或是山峦的起伏。
在英国,人们习惯于树木长着暗色的躯干和色调明快的枝叶;澳大利亚的情
况恰恰相反,另有一番新意。
到处是银白色的树干,暗淡的树叶如同照片的底片一般。令人兴奋的还
有钨鸥鸟: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成群地邀翔在空中。斑斓的色彩美极
了,像是飞翔的宝石一样。
在澳大利亚和在新西兰,我在社交场合一再出丑,那是由于宴会餐桌的
位置。以前每到一地,我们的座位通常挨着市长或商会会长,所以在这儿举
行的首次宴会上,我便不假思索地径直坐到市长之类的显赫人物的旁边。一
位老妇人酸溜溜地对我说:“克里斯蒂夫人,我想您一定愿意坐在您丈夫身
边。”我忙满脸羞容地坐到阿尔奇身旁的座位上。
我们曾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好像叫杨加的车站停留,记得那儿有一个大
湖,湖面上黑天鹅游来游去,宛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在那儿,贝尔彻和阿
尔奇忙于呈送大英帝国的要求,讨论帝国移民问题和帝国贸易的重要性等诸
如此类的事情,使我有暇坐在桔园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的旅行一半是坐火车,但更多的是坐汽车。坐车奔驰在那样广袤无
垠的大草原上,只有偶尔几个风车划破地平线,我认识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
的事实:迷失方向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太阳高悬在头顶,无法辨别东、西、
南、北。我无法想象绿草茵茵的沙漠的样子,而只有到处是沙砾的荒漠的概
念。但是在沙漠中旅行毕竞可以找到指引方向的路标或什么明显的标记,可
在这一望无际的澳大利亚草原上却找不到这种标记。
我们到了悉尼,在那玩得好极了。听人说悉尼和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最
美丽的两个海港城市,但悉尼却令我失望。
大概我对它期望过高了。幸运的是,我从没有到过里约热内卢,因此,
我脑海里总能想象出一幅关于那里的迷人画面。
不久,阿尔奇和贝尔彻赶到了,不懈的努力弄得他们精疲力荆我们过了
个充满欢笑、无忧无虑的周末,别出心裁地玩,还坐着窄轨火车游览,我还
驾驶着它跑了几英里呢。
英国巡视团在澳大利亚备尝艰辛。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讲演,宴会,
工作午餐,招待会和长途跋涉。我都背得出贝尔彻说的话。他善于演讲,那
发自内心、充满激情的讲话仿佛是他的即兴杰作。阿尔奇以其审慎和善于理
财的特点与他形成对照。阿尔奇曾经被报纸称为英国银行总裁。他任何与之
相关的言谈从未见诸于报端,因此就新闻界而言,他俨然是英国银行总裁。
离开澳大利亚,我们去了塔斯马尼亚,从朗塞斯顿坐车来到美丽得令人
难以置信的袒巴特,湛蓝的大海和港湾,扶疏的花木,我准备将来有一天再
回到那儿并在那儿定居。
告别霍巴特,我们抵达新西兰。那次旅行我记忆犹新。
因为我们的命运落在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脱水机”的家伙手中。那时
脱水食品的概念风靡一时。这家伙总是想法把一系列的食品脱水,每次用餐,
使从他的桌上递过来一盘盘荣看,一再请我们品尝。我们吃了脱水胡萝卜,
脱水杨梅等等——统统无一例外地食之无味。
贝尔彻说:“让我装模作样地再吃一口他的脱水食品,我就会发疯。”但
是由于“脱水机”有钱有势,对英国巡视团颇有用处,贝尔彻还得强压不快,
继续与脱水胡萝卜和脱水土豆周旋。
这时,初期共同旅行的愉快气氛已荡然无存。那个曾经彬彬有礼地在我
家聚餐的贝尔彻再也不像个朋友了。他举止粗鲁、傲慢、专横、不体谅人、
而且在细微琐事上斤斤计较,我始终认为新西兰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国家。
那儿的景致无与伦比。我们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到达惠灵顿的,据那儿的居
民说这种好天气不多见。农村景色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我当时发誓要在春天
回来——我是说当地的春天,看那蜡达树繁花朵朵,满树的金黄和猩红色。
可这没能实现。
贝尔彻欣然返回了新西兰。他在那交了不少朋友,惬意得像个孩子一样。
他在我和阿尔奇赴檀香山前祝福我们万事如意,过得愉快。谢天谢地,阿尔
奇不再公务缠身,不必和那个坏脾气的想入非非的同伴费口舌了。我们悠然
旅行,在斐济和其他小岛上滞留,最后终于到了檀香山。那儿远比我们想象
的旅馆林立、路广车多的景象要繁华得多。我们是在清晨到达的,一进旅馆
卧室,凭窗远眺,看到的是人们在海边冲浪和人群蜂拥租赁冲浪板,跃入大
海的景象。我们不知深浅,那天不是冲浪的好天气——只有冲浪好手才去的
天气——可是我们在南非冲过浪,自以为驾轻就熟。檀香山的情况完全不同。
冲浪板是一块厚木板,重得几乎浮不起。你躺在上面,慢慢地滑向礁石,礁
石在我看来只有一英里之遥。到那儿后,你得再选好位置等待合适的海浪打
来,把你抛向岸边。这种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要看准海浪的时机,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要识得暗含杀机的海浪,因为你一旦裹到里边,就会
被卷人海底,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下榻的客房周围种满了香蕉树,——可这香蕉像菠萝一样令人失
望。我曾想象着随手从树上摘下个香蕉尝尝。檀香山的香蕉可不是这种吃法。
那是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还泛青就被砍下来。然而,虽不能从树上随手可
得,但总还是可以尝尝许多闻所未闻的品种。檀香山的香蕉有十来个品种:
红香蕉,大香蕉,被称做冰淇淋的瓤白而酥软的小香蕉,菜香蕉等等。苹果
香蕉则味道独特。
夏威夷人也有些令人失望。我曾把他们想象为美的造化。一开始,姑娘
们身上散发出的刺鼻的可可油味就令我不快,而且许多姑娘长得并不漂亮。
热气腾腾的丰盛炖肉更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一直以为波利尼西亚人多以各种
美味浆果为生,可他们对炖牛肉狼吞虎咽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
假日要结束了,一想到又要为工作所累,我们都长吁短叹。旅途开销也
有些让我们担心。檀香山是个费用昂贵的地方,吃喝要比想象的贵两倍。租
赁冲浪板,给雇童小费——处处要破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过得去。可是
该是为将来考虑考虑的时候了。我们还要去加拿大,阿尔奇的一千镑花得很
快。船费已付清。因此不必多虑。我去加拿大,回英国都不成问题,但是我
在加拿大的旅行生活费用尚没有着落,这如何是好?但是我们把它置之脑
后,继续不顾一切地冲浪玩,简直玩得忘乎所以。
这时,我已察觉到脖颈和肩膀上的病痛。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右臂疼得
钻心,使我难以再入睡。我患了神经炎,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持续了三四个
星期。
贝尔彻见到我们时,竟毫无怜悯之心。他似乎对我们的假日满心忌妒。
我们每次出游,他都说:“到处溜达,不干正事。天哪,这么准备旅行可不
行,总是花钱雇人不干事!”而他对自己在新西兰玩得不亦乐乎和朋友难舍
难分却从来只字不提。
我们商定我放弃去新斯科舍和拉布拉多半岛旅行,钱一告罄,我就去纽
约。那时,我到卡西婶母或梅姨家去住,阿尔奇和贝尔彻去视察银狐业。
我想大概是在温尼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看高粮仓。我们本应知道患有
痿漏的人是不能挨近高粮仓的,但是我俩谁也设想到这一点。那天他回来后,
两眼淌泪,一脸病容,弄很我惊惶失措。第二天,他强挨着到了多伦多,一
到那儿就躺倒了,要他继续旅行是办不到了。
又过了四五天,阿尔奇恢复了健康,虽然还有点虚弱。
我们找到了遭人恨的贝尔彻。我记得大概去渥太华,正是秋天,枫叶金
黄。我们借住在一位中年船长家,他是个富于魅力的人,养了条逗人喜爱的
阿尔萨斯狗。他曾带我坐在狗拉的车上去逛枫树林。
离开渥太华,我们去了落基山脉、露易丝湖和班夫。每逢问到哪里是我
曾见过的最美的地方时,我都回答说露易丝湖,宽广、修长、湛蓝的湖面,
两岸低矮的丘陵,山随水势,景色壮观,尽处与雪山迢迢相接。在班夫,我
交了好运。神经炎依然作痛,我决心去试试许多人都说对此有好处的温泉水。
我每天早晨洗一会温泉,那地方像个游泳池,走到一端就能感到从温泉汩汩
涌出的硫磺味十足的泉水。我任凭泉水冲洗着我的脖颈和肩膀。令我高兴的
是,到第四天神经炎症状消失了,彻底地治好了。摆脱了病痛再次使我高兴。
接着我和阿尔奇到了蒙特利尔。我们又得兵分两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
视察几家银狐农场,我乘火车南下纽约。这时我已身无分文了。
亲爱的卡西婶母在纽约接我。她待我温厚、慈爱、亲切。
我和她一起住在她里费赛得街的公寓里。她那时年事已高——我估计快
八十了。地带我去看望她弟媳皮尔庞特·摩根家年轻的一代,还带我去一家
高级餐馆品尝美味佳肴。
她谈起了我父亲以及他初来纽约的日子。我过得很开心。临走前,卡西
婶母问我临别有何要求,我告诉她我渴望去自助餐厅吃顿饭。英国人对自助
餐厅一无所知,我是在纽约看了报才了解到的,想去试试。卡西婶母觉得这
是个不一般的愿望。她想象不到谁会想去自助餐厅,但由于她一心想让我高
兴,就带我去了。她说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去自助餐厅,拿着餐具从柜台上自
己选莱,我发现这种经历既新鲜又有趣。
与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见面的这天终于到来了。我盼着他们的到来,
因为尽管卡西婶母待我和蔼可亲,可我仍然感到像只被困在金笼子里的小
鸟。卡西婶母从未想到让我独自一人出去走走。这对在伦敦四处闲逛惯了的
我可真非同一般,我被困得焦躁不安。
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登上贝伦加里亚号启程回
英国。我不敢说再次坐船旅行已能适应,但这次我只是稍稍有点晕船。突变
的天气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正在打桥牌,贝尔彻坚持要和我搭档,我可
不情愿,因为尽管他牌打得不错,可一输就脸色阴沉。我本打算玩几局就散
伙,于是就和他搭档玩起来。谁料想一直打到最后一局。那天海风猎猎,轮
船前后颠簸。我没敢想中途退下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在牌桌前不要出丑。可
能是最后一局,发牌时贝尔彻突然大骂一声,把牌摔在桌上。
“这局输定了,”他说,“输定了!”他怒骂着。我估计再稍有不快他就会
摊牌认输,让对方轻取这局。然而,我倒有满手的好脾。我的牌技槽透了,
可牌争气,不能输掉。我由于晕船一阵阵恶心,打错了牌,忘了将牌,干尽
了费事——但是我手气好极了。
我们终于赢了这局。随后我便回到客舱,声音凄凉地呻吟着直到抵达英
国。
2
回到家本应是愉快的团聚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搅碎了这个好梦。我们
一贫如洗了。
阿尔奇给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职位已被另一个年轻人取代
了。当然,我手头还有可从祖父的遗产中提取的进款,我们可以靠这一百镑
年金过活。可是阿尔奇不愿动用积蓄。他得找个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赶在
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周的食品账单之前。找工作并非易事一一事实上
甚至比战争刚结束时更难。幸运的是,如今我对那段艰难的日子的记忆已淡
漠了。我只记得日子过得不舒心,因为阿尔奇整日愁眉苦脸,他不是那种能
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记得他在我们才结婚时曾警告我说:
“记住,我不是个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