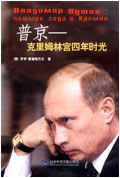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不久才从那儿回国。饭后,他妻子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一起闲聊。她说,人
们总是说巴格达是个可怕的城市,但她和她丈夫却迷上这座城市。他俩讲述
了它的概况,使我对它愈发感兴趣。
我说去那得坐船吧。
“可以坐火车——乘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
我一辈子都想坐坐东方快车。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旅行时,东方快
车经常停在加来车站。我多想登上它。东方快车——米兰,贝尔格莱德,伊
斯坦布尔。。我动心了。
豪中校给我写下了在巴格达该去的游览点。
“在阿尔韦亚和梅姆一萨希伯斯等不要耽搁太久。去摩苏尔、巴土拉转
转,还一定要去乌尔参观。”
“乌尔?”我说。我才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看到伦纳德·伍利在乌尔
作出了奇迹般的发现。我虽然对考古一无所知,但一直对此多少有些兴趣。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退掉了去西印度群岛的票,预订
了东方快车的坐位,路线是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大马土革。自大马士革穿过
沙漠到巴格达。我激动异常。办理签证和打点行装需四五天时间,随后就可
以出发了。
第八章 梅开二度
1
坐火车是我平生一件快事。可悲的是如今谁对它也没有了那种如同对好
朋友的亲密感情。我在加来登上了预订的卧铺车,这样免得再到多佛尔,而
且也避免了乘船的疲惫,终于在梦寐以求的火车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到
这时我才意识到旅行一开始就潜伏着危险。和我同车厢的是一个中年夫人,
她是个穿戴华丽,富有经验的旅行者,随身带了许多手提箱和帽箱。她和我
搭上了话。这很自然,因为我俩合住一个包厢,这种包厢像其他二等车厢一
样有两个铺位。在某些方面,二等车比一等车还舒服得多,因为这种车厢空
间大、使人有活动余地。
我的同伴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地去巴格达。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碰巧就
住在巴格达。
她断定我到那住在朋友家,并说她多半也认识他们。我说不住朋友家。
“那你住在哪儿呢?总不会到巴格达住旅馆吧?”为什么不呢?不然要
旅馆干什么用?我至少心里嘀咕着,可嘴上没说。
“啊!旅馆可住不得。你可别那么干。我告诉你应该这样:来找我们!”
我有点吃惊。
这位C 夫人告诉我她丈夫在巴格达,她本人是当地最早的居民之一。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再感谢并补充说我的计划尚未定下来。幸运的
是,C 夫人不和我一起走完全程,这得感谢上帝,因为她的话总是滔滔不绝。
旅行正如所期待的那样。过了的里雅斯特,列车穿过南斯拉夫和巴尔干
半岛,凭窗眺望,眼前是一个景色全异的世界,富有奇特的魅力:掠过峡谷,
望着牛车和别致的运货车,审视着站台上的人群;在尼斯和贝尔格莱德偶尔
下车转转,看着原来的车头被一个涂着截然不同的字母和符号的新的庞然大
物所取代。旅途中自然又结识了几个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不像第一个那
样张张罗罗。我先后遇到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一位荷兰工程师和几位土耳其
女人,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最后—位几乎无法交谈,我俩只断
断续续地用法语谈了几句。我发现自己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而明
显地感到脸上无光。这位夸耀起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十三次怀胎,三四
个流产了。
只有亲身旅行才能认识到大千世界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人们,当然并不总
是事事都遂人心愿。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治疗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
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住在何处严肃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当
心那个城市不安全:“你得留神。
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你。出门在外不
要相信人们说的话。除非你知道带你去哪儿,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
上,他把我看成个十七岁无知的孩子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多
加小心的。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
“去托卡特里安旅馆,”他说,“那是个上好的旅馆。住在那儿相当安全。
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可口的餐馆,就这样。
那是俄国夫人们开的,是些出身高贵的白俄女人。她们烹调技术高超,
在餐馆内举止非常得体。”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
还给我找了个向导。“别从库克斯的公司雇向导,他要价太高、我向你保证
这个向导非常正派。”
我们在俄国夫人穿梭往来、温文尔雅的微笑和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屈尊
俯就的态度中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来,他又带我看了伊斯坦布尔的
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旅馆。我俩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
是不是,”他探询地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
反应后,那种探询更是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
是不问更明智些。”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说,“而且很够朋友。”
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
他是个正派人,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观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
谢他。
第二天,库克斯公司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请我,带我们过了博斯普
鲁斯海峡,到海达帕夏重又乘坐东方快车旅行。我很乐于身边有个导游,因
为海达帕夏车站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着,尖叫着,砰
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
我领教了库克斯公司向导的本事。
“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子,
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儿,这儿。”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
绶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
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我把你上车的事都安顿
妥当了。”库克斯公司的向导说,“那么?”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
我掏出土耳其货币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
你再给我一英镑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吃一堑,长一智,就递给
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差别。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
列车沿马尔马拉海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
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尽管难以描述各自的特征。我感到了人地两生,但
对我的所做所为和我去的地方愈加有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环顾站台,
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不曾见过的熟食卖
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包着叶子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应有尽有。
列车愈往东行,膳食变得愈难以入口,顿顿都是一份油腻而无味的热饭。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门堡①。这是个
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
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景色的确壮
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
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伫立在那儿。
夕阳渐渐西沉,景致美不胜收。来此地我惬意极了,心里充满了喜悦和
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呜,列车沿山谷盘旋而下,穿行于山涧,
又从山下的河谷钻出。就这样,列车缓缓穿过土耳其,从阿勒颇进入叙利亚。
①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脉的山口。--译注
到阿勒颇之前,我却触了霉头。我身上挨了臭虫咬。我一辈子都特别易
遭这种虫子咬。它们藏在老式的木制车厢里,贪婪地吸吮着车上旅客的鲜血。
我体温上升到102'c(华氏,译者注),胳膊也肿了。我发着高烧,头痛,
感到凄惨。然而,那位法国朋友给我很大帮助:他下车买了些葡萄,那种当
地特产的小粒甜葡萄。尽管母亲和姨婆教育我在国外吃东西一定要先洗再
吃,我却把它抛到脑后。每过一刻钟,我就吃点葡萄.这使我热度大大下降。
我对其他什么都没胃口。那位法国朋友在阿勒颇与我分手,到第二天,肿痛
有所减轻,感觉也好多了。
我在列车上又度过了冗长乏人的一天,列车似乎始终以每小时五英里的
速度爬行。
而且总是不断地在环境毫无变化的无名小站停车。列车终于到达大马士
革。车站里一片喧嚷声、搬运工一把夺过我的行李.叫喊着。出了车站,我
看到一辆写着东方宫殿旅馆字样、外观漂亮的汽车。一个穿制服的仪表堂堂
的人救了我和行李的驾。我和其他几个手足无措的旅客一起上了车,汽车驶
向旅馆,那儿已经给我预定好房间。这座旅馆富丽堂皇,宽敞的客厅,大理
石光彩照人,只是电灯昏暗得无法看清周围。
记得我在大马土革呆了三天,这期间我按计划由库克斯公司的人导游,
四处游览。
有一次.我和上了年纪的牧师和一位美国工程师结伴去看了一处十字军
的城堡,工程师对近东都一无所知。我们八点三十分在汽车上首次相遇。那
位老牧师目光慈祥,把我和那个美国工程师当成了夫妻。
老牧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婚姻生活的好处,索取与给予的必要性,并祝
我们幸福。
我俩没做什么解释,或者说曾试图解释,美国工程师对着老牧师的耳朵
大声告诉他我们并非夫妻,最好别管别人的事时,老牧师看上去很沮丧。
“但你们应该结婚,”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摇了摇头说:“姘居,知道吗,
这不合适,这的确不合适。”
我去看了看可爱的贝勒贝克,逛了逛集市和斯特雷特大街,在那儿买了
许多当地制造的令人爱不释手的铜餐具。
我估计现在的大马士革,这种老手艺人和人家存留无几:他们被工厂取
而代之。当时,镶花木箱和桌子已经屡见不鲜,到处都能仿制,仍是手工制
作,采用传统图案和工艺。
进一步的游览只是增强了我返回大马士革的决心,我又去大马士革的许
多地方观光.随后。我踏上了穿越渤海去巴格达的路途。这时,旅行事务由
奈恩运输公司承办。该公司拥有由六轮汽车组成的车队,格里·奈思和诺尔
曼·奈思兄弟俩负责。他阀原籍澳大利亚,都很豪爽。我是临行前一天晚上
结识他俩的。
汽车黎明时分出发。两个身材魁梧的年轻司机正忙碌着。我跟在行李后
面出来时,他们正忙着把几支步枪塞进汽车,随手用一抱毛毯盖祝这时,一
队人来到旅馆的台阶下。
使我惊奇但不一定高兴的是,领头的不是别人,就是在的里雅斯特分手
的那位C 夫人。我还以为由于我在这盘桓游览,此时她已经到巴格达了呢。
“我猜想你就会走这条路线,”她面带笑容地和我打招呼,“一切都安排
好了,我带你去阿尔韦亚,巴格达的任何旅馆都不适合您祝”我还能说什么
呢?我像是陷入樊笼。
我从未到过巴格达,更没见过那儿的旅馆。就我所知,它们会乌烟瘴气,
充斥着臭虫、跳蚤、虱子、蛇和那种我特别厌恶的灰蜂螂。于是我不得不结
结巴巴地表示感谢。我俩安顿下来,我意识到“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就是
我这个朋友C 夫人。她拒不坐在她的座位上,那儿靠近尾部,她坐在那儿会
晕车。她要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而那个座位已被一位阿拉伯妇女一星期
前预定了。那位阿拉伯妇女上了车,坚决不让出那座位,她的丈夫也一旁帮
腔。随后便是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一位法国妇女也要坐那儿,一个德国将
军也似有此意。我弄不清楚都吵嚷些什么,但世风如此,四人中的弱者失去
了好座位,被赶到车尾。德国将军、法国和阿拉伯妇女都带上了遮沙面罩,
C 夫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留了下来。我从不会吵嘴,而且不会把握时机,不过,
我的座位号实际上是很理想的。
汽车按时开出。我出神地望着汽车隆隆驶过黄色的沙漠,起伏的沙丘和
戈壁,格调单一的景色终于使我昏昏欲睡,我随手翻开一本书。我从不晕车,
但现在的座位靠近车尾,这六轮汽车的颠簸又如同海上的轮船一样,就这样
在颠簸中看着书,我不知不觉地就晕车了,而且很厉害。我觉得丢了面子,
可C 夫人倒还体贴地对我说,晕车常常事先想不到,下次地会关照给我找个
靠前的位置。
四十八小时穿越沙漠的旅行既令人着迷又充满凶兆。
人们这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被罩在真空之中。使我深有感触的首
先是,正午时分根本辨不出东南西北,听说就是在这个时辰,巨大的六轮汽
车常常迷失方向。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除浩确的沙漠之外别无他物,根本谈不上路标。
漫漫旅途只有一个释站,鲁特巴大城堡。
估计大约是午夜时分到了那里。冥冥夜色中,蓦地出现了闪烁的光亮,
到驿站了。
城堡的大门打开了,门旁黑洞洞的枪口警惕地对着我们,那是骆驼队的
士兵在警戒,提防伪装成旅客的土匪。他们深色的粗犷的面庞令人胆战心惊。
经过详细检查才放我们进入城堡,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里面有几间摆放
着床铺的屋子,我们五六个妇女在一间屋子里休息了三个小时后就又起程
了。
大约是清晨五六点钟,晨熹微露的时刻,我们吃了早饭。沙漠披着一层
朝晖,淡紫、杏黄和湛蓝,加上冷丝丝的空气,使人感到奇妙无比。这正是
我求之不得的良辰美景。
它使人忘掉尘世。面对清晨纯净爽人的空气.静谧、甚至不闻鸟语,细
沙从指缝中流下,远方旭日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