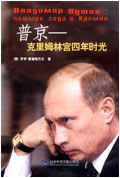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求之不得的良辰美景。
它使人忘掉尘世。面对清晨纯净爽人的空气.静谧、甚至不闻鸟语,细
沙从指缝中流下,远方旭日冉冉升起,此时品尝着香肠、香茗。人生还有何
求?汽车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畔费路查,从船只搭成的浮桥上
过了河.经过哈巴尼亚的航空维修站,继续前行,直到看得见棕榈树丛和一
条凸起的公路。往前走又过了一座浮桥,渡过了底格里斯河,进入了巴格达
市,首先映于眼帘的便是一条两边是招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衔道,街道中似乎
矗立着一度青绿色圆顶的漂亮的清真寺。
我根本没机会去看旅馆的情况。C 夫人和她丈夫带我上了一辆舒适的轿
车。沿着巴格达驶去,经过莫德将军塑像,出了城,路两旁是行行棕榈,成
群漂亮的黑色水牛在水塘中游憩。完全不同于刚才的景色。
2
在巴格达,他们夫妇俩待我很热情。大家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很愉快。
我为自己曾有过身陷樊篱的预感而惭愧。阿尔韦亚现在已成为市区的一部
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流不息,可在当时,它还距离城市中心几英里远
呢。
一天。我搭车去水牛镇游览。这个镇子如今乘火车从北面进入巴格达时
仍可看到。
在陌生人眼中,它看—上去似恐怖之地.破屋陋舍,巨大的围栏里满是
水牛及粪便,奇臭难闻,汽油筒搭成的棚舍使人相信这是贫困和耻辱的缩影。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水牛的主人们生活得满不错,尽管他们住得邋里邋遢,
但是一头水牛价值一百多英镑,如今就更值钱了。水牛的主人自认为很走运,
女人们在烂泥中踽踽而行时.脚踝上饰戴着的漂亮的银制脚镯和绿松石显露
可见。
我不久就听到有人说在近东看到的一切都得打折扣。
一个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观察和行动,都得颠倒重新研究。看到一个
男人粗鲁的打手势叫你走开,你忙跑开了。实际上他在邀你过去。另一方面、
假如他向你招手,那就是让你走开。远远地面对面站着两个人,冲着对方大
喊大叫,颇有立刻就杀死对方的架势,其实不然。这是兄弟俩无聊地打发时
光,提高嗓门是因为谁也懒得向前迈那两步路。
阿尔韦亚的人们待我极为友好。打网球,开车去看赛马,带我去观光,
逛商店,我感到就像在英国一样。从地理上看,我在巴格达,而精神上我仍
在英国;我出游的想法就是离开英国去看看异国风光。我打定主意得改变一
下。
我打算去访问乌尔。我询问了一下,高兴地发现他们并不阻挠我,而是
鼓励我去。
旅行都安排好了,而且带了不少不必要的装饰品。
我如期出发。对给我背东西的家伙,我略怀戒心地盯着他。他细高的个
子,带着一副陪着夫人们走遍近东,比她们本人还了解应该如何是好的神气。
他穿着鲜艳的衣服,把我安顿在那光秃秃的不太合适的车厢中,对我行了个
额手礼,就走了。临走时向我解释说,到适当的车站他会来带我去设在站台
上的餐厅用餐。
那些年,我坐车旅行到乌尔车站的钟点时有变化,可是时间总是不凑巧。
这一次大概在早晨五点。在像乌尔这样的考古发掘颇有成果的地方,人们每
分钟都在疲于奔命地忙碌着,弄来不少兴致勃勃的妇女四处闲逛是最可气的
事了。伍利夫妇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游客们结伴观光,由导游陪着去值得
一看的地方,随后匆匆返回。我却被视为贵客受到热情接待,我应该对此倍
加感谢才是。
这种优待完全是由于伦纳德·伍利的妻子凯瑟琳·伍利刚刚读过我的《罗
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的缘故。她对此书津津乐道,所以我也受到像接待
重要人物那样的款待。
她还询问同行的其他游客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有谁还没看过,她就极
力地推荐。
伦纳德·伍利态度殷勤地陪我参观,伯罗斯神父是个耶酥会神父和碑铭
研究专家,他也带我四处游玩。这人是个见解独特的人物,他描述事物的方
法与伍利先生形成有趣的对照。伦纳德·伍利用充满想象力的眼光看待一切:
这地方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一千五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模样。我们每到一处,他
就能使其活起来。他讲解时,我会毫不怀疑地确信某个角落的那间房子就是
亚伯拉罕的故居。这是他对历史的再创造,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谁听到他
的话都会相信他的解说。伯罗斯神父的口才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
来的。他总是以一种充满辩解味道的语调来形容院落、教堂或商业区。
一次午餐时,他对我谈起他觉得我可以写篇很好的侦探故事,他极力主
张我动笔。
直到那时,我对他爱看侦探小说还全然不知。他勾勒出的这个故事,虽
说实际上还是个轮廓,却多少描绘出了一个曲折的故事画面,我拿定主意有
一天会动笔的。过了许多年,大概在二十五年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情节完
整的故事又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把它加以组合安排,写了一篇篇幅很
长的短篇小说。伯罗斯神父那时早已去世,但我希望他天上有灵,我是怀着
深深的谢意采用他的构思的。像任何作家那样,我把它融合在我的构思之中,
他的痕迹很难看得出来,可他的灵感是这篇小说的源泉。
凯瑟琳·伍利后来与我结成莫逆之交。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人们总是
有一半对她恨之入骨,另一半则为之倾倒,这或许是由于她的情绪飘忽不定,
令人难以把握。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如果需要与一位妇女结伴去沙漠,
或是其他什么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那么她会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你的旅行情
趣盎然。她谈论的事决不是一杯白开水,她会促你沿着一个崭新的思路去考
虑问题。地不会矫揉造作,但只要她想博得你的高兴,她就办得到。
我爱上了乌尔这块地方。傍晚美丽的景色,宝塔式建筑耸立着,夕阳半
遮半映、浩确的沙海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颜色,杏黄、瑰红、湛蓝、紫红,
我喜爱那儿的工匠,带班的,挎篮子的孩子,考古发掘者,他们的手艺和生
活。历史的吸引力摄取了我的心灵。
目睹从沙中慢慢发掘出一柄熠熠闪光的匕首,真是富于浪漫色彩。望着
从沙中小心翼翼地捧出陶罐和其它器皿使我也心血来潮要做个考古工作者。
我想,我一直过着一种无意义的生活是多么地不幸呵。这时,我羞愧地回想
起在开罗我还是个姑娘时,母亲极力劝我到卢克苏尔和阿斯旺一览埃及的辉
煌历史,我却醉心于和小伙子们约会跳舞跳到凌晨。
我想现在一切还为时不晚。
凯瑟琳·伍利让我那个佣人先返回巴格达,说我何时回去还不一定。这
样,我可以避开那位热情的女主人的注意返回巴格达,从而毫无顾忌地住到
了底格里斯王宫旅馆。
那家旅馆毫不逊色。首先穿过一片昏暗,那是休息厅和餐厅,总是挂着
窗帘。二层楼每间客房都有阳台、就我所知,任何一个过路人都能从那儿望
见屋里,你躺在床上也罢,整日里人们总是来来往往的。这家旅馆的一侧濒
临底格里斯河,河上千舸竞帆.宛如仙境一般。
促成我旅行的那对举止文雅的豪夫妇曾给我推荐过一两个人。我估摸这
些人不好交际,而只是被介绍给他们自己认为值得结识的人。这些人曾陪他
们去看了城市的名胜。
尽管阿尔韦亚英国味十足,但巴格达仍是我见到的第一座东方城市,纯
东方化的。从拉希德大街转弯,拐进窄小的衔巷,就会来到格调迥异的伊斯
兰集市:铜器摊前钢匠们敲敲打打,香料市摊放着各种香料。
豪夫妇的一位朋友,莫里斯·维克斯是个英印混血,自己过着独居的生
活,他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引我去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集市闲逛。我俩穿
过棕调树丛和枣园到河边散步,也许我对他的谈吐比眼中所看到的更感兴
趣。从他那儿我才第一次学会考虑时间的概念。我以前没有从非人格的角度
考虑过时间的问题。但是对他来说,时间以及时间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旦你考虑到时间及其无限性,个人的东西就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
你了。悲哀、苦难,所有生命中有限的东西部以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了。”
他问我是否读过邓恩①的《时间试验》,还借了一本给我,从那时起,
我发现自己有了某种变化,不是内心变化,由不是外表的变化,而是我看待
事物更客观了,在一个充满着内在联系的大千世界里,我自己不过是沧海一
粟。人们可以不时地把握自己,从另一个既有的平面上观察自己的存在。
①邓恩(1867— 1936)美国幽默作家和新闻记者。--译注
开始时会很笨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舒适感和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对宁静的真切理解。
对其里斯·维克斯,我感谢他引导我心胸开阔地面对生活。他藏书很多,
有哲学及其他各方面的,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时我怀疑我俩还能否
再次见面,我觉得不见面也知足了。我俩就像黑夜里撩舷而过的两艘航船。
他递过一件礼物。我接受了。这是一件不曾有过的礼物,因为它是智慧的礼
物。它来自头脑,而不仅仅来自心灵。
我不能在巴格达再呆下去了,因为我急于赶回家准备过圣诞节。
在旅馆里,我结识了皇家非洲步枪队的德怀尔上校。他到过世界许多地
方。他上了年纪,对中东的事无所不知。我俩的话头是从肯尼亚和乌干达开
始的,我提到我的哥哥曾在那儿住了许多年,并告诉他我哥哥叫米勒。他审
视着我,随之脸上浮现出一种我已熟悉的表情,一种充满疑问神情。
“你是说你是米勒的妹妹?你哥哥是烟鬼比利·米勒?”我从没听说过
烟鬼比利这个绰号。
“疯疯癫癫的?”他探询地补充说。
“是这样,”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你比他年纪小多了,是不是?”
“比他小十岁。”
”他出门时你还是个孩子吧?”
“对。我对他不熟悉,可他放假时常回家来。”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曾听说他住进了医院,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介绍了我哥哥的生活的情况,他如何被送回家等死,虽然医生说他活
不多久了,可他又活了几年。
我和德怀尔上校从此结为好友。有时我去他那里吃饭,有时他来我旅馆
进餐;我们的话题总是扯到肯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
以及我哥哥的一些轶事上。
德怀尔上校以一种专横和军事化的方式给我安排了下次出国旅行的游玩
日程。“我给你安排了三次旅行,”他说,一旦你合适,我又脱得开身,我就
跟你定下时间。我想到埃及什么地方碰头。”接着他把旅行计划讲给我听。
我脑海里时常出现疑窦:这样的日程安排我身体吃得消吗?也许,我们
俩人都知道这种安排不过是想想而已。他是个孤僻的人。德怀尔上校行伍出
身,过着严格的军旅生活,而且渐渐地与不愿离开英国故土的妻子产生了隔
阂。据他说,她所关心的就是在幽寂的路边有所清静的小房子过日子;他的
孩子对他回家休假毫无亲热的表示。他们认为他去原始地区旅行是荒唐的。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天气渐渐地变了。炙人的太阳见不到了,甚至偶
尔会下场雨。
我订了回国的票,可能我会怀着遗憾之情告别巴格达,但也不尽如此,
因为我已经制订了重返巴格达的计划。
3
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搭乘劳埃德·的里雅斯蒂诺号船去贝鲁特旅行。
在那儿住了几天,再次随奈恩运输公司的车队穿越沙漠。船离开亚历山大勒
达沿海岸航行。海面波浪起伏,我身体有些不适。在船上,我注意到另一位
妇女,这位叫西比尔·伯内特的妇女后来告诉我,她也不习惯于颠簸的海浪。
入们通常叫她鲍夫·伯内特,是当时的空军少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的妻子,
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和丈夫团聚。她是个很有见地的女人,心直口快,爱好
旅行和观赏异国风光,她在阿尔及尔有一套漂亮的住宅。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些英国天主教徒,她们去伊拉克瞻仰《圣经》中提
到过的地方。
领头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女人,叫威尔布里厄姆婶婶,西比尔·伯内特
说她活像个大甲虫,说得太对了。她是个人人都想和她作对的女人。
我们到了巴格达,我拜会了几位老朋友,在那痛快地玩了四五天,随后
就接到伍利夫妇的电报,去了乌尔。
这年六月,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们,当时他俩回家探亲,我还把刚刚买下
的克莱丝威尔街巷中的一幢小房子借给他们祝就在他俩修缮房屋时,他们为
我安排了一项迷人的计划。
我在初夏前一星期左右到了乌尔,待他们收拾好行李后,就和他们一道
走,穿过叙利亚,直奔希腊,能和他俩同行去希腊的德尔法,我很高兴。
我顶着沙漠风暴到了乌尔。以前在那儿旅行曾遇到过沙漠风暴,但这一
次更猛烈,持续了四五天。我从没领教过四周到处弥漫着沙粒的情景。尽管
窗户紧闭,还挂着防蚊帘,可到了晚上,床上仍是一层沙子。虽然睡前到门
外抖干净,但次日早晨脸上的沙子还是不少。整整受了五天的罪。
然而我们却谈天说地,大家一团和气,我在那儿过得有滋有味。
伯罗斯神父又到了那里,还有建筑家威特伯恩,这次还有伦纳德·伍利
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他已经当了五年助手了,可前一年我来时他刚好不
在。他是个身材削瘦,皮肤黝黑的青年人,沉默寡言,极少开口,但对自己
分内之事极为熟悉。
我很快看到他善于处事。他和工匠们关系融洽,更难为他的是,把凯瑟
琳·伍利哄得团团转。凯瑟琳对我说:“马克斯当然是个出色的助手。我不
知道要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