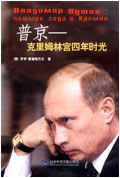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害怕结婚。我认识到,许多女人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即在生活中惟
一能伤你心的人只有自己的丈夫。再没有更亲近的人了。再没有比每日相伴
的亲人更叫人依赖的了,而这就是婚姻。我拿定主意决不把自己托付给别人。
在巴格达,一位空军朋友说过一些令人不安的话。他讲述了自己婚姻的
坎坷,最后说道:“我觉得生活都安顿下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了。
但是最终出点纰漏。
或者找一个情人,或者找几个情人。
要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
有时,我心神不定地认为他的话是对的。但是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比结
婚强。几个情人不会伤你的心,而只有一个情人往往会令你伤心,但也不是
像丈夫那样叫人心碎.对我来说,丈夫成为过去。当时,我脑子里不考虑任
何异性。但是,我那位空军朋友的话也不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
使我惊讶不已的是即使没明确宣布和丈夫分居或离婚,人们也会不厌其
烦地问起这件事。一个小伙子曾用认为我毫无道理的口吻对我说,“你已经
和丈夫分居了,或许还将和他离婚,那么你还祈望得到什么呢?”开始时,
我也弄不清自己对人们这种关心是高兴还是气恼。我想基本上是高兴的。另
一方面,它有时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一位意大利人就是这
样。这是我不懂意大利人的习惯而自作自受的。他问我船上夜里装煤的声音
是否搅得我睡不着觉。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因为我的卧舱在船的右舷,不临
码头一边。
“噢,”他说,“我想您是三十三号卧舱吧。”
“不是,”我说,“我的是个偶数:六十八号。”
在我看来,这话无可挑剔吧?可是没想到问你卧舱号的意大利的习惯,
意思是能否去你卧舱。随后他没说什么。可午夜过后,这位意大利人来了。
滑稽场面也随之出现。
我不懂意大利语,他不通英语。于是我俩用法语压低嗓音叽叽喳喳地争
吵起来,我很生气,他也很恼火。我们是这样说的:“您怎么敢到我的卧舱
来?”“您邀请我来的呀。”
“没有的事。”
“您邀请了。您告诉我您的卧舱号是六十八号。”
“不错,可那是由于您问我的。”
“当然是我问的,我问您是因为想到您卧舱来,您告诉我可以来。”
“我没有。”
我俩吵了一会,声音时高时低,最后我让他别作声了。
我相信隔壁卧舱的使馆医生和夫人会对我妄加猜测的。我气愤地撵他
走,他坚持要留下来。最后他恼羞成怒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于是我向他道
歉,说我的确不知道他当时的问话实际隐含的其它意思。我最后终于把他赶
走了。尽管他仍忿忿不平但却弄清楚了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走到哪混到哪
的女人。第二天早晨,使馆医生的太太冷冷地白了我一眼。
没多久,我就发现罗莎琳德从一开始就以很实际的态度掂量我的每一个
求婚者。
“嗯,我想你肯定会再结婚的,我自然要关心那个人是谁。”她向我解释
说。
马克斯此时从法国他母亲那儿回来了。他说在大英博物馆找份工作,并
想知道我是否在伦敦。刚好我的出版人科林斯准备在萨伏依举行一次大型宴
会,特别邀我去见见出版我作品的美国出版商以及其他一些人。那天的会面
排得满满的,于是我乘晚车去了伦敦,邀请马克斯来吃早饭。
我一想到要与他重逢就感到兴奋,但奇怪的是,他的到来竟使我窘迫不
已。在那次结伴旅行中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我难以想象此次相会为什么使
我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他看来也有些拘谨。可待我俩吃完我亲手制做的早餐时,我们又恢复到
老样子。令人高兴的是我没有和他失掉联系。
继《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后,我又在写《七面钟之谜》。这是我
以前那本《名苑猎凶》的续集,属于被我称之为“轻松惊险小说”那类书。
这种书容易一挥而就,无需太多的情节和构思。
此时我对写作又恢复了信心。我觉得每年写一本书不成问题,还能写几
篇短篇小说。
那时,我写作的直接动力就是能赚到钱。写一篇小说,就可以带来六十
倍的收入,扣除所得税,当时每英镑扣四至五先令——这样,足足四十五英
镑就归自己了。这极大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
当时是个讲求实际的年代,我成了一个手头阔绰的人。
我的作品在美国连载出版,其收入远比在英国的连载权的收入可观。而
且还免征所得税。这被认为是资本的收入。我并没即刻得到这笔稿费,但我
可以感到财源不断,在我看来,要做的事就是不顾劳累地赚钱。
我常常觉得现在不妨只字不写,因为一动笔就招致一堆麻烦。
马克斯到了德文郡,我俩在帕丁顿见了面,乘晚车回到家。
和马克斯又见面了,我真高兴。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亲密,
几乎不用开口就明白对方的意思。第二天晚上,我和马克斯互道晚安后,我
就在床上看书。这时,有人敲门,接着马克斯走了进来,这出乎我的意料之
外。他手里拿着一本我借给他的书。
“谢谢你借给我这本书,”他说,“我很喜欢。”他把书放在床边,随后坐
在床头,深情地望着我:他说要娶我作妻子。
第二天他乘车离开,我去送他时,他说:“你肯定会嫁给我的。”
这时天刚蒙蒙亮,我不能继续和他争辩。望着他远去,我感到茫然不知
所措,悒悒回到家。
我问罗莎琳德是否喜欢马克斯。
“当然喜欢,”她回答说,“我非常喜欢他,比R 上校和B 先生还要喜欢。”
我相信罗莎琳德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只不过是出于礼貌而不挂在嘴边罢
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是多么难熬埃我感到凄然怅惘,脑子里一片混乱。起初,
我曾决计不再结婚,我得有保障,不再受任何伤害;没有比嫁给一个比自己
年龄小得多的人更蠢的事了;马克斯年轻,还不了解他自己;这对他不公平,
他应该娶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我刚刚尝到了独立生活的甜头。后来,这些
论点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变了。不错,他是比我年轻,但我俩共同点太多了。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转变。假如初次见面我就想到马克斯可能会成为我
丈夫的话,我就会倍加小心,决不会轻而易举地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我没
料到竟会发生这种事,俩人都心情愉快,在一起交谈是那样的充满乐趣,无
拘无束,仿佛是一对夫妻一般。
就在这一等莫展之际,我向我的神灵请教。
“罗莎琳德,你认为我再结婚如何?”
“嗯,我料到你会这样的,”罗莎琳德以一种始终明察秋毫的口气说话,
“我的意思是,这事很自然,对不对?”“唔,也许对吧。”
“我可不赞成你跟R 上校结婚。”罗莎琳德若有所思地说。这倒挺有趣,
因为只上校过份地宠着罗莎琳德,他为讨她高兴而和她玩游戏玩得似乎很开
心。
我说出了马克斯的名字。
“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了。”罗莎琳德说,随后又补充说,“我们可以自
己弄条船,行不行?他可就派上用场了。他网球打得不错,是吧?我可以和
他打网球了。”她毫无顾忌地设想着,完全是从她个人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出
发。
尽管如此,那个夏天仍是我一生中最难提的。人们纷纷反对我和他结婚,
也许这实质上给我增添了勇气。我姐姐坚决不赞成:年龄差别!甚至我姐夫
詹姆斯也委婉地道出要我慎重从事的告诫。
我终于把消息透露给伍利夫妇。看上去,他们都很高兴。莱恩当然不必
说了,可凯瑟琳总是捉摸不透似的。
她不容置否地说:“只是你两年之内决不要嫁给他。”
“两年之内?”我沮丧地道。
“对。这是命里注定的。”
“哦,我认为这样不明智。我已经比他大许多了,年龄愈来愈大,结婚
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还是应该让他享受生活的甘美才好。”
“我认为这对他毫无益处。”凯瑟琳说,“对他这种年龄的人毫无好处可
言,他会认为万事如意的。我认为最好让他等两年,不能再短了。”
这个主意我不敢苟同,这似乎是个严厉的清教徒的观点。
我的婚事弄得满城风雨,给我带来了难堪,于是我想尽量地不再声张了。
我们商定卡洛和玛丽·费舍还有罗莎琳德跟我们一起去斯凯岛,在那里住三
个星期。我们的婚事预告将在那儿公布,在爱丁堡的圣哥伦教堂举行婚礼。
随后,我带马克斯去探望宠基和詹姆斯,詹姆斯虽然没有提出异议,但
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宠基仍极力阻止我们的婚事。
在列车上,我几乎反悔。马克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家里情况。
“你说的是詹姆斯·瓦茨吗?”他问,“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叫詹姆斯·瓦
茨,那是你姐姐的孩子?他可是个绝妙的喜剧演员,极擅于模仿人。”
听说马克斯和我的外甥是同届同学,我简直要坚持不住了,我俩的婚事
似乎毫不可能了。
我绝望地说:“你年龄太小了,太小了。”
这次马克斯真的害怕了。
“根本不小。我上大学的确年纪不大,可我的同学都说我很老成,我和
瓦茨那帮人根本不同。”但是我在良心上仍感到不安。
宠基竭尽全力要说服马克斯,我都怕会引起马克斯的讨厌,事实恰恰相
反。他说她是那么真诚,那么急切地渴望我幸福。人们对我姐姐的断语总是
如此。
临别时,宠基泪如泉涌,不再说话。詹姆斯向我很宽厚地告别。好在我
外甥杰克没在家,不然会把事情弄糟的。
“当然,我一眼就看出你打定主意要嫁给他,”我姐夫说,“我知道你不
会改变主意。”
“嗨,简,你不知道,我奸像每天都在变来变去。”
“这倒未必。我希望你会一切随心。这不是我所希望你选择的,但你总
是很有眼力,我觉得他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年轻人。”
我多么喜爱亲爱的詹姆斯啊,他总是那么苦口婆心,“别理会宠基,你
知道她的为人,生米煮成熟饭她就会改变看法的。”
我问宠基能不能去爱丁堡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认为最好是不去。“我会
哭出声的,扫大家的兴。”我为此由衷地感谢。
在圣哥伦巴教堂内举行婚礼后,我俩仍分居两地,像古老的歌谣说的那
样,我们在教堂前的草坪上分手了。马克斯回到了伦敦以便三天内完成乌尔
的研究,而我则在第二天和罗莎琳德一起回到了克雷斯威尔,在那儿忠诚的
贝西迎接我,她还蒙在鼓里。马克斯两天后坐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克雷斯威尔
门口,我们乘车去多佛尔,从那里渡过海峡去我们蜜月的第一站:威尼斯。
蜜月是马克斯一手安排的。我相信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沉浸在蜜月的幸
福之中。惟一与蜜月不和谐的就是东方快车上的臭虫,甚至在到威尼斯之前,
它们就从木板下钻出来,频频袭扰我们。
第九章 共同生活
1
蜜月期间,我们游览了杜布罗夫尼克,从那儿又到了斯普利特。我永远
忘不了斯普列特。傍晚时分,我们从旅馆出来散步,当走到个广场的转弯处,
看到圣·格雷戈里的巨影耸入云霄,这是雕塑家梅斯特罗维奇的杰作。它俯
瞰着万物,像是永恒的里程碑在人们记忆中难以磨灭。
旅行的下一步是顺达尔马提亚海岸而下,沿希腊海岸到达帕特雷。我们
搭乘的船是只小货轮,船上总共才有四名乘客,我俩住一间客舱,另外两人
在另一间客舱。他们到下一站就下船了,于是剩下我们两个乘客。
我从没在船上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切成薄片的美味羊肉,非常鲜嫩,新
鲜蔬菜、米饭、烤肉扦上满是香喷喷的调料。我们和船长结结巴巴地用意大
利语交谈着。他问道:“喜欢这饭荣吗?我很高兴为你们安排英国式饭荣,
这是地道的英国式饭菜。”
但愿他别到英国来,以免他会看到真正的英国饭莱。
我们在这条塞尔维亚小船上愉快地过了几天,船不时地在沿途港口停
靠,圣安娜、圣毛拉、圣地夸拉塔等等。我俩上岸前,船长总是提醒我们开
船前半小时鸣气笛。于是当我们俩倘徉在橄榄树下或坐在百花丛中,耳边会
突然响起笛声,我们便急忙转身跑回船。坐在橄榄丛中,四周一片静谧,我
俩沉浸在幸福中.此情此景多令人惬意啊,简直是在伊甸乐园,人间天堂。
终于到了帕特雷,我们愉快地告别船长,坐上滑稽的小火车去奥林匹亚。
希腊无须多谈。奥林匹亚正如想象那般美丽。第二天我俩骑着骡子去安
德里策纳,坦白地说,这几乎使我们的婚姻出现危机。
我以前从未骑过骡子,十四小时的路程带来难以置信的痛苦。我竟到了
分不清骡子与步行两者之间哪一个更痛苦的地步。到目的地后,我从骡子上
滑了下来,腿脚僵直得难以走路,我责怪马克斯说:“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经
过这种跋涉后的痛苦,你就没资格结婚。”
我们在安德里策纳休息了两天来恢复体力。我承认嫁给他并不后悔,他
也可以学一学如何照顾妻子,仔细地计算路程之后再请妻子骑骡子旅行。我
俩到巴萨神庙又骑了近五小时的骡子,可这一次我毫不感到劳累。
埃皮德奥鲁斯在我眼中绮丽极了,但是在那儿我第一次领教了考古学家
的性格。那天天气很好,我攀到剧场高处坐下,把马克斯一人撇在博物馆里
看碑铭。过了很久,他还没来找我。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下来走进了博物馆。
马克斯仍直挺挺地俯卧在地上,蛮有兴趣地研究铭文。
“你还在看那玩意儿?”我问他。
“嗯,这很罕见,”他说,“你看这儿,我给你讲讲好吗?”“我想用不着,”
我语气坚定地说,“外面美极了,真称得上是赏心悦目。”
“嗯,我相信一定是这样。”马克斯心不在焉地说。
“我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