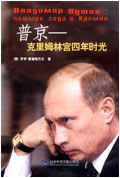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我相信一定是这样。”马克斯心不在焉地说。
“我再出去你不会介意吧?”我问。
“不会,”马克斯略带惊奇的口吻说,“这很好,我还以为你对这铭文感
兴趣呢。”
“我想这不会比外面更有趣。”我说,又回到剧场高处坐着眺望远方。一
个钟头过后,马克斯来找我,脸上浮着微笑,他已经解读了一个极为难解的
希腊短语,这对他来说,一天都会因此而变得更有意义。
德尔法真令人难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迷人的景色,我们甚至四处寻
觅,想在那儿找一块地将来有一天造所房子。我记得我俩选定了三处。这是
美好的梦想:不记得我俩当时是不是相信这个计划。前两年,我故地重游,
看到大轿车川流不息,咖啡店,纪念品和旅游者到处可见,我真庆幸没在那
儿造房子,到雅典,蜜月就到日子了,就在还有四五天就要分手的时候,我
们这两个伊甸乐园的幸福居民突然大祸临头.我病倒了,最初以为是患了那
种在中东常见的肚子疼,其中有吉皮肚子疼,巴格达肚子疼,德黑兰肚子疼
等。我把这一次叫做雅典肚子疼,但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
过了几天,我起来了,可驾车游览时,我难受得不得不又把车子开回来。
当时能请到的只有希腊医生。他讲法语,我很快认识到,尽管我的法语足以
应付一般交际,可对医学术语却一无所知。
这位医生把我的病归于吃了红鲱鱼头的缘故。据他说,这种鱼对于不大
会炖鱼的初来乍到的人危险性很大。曾有一位内阁大臣也得了这种病,差一
点送命。我确信自己病得随时都可能死掉。我仍发着高烧,吃不进东西。然
而,这医生到底救了我一命。我告诉马克斯让他放心,第二天他就可以走了。
“岂有此理,我怎么能撇下你呢,亲爱的?”他说。
麻烦在于马克斯受人之托,要按时赶到乌尔,为考察队的住房砌造各种
辅助设施,以便在伍利夫妇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两星期后到达时一切都准备就
绪。他要砌一间新餐厅并为凯瑟琳修一间新浴室。
“我相信他们会谅解我的,”马克斯说。但他语气中流感出迟疑。我知道
他们是不会谅解的。我气愤地告诉他说他们会把他的不负责任归罪于我。这
事关我俩的名誉,马克斯必须按时赶到那里,我让他放心,我会平安无事的。
我将静卧休息一星期,然后坐东方快车径直回家。
可怜的马克斯心都碎了。同时他又被那种该诅咒的英国式的责任感所围
困。这是伦纳德·伍利长期以来对他施加的影响的结果。
最后,我们俩怀着某种生离死别的悲壮心情告别,马克斯终于离我而去
履行他的职责去了。
我像根木头似地躺在由绿色墙纸裱糊的房间里,像只猫那样病恹恹的.腰
疼,胃疼,虚弱得连手都不愿抬一下。我叫人端来淡而无味的煮通心粉,吃
了两口就推开了。看来再吃点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惦念着马克斯。此时他应该到贝鲁特了,明天他将随奈恩车队穿过沙
漠。可怜的马克斯,他该多挂念我呵。
幸运的是,我不必再为自己担心了。我已感到内心翻腾着要干点事或挪
挪地方的决心。我又吃了些无味的煮通心粉,放了点碎乳酪。每天早晨在室
内来回走三趟以便恢复腿劲。医生来看我时说已经好多了。
“不错。嗯,看得出你是在恢复。”
“说真说,我后天就想回家了。”
“噢,别说蠢话。告诉你,那位内阁大臣。。”我按计划离开了那儿。
旅馆的搬运工搀着我蹒跚地登上火车。我躺倒在我的铺位上,没怎么动弹,
偶尔叫人从餐车给我端碗热汤来。汤总是油腻腻的,我毫无胃口。假如是若
干年后,这种不喜油腻倒是对保持体型有好处,可在当时我还很纤瘦。旅程
结束回到家时,我已皮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回到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真是再舒适不过了。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
完全恢复了体力和精力。
马克斯平安抵达乌尔,他为我一直心烦意乱,一路发了数封电报,盼我
的回音,可总是杳无音讯。他用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焦虑,所干的话比伍利夫
妇预料的要多得多。
到了我现在的年纪,我非常清楚如何对付性格爱冲动的人:演员、制片
人、建筑师、音乐家和像凯瑟琳·伍利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母亲而言,马
克斯母亲是那种我所说的极敏感的人,我母亲也属同一类人。
我的几位演员朋友就好发脾气。查尔斯·劳顿在《不在犯罪现场》中扮
演赫尔克里·波洛。一次在排演休息时,他一边吸着冰淇淋水,一边向我说
起他的处世绝招:“装作喜怒无常很有好处。人们会说,当心别惹恼了他,
要知道,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这种做法有时让人心烦,”他补充说,“尤其是你并没有这种欲望的时
候。但是这样毕竟划得来,每次都不会吃亏。”
2
这时期的创作活动在我记忆里似乎难以理解的模糊,这看来不可思议。
其实即便在当时,我也没把自己看做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写作长篇和短篇
小说,并能出版。我开始习惯于把这做为一项固定的收人。可每当我填写表
格中职业一栏时,我除写上当时引以为荣的“已婚妇女”之外不知道还有什
么好写的。我是个已婚妇女,这是我的身份,是我的职业。写书是我的副业。
我从没有把写作冠之“专业”的金字招牌。我觉得那样太荒唐。
我的婆婆对此不理解,“你写得精彩极了,亲爱的阿加莎,你应该写点,
嗯,更严肃的?”指的是“值得写的”东西。我发觉我无法向她解释,也没
想到要解释,我的作品是为消遣而写的。
我想做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我的一些作品使我感
到得意和满足。但是,我从未得意忘形过,因为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最高成就。
故事并不像为第一章拟写线索发展时所构想或镀步时喃喃自语展现在眼前的
那样理想。
可爱的婆婆大概是要我写出某个世界著名人物的传记。我想象不出还有
什么会比这更棘手的了。然而,我总是不加思索十分谦虚地回答说:“您说
的对,不过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罗莎琳德往往会纠正我说:“可你就是
个作家,妈妈。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怜的马克斯由于结婚而被狠狠地治了一下:就我所知,他从不看小说。
凯瑟琳·伍利把《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强塞给他,他却一个字都没看。
有人在他面前谈过故事的结局,他说:“知道了结局,这书还有什么看头?”
而就在这时,他成了我丈夫,于是他毅然地捧起了书。
到这时为止,我已写了近十本书,他慢腾腾地从第一本看起。马克斯关
于轻松读物的概念是那些深奥的考古学著作或古典专题的研究著作。因此,
他看这种轻松小说时愁眉苦脸的样子十分好笑。可我应该骄傲地说,他坚持
下来了,后来,他似乎对这种自讨苦吃也乐在其中了。
可笑的是我对婚后撰写的书竟然印象无几。大概是我过于沉湎在日常生
活的欢乐之中,而写作成为我的时断时续的任务了。我从没有一间固定的专
用写作室。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每逢接待来访
者,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拍摄一张我的工作照。
“带我们看看你的写作室吧。”
“噢,我在哪儿都可以写。”
“可总有个专用房间吧?”
然而我没有。我的全部用品不过是一张结实的桌子和一台打字机。这时
我已开始用打字机直接写作,尽管我仍习惯在开始几章时以及间或着用笔创
作,随后再用打字机打出。卧室里一张放脸盆用的大理石桌面成了写作的好
地方;餐厅里的餐桌也挺合适。
家里人常常注意到我又要开始创作了,“看,米苏斯又在琢磨呢。”卡洛
和玛丽总是叫我米苏斯,她们都看得出我陷入沉思的表情,她们有所期待地
望着我,催我躲进屋子里专心写作。
许多朋友对我说:“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写书,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你写
作的情景,甚至看不到你到什么地方写作。”我的行踪大概和狗叼着骨头走
开的情况差不多:狗偷偷摸摸地走开,半小时内见不到其踪影。随后它会鼻
子上沾满泥土,扭扭捏捏地出现在面前。我大概也是如此,要去写作时,我
总是有些不自然。可每逢我得以抽身,关上房门不让别人打搅,就可以伏案
疾书,完全沉浸在写作之中。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我写的作品相当可观:除了一些完整
的长篇之外,还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
一本以奎因先生为主角的小说集,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写作并不经常,
或许隔三四个月才写一篇,有时间隔还会更长些。期刊似乎喜欢这类作品,
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是我回绝了给期刊写系列小说的要求。我不想写一部
关于奎因先生的系列小说,我只是在有创作冲动时才动笔。
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犯罪团伙》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小说都是模仿当
时某一定型侦探模式写成的。现在有些已记不清了。我记得有索思利·科尔
顿那个瞎子侦探,当然还有奥斯亭弗里曼;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和他
那奇妙的时间表;也有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我挑选了十二位侦探小说作者,
看看他们中哪一个至今仍为读者所熟悉是很有趣的。有些人的名字变得家喻
户晓,有些则默默地消失了。当时在我看来,他们写得都很出色,以不同的
风格给人以享受。《犯罪团伙》其中有描写我的两位年轻侦探汤米和塔彭斯
的故事,这俩人成了我第二本书《暗藏杀机》的主要人物。为了换换样,再
次以他俩为主角创作倒颇有趣。
《寓所迷案》是在一九三零出版的,但是,我对出版时间和地点以及写
作过程、起因,甚至连怎么想起用一个新角色马普尔小姐作为小说中的侦探
都记不清了。当时,我肯定没打算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继续以她为主人公。
我没想到她会成为赫尔克里·波洛的竞争对手。
如今,人们络绎不绝地写信给我,建议马普尔小姐和赫尔克里·波洛应
该邂逅相遇。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我肯定他俩决不会对此感到高兴的。赫尔克里·波
洛清高自负,他不会要一个老处女来教他几手的。他是个职业侦探,有他在,
就不会有马普尔小姐的立足之地。他俩都是红人,都是凭本事吃饭的。我不
会安排他们邂逅相遇的,除非我一时心血来潮,感到有必要这样做。
我想,大概是在《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中刻划谢泼德医生的妹妹
时所产生的乐趣,促使我产生了创造马普尔小姐这个人物的想法。我喜欢书
中她这个角色,尖刻的老处女,好奇心十足,没她不知道、没听过的事:地
地道道的私人侦探。当这本书被改编成剧本时,使我大为不快的是卡罗莱挪
不见了。医生又多了一个妹妹,一个妙龄少女,能唤起波洛春心萌动的娇媚
姑娘。
我不了解这主意刚刚出现时。人们对于戏中的改动是多么难以接受。这
时我已经写了一个自己的侦探故事剧本,记不得这是什么时候了。休斯·梅
西对此颇有异议;他们实际上要我最好不要对这个剧本存在什么期望,因此
我也就没有强求他们。这个剧本名叫《黑咖啡》。这是一部传统风格的惊险
剧,虽然其中不乏老调重弹,但我觉得还不错。
后来,时来运转,我在森尼代尔时的一位朋友伯曼先生与皇家剧院有关
系,他向我提出这剧本或许能上演。
弗朗西斯·沙利文在《黑咖啡》中饰演波洛。他体态臃肿,身高六英尺
二英寸;我对饰波洛的演员总是一个肥胖的家伙感到奇怪。我记得首场演出
是在汉普斯持德的大众剧场,露西娅的角色是由乔伊斯·布兰德扮演的,我
一直认为她是个出色的演员。
《黑咖啡》公演了四五个月后,终于挪到西区上演。二十多年后,这个
剧经过稍许修改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作为保留剧目,人们对它反应很好。
《不在犯罪现撤是由迈克尔·莫顿根据我的一部书《罗杰·艾克罗伊德
谋杀案》改编上演的第一部剧作。他是个剧本改编行家。我对他最初的想法
不以为然,他想让波洛年轻二十岁,改名为博·波洛,身边有许多姑娘献媚。
这时我和波洛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意识到他将永远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极力
反对完全改变他的性格特征。后来,在监制人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支持
下,我们决定去掉医生妹妹卡罗莱娜这个人物,用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来代
替。我前面说过,我很不情愿去掉卡罗菜挪这个人物,我偏爱以乡村为背景
的关于她的那段故事。我喜欢通过医生和他主宰一切的妹妹的生活表现出来
的乡村生活的剧情。
如今重温《寓所迷案》,我并不像当时那样满意。我觉得它的人物过多,
枝节也太多。但主要情节还是经得起推敲的。我看那村子就像确有其事一样,
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些村庄与之相似。孤儿出身的侍女、训练有素且会向上
爬的佣人不见了,但取代他们的日间女佣又与他们何其相似,尽管应该承认
她们不如前辈人那么有心计。
马普尔小姐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我的生活,竞丝毫没引起我的注意。我给
一家期刊写了六篇系列短篇小说,选择了六个人物每星期在一个小村庄聚
会,讲述疑难案例。我从简·马普尔小姐写起,这位老处女很像我姨婆在伊
灵的某些至交。我年轻时去乡村时常遇到这种老妇人。马普尔小姐决不是我
姨婆的再现;她要比我姨婆更大惊小怪、更有老处女的味道。但是俩人确有
相似之处,她们性格爽快。她们总喜欢把人和事往坏里想,而可怕的是事实
证明十有八九她们是对的。
姨婆的预见性相当可怕。我哥哥姐姐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