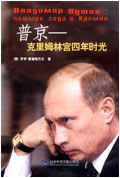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伦敦写了一本叙述我们在叙利亚生活的书,
定名为《在遥远的叙利亚》,后来我每每读起这本书就很兴奋地回忆起在叙
利亚的日子。
一九三零到一九三八年那几年特别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没有来自外界的
阴影威胁。
由于工作压力,特别是工作成功后的负担使得人们往往愈来愈少闲暇;
但是这仍然是无忧无虑的年代,总有好多事要干,虽然并不富于吸引力。我
写作侦探小说,马克斯撰写考古的著作、报告和文章。大家都忙忙碌碌,但
并不很劳累。
我们就这样悠然度日。马克斯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考古工作,我从事写作,
这时写作已成为我的职业了。因此,并没有多少热情可言。
起初,写作是件激动人心的事,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并没有感到自已是个
作家。写的书每每得以出版都使我感到吃惊。而现在,写作成了天经地义的
事了,成了我的专职。
人们不仅要求出版我的书,还催促我继续写下去。可是那种想干点分外
事的无休止的渴望使我坐立不安;而实际上不这样生活也太乏味了。
这时我想做的是要写点侦探小说以外的东西。因此,我怀着志石不安的
心情,沉浸在一本名为纯小说《巨人的面包》的写作之中。这是一本以音乐
为题材的小说。严格说来,它时时暴露出我对这个题材的无知。读者对这本
书的评价尚好,销路也如预期那样不错。我用了玛丽·韦斯特马考特的笔名,
谁也不知道本书的作者是我。这秘密我一直保守了十五年。
一两年后,我又用这个笔名写了另一本书《未完成的肖像》。只有一个
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现在她叫楠·昆。楠的记忆力很强,我描写孩子的
某个短语和在第一本书中的一首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语地说:
“肯定是阿加莎写的。”
一天,她捅了捅我的腰肋,用一种稍不自然的声音说:“前两天,我看
了一本爱不释手的书,让我想想看书名是什么来着?《矮人的血》,对,就
是《矮人的血》。”
然后她又调皮地对我眨了眨眼。我到她家后,说:“那么你猜《巨人的
面包》是谁写的呢?”“当然知道是你啦,我熟悉你的写作风格。”楠说。
我有时还写写诗歌,多半是民谣。但是,我不想凭运气闯一闯一个完全
不同的写作领域,也不想在这个不大容易干点新鲜事、冒险事的年纪去干这
种事。
我想促使我动笔的原因是人们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来把我的小说改编成剧
本,我为此倍感懊恼。虽然我写了《黑咖啡》这个剧本,可从没认真地想去
创作剧本。我对写《埃赫那吞》很得意,但是绝不相信它会上演。我突然想
到,既然我不喜欢别人改编我的作品,那么何不自己尝试——下改编呢。在
我看来,我的作品被改成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摆脱不了原作。侦探小
说决不会像个剧本,因此改编它要比改编一部普通小说困难得多。它的情节
是如此错综复杂,人物繁多,线索干头万绪,扑朔迷离。需要的是删繁就简。
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十个小黑鬼》(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改为《十个
小印第安人》),因为它太难写了,所以就更有吸引力。十个人要合情合理地
在谋杀犯不好马脚的情况下被干掉。我在经过充分构思之后动笔了,写完后
我很满意。
这本书线索既清晰明快又令人迷惑不解,可解释又合情合理;事实上,
为了解释就需要有一个尾声部分。这本书的评论和销路都不错,但是真正为
之满意的还是我本人,因为我比评论家更清楚写这本书是多么不易。
其后,我又进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会更令人激动。
乍一看这似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来讲故事的结局,于是我只好有所改动。
我必须使其中两个人物摆脱干系,从磨难中平安地脱身,在故事结束时再团
聚。这与原来的童谣的内涵并不相悖,因为有一首“十个黑孩子”的歌谣是
这样结尾的:“他成了家,万事大吉。”
我写完了剧本。它并没有得到多少赞许,断语是“无法上演”。查尔斯·科
克伦却对它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为此剧的上演尽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无法
说服他的赞助人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说的都是空泛之辞,什么没法演啊,
观众会笑话啦,情节太紧张啦等等。科克伦坚定地说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可事情明摆着不行。
“希望将来这个剧本的运气会好一点,”他说,“因为我很想使这部剧上
演。”
后来机会来了。对它感兴趣的伯蒂·迈耶,他曾和查尔斯·劳顿一起把
《不在犯罪现场》搬上舞台。艾琳·亨舍尔是该剧的舞台监督,我觉得她工
作兢兢业业。我对她的手法颇感兴趣,因为她的手法与杰拉尔德·杜·莫里
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这个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
极不老练,仿佛心中没底;但是当我看到技巧进一步发挥时,我才认识到这
种手法的魄力。她开始时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观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
观察舞台动作和舞台灯光以及总体效果如何。随后,她几乎事后才想到集中
演员对台词。这种作法卓有成效,给人印象极深。这造成了一种紧张感,舞
台灯光转暗后,在三盏聚光灯柱照射下,演员们都正襟危坐在闪烁的蜡烛旁,
这种灯光效果强极了。
随着演员的杰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绪愈来愈紧张,恐怖和不信任在人
物间蔓延;在我看来,谋杀设计得极为巧妙,丝毫没有什么破绽或者显得过
分哗众取宠。我不是说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认为届上乘,可我确实认
为在某些方面,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写得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是《十个小
黑鬼》使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又踏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后除我
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改编我的作品。我自己决定哪些小说应该改编,并且
仅仅这些小说才可以改编。
我着手改编的第二部作品《空幻之屋》是在几年后的事了。一天,我突
然冒出个想法,《空幻之屋》一定会成为一出好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
莎琳德。在生活中她总是扮演试图劝阻我又屡屡受挫的角色。
“把《空幻之屋》改为一出戏,妈妈?”罗莎琳德面带惧色地问,“这是
部好小说,我也很爱看。可是你无法把它改编成剧本。”
“我行。”我说,为有了对立面而激动不已。
“噢。但愿你别这样。”罗莎琳德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样,我兴致勃勃地记下了《空幻之屋》剧本的构思。这本书在某
些方面当然更像小说而不是个间谍故事。我一直认为《空幻之屋》这部作品
由于增加了波洛这个人物而被我毁了。我已经习惯于作品中出现波洛,因此
他也很自然地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可是他一出现,全都乱套了。他的确大显
身手,可我总想没有他这部作品会更好。于是在设计剧本情节时,我割舍了
波洛这个人物。
《空幻之屋》脱稿了,尽管除罗莎琳德外还有些人持相反意见。彼得·桑
德斯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曾把我的许多剧本搬上舞台,他相信这个剧也会成
功。
《空幻之屋》获得成功后,我开始自讨苦吃了。当然,我知道小说创作
是我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我可以继续这样编织情节,进行创作一直到老。
我对能否再构思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从未产生过绝望情绪。
当然,在一部作品动笔之前,我总得经历极为难熬的三到四个星期的时
间。这种痛苦无法形容。独处一室,咬着铅笔,眼睛盯着打字机;或踱来踱
去,或——屁股坐在沙发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然后走出房间去打扰某个
正忙碌着的人,通常要打扰马克斯,因为他的脾气特别温厚,对他说:“真
糟糕,你看我不晓得如何下笔了,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也写不出书了。”
“哦,怎么会呢?你肯定能行。”马克斯常这样安慰我。他总是带着期望
的语气边安慰我,边将目光转向他的工作。
“可我知道不行了,我想不出什么故事。我脑子里曾有个故事轮廓,可
现在看来毫无可取之处。”
“你只需闯过这个阶段。类似的情况以前曾发生过。你去年就曾这样唠
叨过,前年也一样。”
”这次不同了。”我确信无疑地说。
但是这次当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我这样地凄惨和绝望。然而这种特殊
的阶段需要有所体会。这就像把雪貂放在兔穴里,而自己在洞口守着猎物一
样。在洞穴内一片混战之前,在无聊中度过漫长的时间,精神上得不到平衡。
同样,脑子里对想写的东西一片空白,随手翻开一本书,但不久又会发现根
本没有看进去;试试做字谜游戏,心思又没放在解法上;全部身心都被一种
痴呆的绝望情绪所占据。
之后,由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原因,一种内在的动力使人文思如涌。大脑
开始运转,自知这时迷雾已经散去,灵感已经到来。你会突然绝对有把握地
弄清楚了甲想对乙说些什么。你会跑出房间,沿路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断地
重复着某节对话,譬如莫德和阿尔温的一问一答,他们要去哪,另外一个人
会从树后的什么地方盯着他俩,地上的一只小死野鸭如何勾起了莫德早已忘
却的经历,诸如此类的情节。回到家时满心欢喜,虽然还只字未写,但是终
于可以动笔了。
那时,我像是迷上了剧本创作,而这仅仅因为它不是我的本行。剧本要
比小说容易写,因为可以想象出剧情,而不会因那种苦于小说中的描写而中
断情节的连续性。舞台的时空限制了故事的复杂程度。你不必随女主人公上
楼下楼,或是来往于网球场,对这些情节不必绞尽脑汁进行描写。惟一要写
的是所见所闻和所干的事。观察、倾听和感受,做到这些就足矣。
我应该坚持一年完成一本书,我相信能做到这一点。剧本创作不过是冒
冒风险,什么事都是这样,有成功也有失败。
成功会接踵而来,随后是不明不白的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谁也无法
解释。我发现许多创作家都这样。我曾看过一个相当不错的剧本,但它的演
出却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或是因为它不合时宜,或者因为
演员阵容对其演出有些影响。剧本创作是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每次都是一次
有趣的赌博,我喜欢这种冒险。
写完《空幻之屋》后不久,我明白应该再写一个剧本。我暗想,如果可
能,我要创作一个不是小说改编的剧本,一个纯粹的剧本。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
我们再次陷入了世界大战。这次战争不同于上一次。人们本来以为这次
战争还会像上次一样。因为我想人们料事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了,就好像它是闻所未闻、毫不可能的事。
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没发生过这种事,人们便以为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而这一次大战完全不同。
起初,人们对一切如常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人们以为在第一个夜晚就
会听到轰炸伦敦的轰轰声。然而,伦敦没有遭到轰炸。
马克斯参加了英国国民军,我到托基的医院询问能否同意我到医院药房
工作,这样也可以使我的医药知识有所更新,今后或许有用。由于随时都可
能发生大批伤亡.药房很欢迎我去。罗莎琳德填写了妇女辅助航空队的登记
表.但是她并不热衷于此,只是想作为一个战时女子去试试。
这时。马克斯在我们的朋友斯蒂芬·格兰维尔的帮助下参加了空军感到
很得意。这位朋友是一位埃及学教授,他和马克斯一起在空军部共事,合住
一个房间。两人都是烟鬼,马克斯抽烟斗,没停的时候。空气浑浊不堪,他
们的朋友把他的房间叫“小炭窑”。
妇女辅助航空队和其他一些战时服务单位都没有吸收罗莎琳德,就我所
知,她也没想干点什么事。她又打算进入空军训练学校,于是又填了一大叠
包括日期、地址、姓名和许多官僚们需要了解的鸡毛蒜皮的情况的表格。可
是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今天早晨,我把那些表格都撕了。我不想进空军训
练学校了。”
“是吗,罗莎琳德?”我严肃地说,“你干什么应该拿准主意。我不在乎
你干什么,干你想干的事。但不要总是三心二意的。”
“嗯,我想干点更有意义的事,”罗莎琳德说,随后她像她的同龄人在告
诉长辈什么事时那样扭扭捏捏地补充说,“我打算下星期二和休伯特·普里
查德结婚。”
这并没奇怪的,只是有些突然。
休伯特·普里查德是——名正规军少校,威尔士人;罗莎琳德在我姐姐
家结识了他。
休伯特是我外甥杰克的朋友,常去他家。他也曾来过我家一次,很招人
喜欢,文静,黝黑,养了一大群狗。罗莎琳德和他已经好了一段时间了,但
是我没想到会谈到结婚。
“我想,”罗莎琳德说,“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妈妈?”“当然会参
加。”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又觉得那纯粹是没必要的折腾,我是说,你
不觉得没有婚礼更简单、更省事吗?我们得在登比结婚,因为他无法请假。”
“没关系,”我安慰地说,“我会去登比的。”
2
光阴荏苒。战争仍在继续。
我有许多事要做。每周在医院工作两整天和三个半天,星期六上午隔周
去一次,其余时间在家写作。
我决定两本书同时动笔。因为写作同一题材常使人丧失新鲜感,这对写
作很不利。
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把它放在一—边,干点别的事,可是我没其他事可干。
我不想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相信,如果同时写两本书,不断变换口味,
工作会有新鲜感。这两本书一本叫做《藏书室女尸之谜》,这是我已蕴酿好
长时间的题目;另一本是《桑苏西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