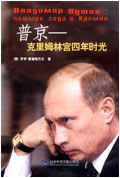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形象仍存留在我的脑海中,后来渐渐地淡漠了。爱情就这样悄然逝去了。三
年之后,我又无望地爱上了一位年轻的陆军上尉。他高高的个子,深色的皮
肤,当时正在向姐姐求爱。
如果说阿什菲尔德是我的故乡的话,那么伊林算得上是个激动人心的地
方,充满异域的情趣。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之一就是房子里的卫生间,里
面有一张富丽堂皇的红松木坐椅。坐在上面就如同女皇端坐在宝座上一般。
迪基女士摇身变成了玛格丽特女皇,迪基成了女皇的儿子——戈尔迪王子,
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他就坐在女皇左面那个精致的彩陶扶手上。我每天一大
早就躲在这里,坐在“御椅”上向朝拜者频频点头,听他们念奏折,伸出手
来让他们吻,就这样一直坐到来解手的人在门外等得不耐烦了,气愤地把我
从便池上拽下来!
由于父亲娶的是继母的侄女,又因为他称继母为母亲而妻子却称她为姨
母,所以我们都叫她姨婆。我的祖父(我父亲的爸爸,母亲的姨夫)晚年来
往于纽约与曼彻斯特之间,曼彻斯特有他的分公司。他曾是美国的一位“传
奇式人物”。他原来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孩子,背井离乡,由曼彻斯特来到
纽约,当上了某办公室的勤杂员,后来发迹成了公司的股东之一。“三代的
时间里,从穿小汗衫到坐旋转椅”正是我们家族的真实写照。祖父挣得了巨
额财富,父亲把它交给同事代理,财富在一点一点地消耗,等到哥哥手中的
时候,就被闪电般地挥霍殆荆祖父去世前不久,在柴郡买下一幢房产。当时
他已病人膏肓。不久,姨婆就守寡了。她那时还算年轻,在柴郡住了一段时
间,受了一两次盗贼的侵扰后,就在伊林买下一幢房子住了下来。当时那儿
还算是乡下,正像她说的那样,房子四周都是农田。可是等到我去看她的时
候,一切都变了,到处都是一排排新建的房子。
姨婆住的房子和庭院有无尽的魅力。我把幼儿室分割为几片“领地”,
靠前的部分是一个向外凸出的窗户,下面铺着一条漂亮的条格台毯;靠后的
部分是餐室,地上铺着布鲁塞尔地毯。我把各式各样的蒲席和一块块亚麻地
毯配备给各个“领地”,神情庄重地在各“领地”巡视,口中念念有词地嘟
囔着。姆妈安详地坐在一旁织毛线。
姨婆的大床是令人迷恋的地方。床的四角镶嵌着四根粗大的红木床腿,
四周是大红的锦缎床围,上面铺着羽绒被褥,每天清早,我还没穿上衣服就
跑过来,爬上姨婆的床。
姨婆早晨六点钟就醒了,总是高兴地把我拥进她的被窝。客厅在楼下,
摆满了镶嵌着五光十色装饰品的家具和德累斯顿出产的瓷器。由于窗外就是
花房,屋子里总是光线阴暗。
客厅仅用于聚会。隔壁是起居室,里面总有一位女裁缝坐在那儿。姨婆
在餐室里心满意足地过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全套家具都是笨重的红松木
的。屋子正中是一张餐桌,四周摆着靠背椅。窗上挂着精细的钩织窗帘。姨
婆有时坐在桌前那把皮背雕木大师椅上写信;有时坐在壁炉旁的一张天鹅绒
软椅上烤火。桌子、沙发以及几把椅子上都堆满了书籍。
姨婆从未间断过买书,有的是留着自己读,有的是赠送他人。后来书籍
越来越多,以至于连她也搞不清哪些书是准备送给哪些人的。有时甚至发现
某某人的那个逗人喜爱的小男孩已转眼十八岁了,而她从前为他买的《圣人
古尔德雷德的孩子们》和《蒂莫西老虎历险记》两本小人书一直还没有送给
他。
姨婆很喜爱孩子,常常搁下手头还未写完的字迹潦乱的长信,兴致勃勃
地跟我一起玩“维特利先生和小鸡”的游戏。不用说每次都由我充当小鸡。
姨婆到商店里买小鸡,挑中了我,询问售货员这只小鸡的肉是否细嫩,然后
回家把小鸡捆绑好,串起来(这时我总是忍不住大笑起来),放到炉灶上烧
烤,翻个个儿再烤另一面,然后端上餐桌。就在餐刀闪闪的霎那,小鸡突然
复活了,欢蹦乱跳,“这是我!”——游戏至此进入了高潮。我和姨婆不厌其
烦地重复这个游戏。
每逢星期天,外祖母就到伊林来吃午饭,常常是带着两位舅舅一块来。
这是最快乐的一天。鲍爱莫外祖母是我母亲的生身之母,她通常在十一点钟
到达。她比姨婆还要矮一些,由于身材矮小,一路走来难免有点气喘吁吁。
从伦敦到这里,一路上要倒几次火车和汽车。她到达后的一件事就是脱掉脚
上那双长筒靴子。她的女佣海丽特通常跟着她一块来,跪在她面前帮她把靴
子脱掉,换上一双松软的羊绒拖鞋。外祖母深深地叹一口气,坐到餐桌旁的
靠背椅上。于是,姐妹俩就开始了周日上午的例行“公事”,谈起一长串纷
乱复杂的账目。外祖母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军人商场为姨婆置买了大量的生
活用品。对这姐妹俩来说,军人商场就是她们心目中的宇宙中心。俩人饶有
兴致地研究着一串串数字,一条条账目,一张张表格,讨论着所购买的物品
的质量。军人商场实行定期付款制,零碎的小账和维修费用都当面了结。姨
婆每次多付给外婆一些钱,作为辛苦的酬谢,姐妹俩关系很亲热,但相互间
也小有妒忌。时而拌嘴,一有机会就互相抬杠、逗趣。外祖母自认为曾是她
们家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姨婆总是不服气。
波丽虽然身材矮小,但年仅十六岁时就被布莱克警卫团的一位上尉爱上
了。家里认为她还很年轻,不到结婚的年龄,可上尉却说他所在的团就要移
防国外,要在那儿驻扎很长一段时间,希望俩人能马上完婚。这样,波丽十
六岁就结婚了。小两口是完美的一对。波丽年轻妩媚,丈夫是团队里公认的
美男子。
波丽很快有了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夭折了。她二十六岁开始守寡。姨
婆结婚很晚,曾与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发生过恋情,可惜两人都很穷,无法
完婚。后来,他找了一个有钱的遗孀,她也嫁给了已有一个孩子的美国富翁。
波丽丈夫生前团队里的几位军官曾向她求爱,想要以她为妻,都被她婉言拒
绝了。她不愿让别的男人来代替丈夫的位置,申言死后要葬在他的墓旁。
姐妹俩了结了上周的账目,明确了下一周的采购任务后,舅舅们就该到
了。欧内斯特舅舅在英国国民军中任职,哈里舅舅是军人商场的管事。大舅
弗雷德在驻防印度的一个团里服役。桌子摆好后,大家就开始用午餐。
丰盛的午餐后,全家人除我之外,都要去小睡片刻。我躺在扶手摇椅里
悠闲自得地摇晃着。午睡醒来,大家开始玩“考校长”的游戏。哈里舅舅和
欧内斯特舅舅都是能说会道的“校长”。大家坐成一排,荣任“校长”的人
手里拿一卷报纸在前面来回踏步,装腔作势地大声提问:“针是什么时候发
明的?”“亨利八世的第三个夫人是谁?”“威廉·鲁弗斯是怎么死的?”“麦
黑病是怎么回事?”谁要能回答上来,就可以升为“校长”,原来的校长自
动让贤。如今人们都喜欢的广播电台组织的知识测验节目大概就是由这种游
戏演变而来的。
游戏结束后,两位舅舅先走一步。外祖母留下来喝过下午茶才离去。
姨婆善于交际,社交活动颇为频繁,家里常常挤满了退役的海陆军将军
和校官,他们到伊林来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再说这地方离伦敦也近,
挺方便。
在训导社交知识方面,姆妈也算是内行。
“吃晚饭的速度要再快一些。假如你长大了。去公爵家赴宴,席前会站
着一位精干的管家和几个仆人。只要时间一到,不管你吃完没有,他都会把
你的盘子撤走。”姆妈常把贵族们的铁事挂在嘴边,这方面的教诲引起了我
的奢望,幻想将来有一天会成为阿加莎公爵夫人。这成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愿
望。
可是姆妈的社会知识无情地告诉我:
“你永远也当不上公爵夫人。”她说。
“是真的吗?”我感到诧异。
“是真的。”姆妈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要想当公爵夫人,必须生
来就是公爵、伯爵的女儿。只有嫁给了公爵,才算得上公爵夫人,而那又不
过是借了丈夫头衔的光,不是你想当就当得上的。”
这即是我与命运的第一次遭际。世间许多事情是不可得的。在童年时代
就意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对自己有益无害。许多事情可望不可及——自然
卷曲的秀发,乌黑的双眸,甚至于公爵夫人的尊称,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存
在的。
我在身世方面的势利之心,总的来说要大于其他方面。
我把身世看得重于财富和才智。
小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卑感,甘于自己的现状,意识到家底不很殷实等
不利条件。
这就像是分到手的一手牌,无法挑剔,只能筹划好,尽最大的努力一张
张打出去。我敢肯定,我并不怎么嫉妒和痛恨那些比我更富有、更聪颖的孩
子。看到某个小朋友手里拿着昂贵有趣的玩具,我不企望,也不闹着要买。
与大多数朋友相比,我们算不上富户。父亲是美国人,别人都以为他很
有钱,似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是富翁。他只能凑合着撑起家里的门面。我
们既没有雇管家,也没有雇男仆;既没有马车,也没有车夫。家里只有三个
女佣人,在当时算是最少的了。要是时逢雨天去朋友家喝茶,就不得不披上
雨衣,穿着套鞋在雨中步行一英里半。除了穿上好一点的衣服参加重要的聚
会外,父母是不会专为孩子叫马车的。
另一方面,家中款待宾客的菜看却又异常的奢侈——与现代的标准相
比,该是邀请一位大厨师和几位助手来制做了。
姐姐很早就被认为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布赖顿的女校长劝她进格
尔顿深造,父亲却不高兴地说:“不能叫麦琪去当女学者,还是送她去巴黎
修完剩下的学业。”姐姐欣然去了巴黎,因为她自己从未打算到格尔顿深造,
她有才智,谈谐,机敏善辩,干什么事都成功。哥哥比姐姐小一岁,长得颇
具男性的魅力,喜欢文学,但在其他方面缺乏才气。
父亲和母亲大概已经意识到他将来是个“难办”的孩子。他酷爱工程学。
父亲原希望他将来进入金融界,却发现他缺乏这方面的才干。为此,同意他
选学工程学,可他在这方面也出息不大,他的数学太差。
尽管家里人对我都很好,但却认为我“反应迟钝”。母亲和姐姐反应快
得惊人,我总是跟不上她们。我口齿也很笨拙,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总是力
不从心。“阿加莎的反应太慢了。”家里人常这么说。这是事实,我了解这点,
也从未否认。这并没有使我感到忧虑和苦恼,我已经甘拜下风了。直到十二
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反应能力相当于,甚至高于一般人的水平。并非
我反应迟钝,而是家里人的标准太高了。我的口头表达能力一直很差,这也
许是促使我从事写作的原因之一。
一生中第一次使我真正伤心的是与姆妈的分手、谁也不晓得她当时有多
大年纪,也许已经八十岁高龄了吧。一位她从前照看过的人在萨默塞特有一
处财产,一直劝她退休。
他在那儿为她准备了一幢舒适的小别墅,供她和她的妹妹共度晚年之
用。最后她终于作出了决定,辞掉了这儿的工作。
我日夜思念着她,每天都给她写一封信,通篇尽是拼写错误——写作和
拼写一直是最伤脑筋的事。信中没有一点新意,翻来复去总是那几句话:
亲爱的姆妈:
我非常非常地想念您,但愿您一切都好。托尼身上长了一只跳蚤。我非
常非常地爱您。吻您,吻您,吻您。
您的
阿加莎
母亲为这些信件提供邮票。不久,她有些不耐烦了:“我想你没有必要
每天都给她写信,一周写两次总够了吧?”我感到愕然。“可是我每天都在
想念她呀。我不能不写。”
母亲叹了口气,不再反对了。但她却常常向我提出一些温和的建议。我
每日一封,一直坚持了几个月,后来才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减至每周两封。
姆妈写东西也很吃力,每个月给我写两封信,信的形式不伦不类,但字里行
间却充溢着慈爱。母亲对我如此情意缠绵地依恋姆妈感到不安。
早年天折和病残是传统小说的主要题材。如今暴力情节更合乎大众的口
味。那时候,年轻的女子都希望让人觉得自己脆弱。姨婆总是自鸣得意地告
诉我,她小的时候弱不经风,而外祖母却说:“玛格丽特一直很健壮,我倒
是家里极弱的一个。”
姨婆活到九十二岁,外祖母活了八十六年,我怀疑她们是否真那么赢弱。
不过,多情善感,不时地晕跃和早期肺病都曾是时髦的做作。姨婆深受其感
染。我长大后,她又煞有介事地悄悄告诉与我接触的青年男子,说我多么多
么地脆弱,一定不会长寿。我十八岁的时候,情郎们就常会忧心忡忡地问我:
“你不会着凉吧?你的姨婆告诉我说你弱不经风!”我总是忿忿地回答说,
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他脸上的忧虑顿然消失。“那你姨婆为什么说你的体
质很差呢?”我不得不解释说,她是想让我对别人更具有吸引力。
在她那个时代,青年女子在有男人出席的晚宴上只能吃上一点点,多一
口也不吃。到了夜里,由佣人再备置一点吃的送到她的卧室里。
就连当时的儿童小说也充斥着病残和早亡的故事情节。我最喜爱读一本
名叫《纯洁的紫罗兰》的小书。从第一页开始,那位叫紫罗兰的小姑娘就忍
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最后一页地那富有寓意的早逝。全家人围着她痛哭流
涕。
《小姑娘们》是一本带有喜剧色彩的小书,但作者还是让脸颊红润的小
贝思离开人世。《老古玩店》中小内尔的死令人毛骨悚然,不过狄更斯那个
时代的人自然要对如此哀惋的结局悲痛不已。
另一本我爱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