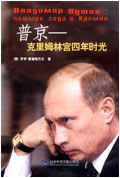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玛丽也跟母亲一样偶尔给我读读法语书。有一天,我拿起一本叫《一个
蠢驴的回忆录》的书一页页地翻看,我忽然欣喜地发现我已经能顺利地读下
来了。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母亲却一句褒奖的话也没有说。经过艰苦的磨
难,我终于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书籍了,尽管遇到较难的段落还需要有人
给我讲解,但我毕竟自己能读了呀。
八月底,我们离开高特里茨去巴黎。高特里茨今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
度过一生中几个最愉快的夏天中的一个。
3
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迪纳尔。令人气恼的是在巴
黎给人留下深刻印记的,只是我们下榻的旅店的卧室。卧室的墙壁漆成了深
褐色,使人很难看见室内的蚊子。
旅店里蚊子成群,夜里嗡嗡叫个不停,叮咬着我们的脸和手臂。我们在
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对付蚊子上了。
我想家里人也一定带着我去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可惜它们在我的记忆中
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家里人特意带我参观了埃菲尔铁塔,就像我第一次
看见大山那样,它也曾让我大失所望。这次巴黎之行给我留下的惟一纪念就
是大概在那时,我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蚊子”。无疑我很讨人嫌。
不过,我并非一点收获也没有,就在抵达巴黎的第一天,我看见了工业
革命的先驱者们。巴黎的街头到处都是被称作“汽车”的新式交通工具。它
们在街上穿梭往来,喧嚣地飞驰而过。(按现代标准,这些汽车的速度自然
很慢,但在当时来看,它们要比马车快多了。)驾车的人都戴着帽子和眼镜,
以及其它一些东西,让人看上去眼花缭乱。
父亲说这种玩艺不久就会遍及各地。我们都不相信。我漠然地望着眼前
的一切,兴趣仍然停留在各式各样的火车上。
母亲慨叹道:”可惜蒙蒂不在这儿,他肯定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回想起这一段生活,我感到有些蹊跷,哥哥的形影仿佛消失了。虽然他
在哈罗公学放假的时候也回到家里来,但却似乎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重要人物
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时期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此
时很为他担忧。他因为考试没有及格而退学。他大概先去了达特的造船厂,
后来又北上到了林肯郡。他学业上的进展总使人失望。在每个家庭中,往往
都要有一个使父母操心和担忧的孩子。在我们家中,哥哥蒙蒂就是这样的人。
他这一辈子都让人感到头痛。
我们由巴黎到了布列塔尼的迪纳尔。
在我的记忆中,迪纳尔是我初学游泳的地方。当我发觉自己僻僻啪啪地
向前划了几下水,居然没有下沉的时候,我得意极了,高兴得不敢相信没有
别人托着我也能游了。
就在迪纳尔,我开始了戏剧实践。当时父母住着两人一间的大卧室,房
间里有一个很大的向外凸出的窗户。实际上是个凹室,前面拉着闭合式窗帘,
酷似一个戏台。我从前一年圣诞节上演的一幕童话剧得到启迪,硬拉着玛丽
每天晚上配合我为家人演出各种神话故事。我选扮自己中意的角色,玛丽一
人兼演故事中其余的几个角色。
回想起父母亲为我们热心捧场,我至今感铭斯切。不难想象,每天晚餐
过后来到卧室坐上半个时辰,观看我和玛丽身穿自己凑合起来的戏装在那里
手舞足蹈,是多么让人兴味索然。我们演出了《睡美人》、《水晶鞋与玫瑰花》、
《美人与野兽》等剧目。我持别喜欢扮演剧中的男主角。我借来姐姐的长筒
抹,当作紧身裤套在腿上,在“戏台”上振振有词地踱步。
起初,我们的戏剧表演也许极为滑稽有趣,至少是博得了父亲的欢心。
但后来却越来越让人腻烦。双亲对我太仁慈了,不忍心坦率地告诉我每天晚
上都来观看我们拙劣的表演实在是活受罪。他们偶尔也会以朋友正在用餐为
借口留在楼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很豁达。
九月,在迪纳尔逗留期间,父亲欣喜地与老朋友皮里夫妇邂逅。他们的
两个儿子当时也在那里度假。马丁皮里跟我父亲在韦维念书时是同窗,两人
一直交往甚密。
父亲与老朋友相会万分高兴。母亲和皮里太太也有共同语言,两人很快
就热烈地讨论起日本艺术。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哈罗德在伊顿读书,
威弗莱德大概是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学习,即将参加海军。威弗莱德后
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中的一个。
我记得当时大家说他小的时候一看见香蕉就咯咯地笑个不停。我为此还
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那时候,这两位小伙子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一个
是伊顿的学生,一个是海军学员,怎么会屈尊来注意一个七岁的毛丫头呢?
我们一家从迪纳尔来到根西,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度过的。我生日那
天,惊喜地收到一份礼物——三只小鸟。它们的羽毛和颜色都带着异域的风
格,它们的名字叫凯凯、都都和贝贝。凯凯是只娇嫩的小鸟,不久就死了。
我喂养它的时间很短,所以它的死并没引起我太大的悲恸。贝贝这只迷人的
小鸟才是我最心爱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兴致勃勃地为凯凯举行了过分铺张
的葬礼。
它的遗体被精心放在用母亲提供的缎料花边做衬里的纸盒中。经过长途
跋涉,我们来到圣彼得港外的高地上,选奸一块墓地,举行了葬礼,小盒被
掩埋了,上面还覆盖着一大束鲜花。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贴。但事情并未到此了结,前往祭扫凯凯的墓平添
了我散步的兴致。
在圣彼得港最惹人注目的是花市。那里有各色各样的花,非常便宜。据
玛丽说,当时的天气一直非常寒冷,刮着大风。每当她问“今天去哪儿散步,
小姐?”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回答:“我们去祭扫凯凯的墓。”玛丽唉声叹气,
我们得顶着凛别的寒风徒步两英里。尽管这样,我还是执拗地拽着她先到花
市,买些山茶花或者其他的花,然后在刺骨的冷风中走上两英里,天还经常
下起雨来。我们在凯凯的墓前举行例行的仪式。将鲜花摆在那里。也许有些
人生来就喜欢丧葬或观看葬礼。人类中若是没有这一生性。那么考古学家也
许就不存在了。
4
有时我想,假如轮回理论成立的话,那我的前世化身一定是条狗。我染
有许多狗的习性。无论谁干什么事,到哪儿去,我都要尾随其后。跟着去做。
同样,当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结束后回到家里时。我的所做所为也全然像条
狗。狗总爱在房子里溜溜达达,四处察看,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用鼻子去
发现有什么异样,哪里好就往哪里蹭。我正是这样。看遍了整个房子,又看
庭院,来到自己的顿地,察看我的铁路线,那棵可以用做跷跷板的树和秘密
了望点,它设在院墙旁一块隐蔽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监视墙外的公路。我
找见了那只铁圈,试了试它是否好。然后。过了一次瘾,用了大约一个小时
的时间,把从前玩过的游戏一个不漏地重玩一遍。
我想,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
“难道你还没有上学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我这时大概已经九岁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大多已经有了家庭教师。不
过当时雇家庭教师主要还是为了让她们照看孩子,训练和监护他们。她们开
设的所谓“课程”完全取决于她们个人的兴趣爱好。
母亲幼年曾在柴郡读过书,后来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抚育女
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她们尽可能四处跑跑,多呼吸新鲜空气,吃得好,不
要强迫她们做任何事情。
(对男孩子自然就不同了。男孩子必须接受严格的正统的教育。)我在
前面曾提到过,她的理论是小孩子不到八岁不能读书。由于这种管束对我没
能奏效,她索性听其自然。我抓住一切时机读我喜欢读的书籍。被称做学习
室的那个大房间设在楼上,里面摆满了各类书籍,其中还专门设有儿童读物
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照镜子》,以及我前面提到的
充满着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情趣的故事集,比如:《我们的紫罗兰》、《萨洛阳
作品集》、大概还有全套的《汉蒂作品集》,除此以外还有各种课本和小说。
我随意选取我感兴趣的东西读。读了大量的书籍。但真正读懂的都不多,它
们不过引起了我读书的兴趣。
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法国剧本。父亲发现我在读这个剧本,
一把夺了过去,神色奇异地问我“你怎么弄到这本书的?”这是法国小说戏
剧集中的一部,被锁在吸烟室,供大人们悉心研读的。
“它就放在学习室里面。”我答道。
“不应该放在这儿,”父亲自语道,“应该锁在我的书柜里。”
我爽快地放弃了这本书,说实在的,我发现它很难懂。
我又兴致勃勃地埋头于《一位艺术家的回忆》、《无家可归》等那些不会
惹事生非的法国儿童读物。
当时我大概也上某些课,但却没有请家庭教师,我继续跟着父亲学习算
术,洋洋自得地由分数过渡到小数,后来终于升入更高水平,学习起“多少
多少只奶牛吃掉了多少青草,几个水箱用了多少小时灌满了水”。我对这门
课简直入了迷。
这时候姐姐开始正式进入社交界,接踵而至的是参加各种聚会,添置衣
物,去伦敦游玩等等。母亲跟着她忙碌起来,无暇顾及我了。有时我变得有
些嫉妒,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在我周围的街坊邻里,碰巧没有一家有与我同龄的孩子。所以在我幼年
时代,只好臆造一系列的亲朋好友。先是小狮狗、小松鼠和小树,后来是有
名的基顿一家。此时,我又在想象中创办了一所小学校。这并不能表明我渴
望进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仅供七位年龄不同,相貌各异的儿童学习之用。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学校没有校名,就叫学校。
首先人学的是埃塞尔·史密斯和安妮·格雷两位小姑橙。埃塞尔十一岁,
安妮九岁。
埃塞尔深色的皮肤,浓密的头发,聪颖、擅长做游戏,嗓音低,看上去
有些男孩子的气质。她的密友安妮恰好与她相反。安妮浅黄色的头发,蓝蓝
的眼睛,羞涩且多情善感,动不动就哭鼻子。她依附于埃塞尔,每次都是埃
塞尔出面保护她。
继埃塞尔和安妮之后,我又收了两位学生。一位叫伊莎贝拉·莎利文。
十一岁,金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是一位漂亮的官家干金。我不喜欢伊
莎贝拉,可以说十分讨厌她。
她俗气,简直庸俗到了极点。她趾高气扬地焙耀自己的富贵,穿着打扮
相当入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另一位叫埃尔西·格林,是伊莎贝拉的表
妹。她有点像爱尔兰人,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性情活泼,总是咯咯笑
个不停。她与伊莎贝拉相处得很好,但时而也被她激怒。格林家境贫寒,穿
着伊莎贝拉穿过的衣服。她有时也对此表示怨恨,但毕竟不大在乎这些,所
以这种时候不多。
我跟这四位姑娘玩得很投机。那段时间里,她们乘“火车”沿“固布勒”
铁路线旅行,骑马、修整庭院、打板球。我还举办了几次锦标赛和邀请赛。
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伊莎贝拉能败下阵来。除了作弊,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
不让她赢——我漫不经心地为她拿着球棍,不加瞄准地胡乱打。可是我越是
对她漫不经心,她似乎就越幸运。她竞穿过了本来是不可能过去的铁圈。把
球正好打过草坪,最后总是获胜夺奎。我恼火极了。
后来,我觉得再有两位年龄小的学生会更好些。这样,学校就又添了两
个六岁的儿童,埃拉·怀特和苏·德·弗特。埃拉学习勤奋,一丝不苟,成
绩优秀,板球打得也很不错,只是人很刻板.头发像毛刷似的。苏·德·弗
特却平庸得出奇。不仅相貌平平——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而且缺乏
个性。可我还是能够看见和感觉到苏的存在。
她与埃拉是亲密的一对。我对埃拉像对自己的手掌那样熟悉,而对苏却
把握不住。也许是因为苏就是我的化身,当我跟其他同学说话时,总是苏在
代言,而不是阿加莎。苏和阿加莎融合一体构成了一个双重人物。苏往往是
一位旁观者,很少是剧情中的人物。最后一位加入这个集体的是苏的同父异
母姐姐弗拉·德·弗特。弗拉年龄最大,十三岁,当时长得不很漂亮,但不
久就将出落成一位抚媚动人的大姑娘。她的出身也很神秘。我初步为她设想
了各种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的未来。她长着淡黄色的长发、一双脉脉含情的
蓝眼睛。
这些“女孩子”陪伴我许多年。随着我的日趋成熟,她们的性格也自然
而然地发生着变化。她们参加音乐会、表演歌剧、在话剧中扮演角色。即使
在我成年之后,我还不时地与她们分享着我的思想,给她们分发我衣柜里的
各种衣服。我在脑子里为她们设计了睡衣的款式。我至今记得埃塞尔穿上一
侧肩上带有洁白百合花的深蓝色薄纱礼服显得更秀美一些。可怜的安妮却很
少能有奸衣服穿。我对伊莎贝拉是公正的,尽管对她抱有成见,仍然让她穿
最漂亮的礼服——往往是有刺绣的绫罗绸缎。即使在今天,当我把一件衣服
放进衣柜时,有时也会喃喃自语:“这件埃尔西穿准好看,她穿绿色的最合
适。
埃拉要是穿上那件三色拼起的针织紧身运动衫一定很洒脱。”此时我自
己也会觉得好笑,可是这些“姑娘”的的确确活在我的心里,只是不像我,
她们没有变老。在我的想象中,她们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三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添加了四个人物:安德莱德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身材颀长修美,有些清高;比阿特丽斯年龄最小,喜欢跳舞,是位
快乐的小仙女;还有罗斯和艾里斯·里德两姐妹,我开始为她们虚构了许多
浪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