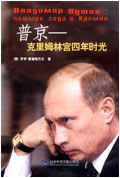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一位,身材颀长修美,有些清高;比阿特丽斯年龄最小,喜欢跳舞,是位
快乐的小仙女;还有罗斯和艾里斯·里德两姐妹,我开始为她们虚构了许多
浪漫故事。
艾里斯有位男朋友,常给她写诗。罗斯很调皮,对谁都敢戏弄,跟所有
的小伙子都调情卖俏。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们都陆续出嫁了,也有的
还未结婚。埃塞尔一辈子独身,跟温柔娴静的安妮一起住在一幢小别墅里,
她们是天生的一对,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两人相依为命也不会是不可能
的。
我们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弗罗茵·尤德就把我领人了美妙的音乐王国。
弗罗茵·尤德是一位瘦小干瘪、神情可畏的德国女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
到托基来教音乐,也从未听说过有关她个人的隐私。有一天,母亲来到学习
室,身旁站着弗莱德·尤德,母亲说她打算让我开始学钢琴。
“是的!”弗罗茵·尤德尽管英语说得流利。却夹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
“咱们现在就到钢琴那儿去。”我们来到钢琴跟前,学习室里摆着的是一架
小钢琴,那架大的摆在客厅里。
“站在这儿,”她命令道.我立在钢琴的后侧,“这个,”说着她重重地在
琴键上敲了一下,我担心钢琴是否承受得住,“是C 大调,明白吗?这是C
调,这是C 大调音阶。”她弹了几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弹C 调的和音。
这样。。再来一遗——音阶。音阶C、D、E、F、G、A、B、C,你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其实她刚才说的我都已经会了。
不久,整个房子里就回荡着音阶和琶音的练习,后来是曲子《快乐的农
夫》。我对音乐课非常痴迷,父母亲都会弹钢琴。母亲弹奏门德尔松作的曲
子以及其他一些她年轻时学过的作品。她技巧娴熟,但对音乐并无强烈的爱
好。父亲却颇有音乐天资,无论弹奏什么曲子都可以不看乐谱。他常弹奏欢
快的美国歌曲和黑人圣歌,还有其他一些作品。
除了《快乐的农夫》,弗罗茵·尤德又给我加了舒曼的一些优雅的小夜
曲。我每日满腔激情地练上一两个小时,从舒曼进到我最崇尚的作曲家格里
格的作品。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弗罗茵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我并不总是弹奏欢快的曲子,还得弹奏大量的我并不怎么热衷的格里格
的练习曲。
弗罗茵·尤德不是那种喜欢干劳而无功之事的人,她对我说:“你必须
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练习很实用,很有必要。曲子是一朵朵瑰丽的小花,
它们开放了,又凋谢了,你必须要有根基,坚实的根基还要有绿叶。”就这
样,我在根基和绿叶上下了大量的功夫,偶尔也插进一两朵小花。我的成就
大概比家里其他人都令人满意。
他们都有些腻烦弹奏这么多练习曲。
当时也开办舞蹈学习班,每周上一次课。教室设在一家甜食店楼上被尊
称为“雅典娜神庙”的房间里。我大概在很早就开始进舞蹈学习班了,一定
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姆妈还在我们家,每周由她送我去学习。年
龄小的学员先从波尔卡舞学起,方法是重走三步:右,左,右——左,右,
左。听到这样的跺脚声。在楼下甜食店喝茶的人一定会感到心烦意乱。回到
家里,麦琪的讥讽多少让我有些不快。她说波尔卡根本不是那样跳,“应该
先向前滑一步,另一步跟上,然后再起第一步,就像这样。。”我感到困惑。
原来这是那位教跳舞的老师希基小姐发明的教学方法,学舞步之前要先以此
来熟悉波尔卡的节奏。
在托基,舞蹈班里几乎全是女孩子。后来我在伊林进舞蹈班学习时,班
里有许多男生。那时我九岁左右,非常腼腆,舞步也不很熟练。一位比我大
两岁,长相标致的少年走到我面前,邀请我跟他跳朗色舞。我窘迫地垂下了
头,告诉他我不会跳朗色舞。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还从未见过这样迷人
的少年。他乌黑的头发,一双大眼炯炯有神。
我即刻感到我们将会成为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朗色舞开始了,我黯然
神伤地坐在一旁。
这时舞蹈班的老师走上前来:“阿加莎,谁都不许光坐着不跳。”
“我不会跳朗色舞,沃兹沃思太太。”
“不,亲爱的,你很快就能学会的,我给你找一个舞伴。”
她将一位塌鼻子,沙土色头发,脸上长着雀斑的少年拽到我面前。“这
儿有一位,他叫威廉。”就在朗色舞相互交位时,我与那位使人眷恋的少年
相遇。他忿忿地对我低语道:“你拒绝了跟我跳舞,却又跟别人跳了,太不
友好了吧。”我试图向他作些解释,说我以为自己不会跳朗色舞,是迫不得
已才跳的,可惜在交位的瞬间是来不及作任何解释的。他依然责怪地注视着
我,直到下课。我真希望下周上课时能遇上他,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再也没
有见过他——人生的又一爱情悲剧。
我所学的舞步中,唯有华尔兹是我一生中都用得上的,可我却始终不太
爱跳这种舞。
我不喜欢它的节奏,常常旋得我头晕眼花,尤其是在跟希基小姐跳的时
候。她的旋转动作轻盈优美,我被她带得双脚几乎离了地,一个曲子下来就
感到天旋地转,几乎站不稳了。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舞姿能给人以美的
享受。
弗罗茵·尤德从我的生活中悄然逝去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是回德国了。
不久,一位叫特罗特的青年人替代了她。他是某教堂的风琴手,他的教
学方法有些让人沮丧。我必须适应另一种演奏风格——几乎是坐在地板上,
高举起双手,完全依靠腕力在琴键上弹奏。而原来弗罗茵·尤德的训练方法
是让我坐得高一些,用小臂的力量弹奏。只有双臂高悬于琴上方,才能给琴
键有力的敲击,那样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5
我们从海峡群岛回来后不久,父亲病重的阴云开始向全家人的心头袭
来。旅居国外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佳,曾两次就医。第二次就诊时,
医生作出了危言耸听的诊断.他认为父亲得的是肾玻回到英国后,我们自己
的医生又给父亲检查了一次,他不同意前一位医生的诊断,领着父亲去见一
位专家。从此,这片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全家人的心头。儿时的我只能膜肪地
觉察出这种心理上的抑郁气氛。就如同狂风暴雨来临前人们隐约能感受到大
自然的沉闷一样。
医疗手段也无能为力。父亲去过两三位医学专家处就诊。第一位认为父
亲心脏状况不好,具体情况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听到母亲跟姐姐说话时说
是“心肌炎”,我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完全是胃的毛病。
父亲夜里常常感到阵痛和气闷,发病的周期越来越短。
母亲起来陪伴他,为他调换姿势,服侍他吃下医生开的药。
平日里,父亲还像以往那样情绪乐观,可是家庭气氛已不那么轻松了。
父亲照常去俱乐部,夏日里把时间消磨在板球场上。回来后讲一些有趣的见
闻。总之,他还是那么慈祥,从不怄气、发怒。可是忧郁的影子迟迟不肯离
去,它笼罩在母亲心头。母亲强打精神宽慰父亲,说他“看上去好多了,感
觉也不同,真是好多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着经济拮据的窘境。祖父留下的遗产都用在了纽
约的房产投资上。但这些房产都是租下来的,并没有水久地买下。它们占据
了市区的一部分,当时那块地产价值连城,房产却值不了多少钱。地产主是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妪。她似乎并不愿意积极合作,处处设置障碍,反对任何
开发和改善工作。定期的房产收入也总是姗姗来迟,而且常常被房屋维修费
用和税款吞噬得所剩无几。
玛丽大概在我父亲去世前就离开了我们家。她到英国来的合同为期两
年,在我们这儿又多呆了至少一年。她思乡心切,而且我想她很明智,也讲
究实际,意识到该是按照法国传统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了。她已经从自己的
工钱中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款。
就这样,她眼里噙着泪花,紧紧地拥抱了她“可爱的小姐”,告别了我
们,剩下我孤独一人。
在玛丽走之前,我俩终于在姐姐未来的丈夫的选择上取得了一致的见
解。我俩过去一直在推测。玛丽始终坚信会是那位“金发碧眼、肤色白晰的
先生”(此文为法语,译者注)。
母亲小的时候跟姨婆住在柴郡。她在学校里交结了一位朋友叫安妮·布
朗,两个亲密无间。后来安妮·布朗跟詹姆斯·瓦茨结了婚,母亲嫁给了自
己的表兄弗雷德里克·米勒,两位姑娘一致表示永远也不能忘记对方,要始
终保持联系。尽管姨婆后来离开柴郡搬到了伦敦,但两人的联系从未中断。
安妮·瓦茨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母亲有三个孩子。两个相互交换彼此孩子在不同时期的照片,每逢圣
诞节向对方的孩子馈赠礼品。
当姐姐准备去爱尔兰旅行时,母亲向安妮·瓦茨提及了麦琪此次旅行。
安妮再三邀请麦琪由霍利黑德返回途中在柴郡的阿布尼堡逗留。她渴望见到
挚友的孩子。
麦琪的爱尔兰之行非常愉快。归途中她在瓦茨家小祝瓦茨家的大儿子詹
姆斯当时二十一二岁,就读于牛津大学。
他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嗓音低缓温和,谈吐不多。他跟大多数小伙子不
同,对姐姐麦琪表现得不很热情。姐姐发现这很蹊跷,引起了她的好奇。她
多次有意跟詹姆斯过不去,但却不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如何。不管怎样,她刚
回到家两人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往来。
其实,姐姐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之倾倒了,只是他
生性腼腆,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第二年夏天他住在我们这里。我一下于
就被他迷住了。他对我也很亲热,待我诚恳,从不戏弄我或者像对小孩子似
地对我说话,而是把我看作一个大人。我很喜欢他。玛丽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称他为“金发碧眼、肤色白晰的先生”,我俩经常在缝纫室里谈论他。
“我觉得他们两人好像彼此爱得不是很深,玛丽。”
“噢,不对,他很爱她,当她不注意的时候,他总是深情地望着她。他
们的婚姻一定会美满,而且很实际。听说他前途远大,生活作风又严谨,会
成为一位顶好的丈夫。
小姐性格开朗,聪敏,风趣,喜欢笑,找一位斯文稳重的男人作丈夫再
合适没有了。他也会喜欢她这种与他不同的性格的。”
只有父亲不太喜欢詹姆斯。但我想,这对一位妩媚动人,性情欢快的姑
娘的父亲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一作父亲的都期望自己的女婿是一位十全
十美的人物。作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媳往往也会有类似的苛求。由于哥哥一辈
子独身,母亲还不曾受到过这种情感的感染。
母亲始终未对她的两位女婿感到十分满意过,但她也承认,这并不是女
婿们的过错,而怪她自己。她曾说:“我也想象不出理想的女婿究竟该是什
么样子。”
我十一岁那年父亲离开了人世。他的身体是逐渐衰弱的,可是他的病似
乎始终未能确诊。长期为经济问题而忧虑过度无疑削弱了他对病魔的抵抗
力。
他去伊灵继母(我的姨婆)那儿住了近一个星期,拜访在伦敦的那些有
可能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的朋友。当时,找工作并非一件易事,只有律师、
医生、财产经纪人、法律顾问或者在军队服役等职业可供选择。父亲跟他同
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未受过任何职业训练。
父亲对自己的财产支配情况一直困惑不解,他去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
感到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也不知道祖父留下的这笔遗产都跑到哪儿去了。
父亲生活并不奢侈,开支总是限制在预计的固定收入范围之内。账簿上写得
都一清二楚,可事实上却是两回事,而且总会有一些好听的藉口或者说明某
项进款的短缺只是暂时的——用在某项必要的维修上了。毫无疑问,原来的
经纪人以及后来接替他们的经纪人经营都不得力。可都为时太晚,无法补偿。
他整日焦虑忧愁。天气寒冷,他受了寒,染上了肺炎。
母亲闻讯赶到伊灵,我和麦琪随后也去了那里。那时候他已病人膏盲。
母亲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家里从医院请来了两位护士。我心情沉重,整日
惶惶不安地闲荡,为父亲的康复而虔诚地祈祷。
我心中依然清晰地记着这样一个场面。那是午后一时许了我站在楼梯顶
端的走廊上,突然,父亲和母亲住的卧室门被推开,母亲双手捂着脸冲了出
来。跑进隔壁房间呼的一声关上了门。医院的一位护士走出来对赶上楼来的
姨婆说:“已经完了。”我明白了,父亲离开了人世。
葬礼是不带小孩子去的。我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徘徊着,可怕的事情终
于发生了。
我从来也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的事。房子里的窗帘都拉上了,点上了灯。
姨婆坐在餐室里,用她那特有的文体写着长信。不时悲伤地招摇头。
是呵,我的父母真是一对恩爱夫妻。我在家中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父亲
去世前大约三四天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多么想回到托基,回到她
的身旁。在伦敦的事情丝毫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但他感到一旦回到他最亲
爱的克拉拉身旁,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信中还说道,他想再次对她说她
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尽管这样的话他从前说过无数次。“你在我的一生中
具有极大的影响,是天下最好的妻子。光阴荏苒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感
激不尽你给我的柔情、钟爱和同情。愿上帝保佑你.我最亲爱的,我们不久
就会团圆的。”
我是在一只绣花封面的笔记本里找到这封信的。它是母亲出嫁时亲手为
父亲绣制的,寄给当时在美国的父亲。父亲一直珍藏着这个袖珍本,里面还
保存着母亲写给他的两首诗,后来母亲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