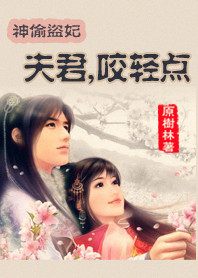睿亲王府的贝勒要出嫁-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格格!别跳!别跳!!奴才这就‘滚’!立即就‘滚’!!”苏克萨哈心惊胆寒地看她又是跺脚又是跳。背上冒起了毛毛汗。
“啪”气急败坏地蹦中。她腰际上地荷包掉了下来。苏克萨哈本已朝后退了几步。此时却一愣死了地上地物件。眉心一皱。迈步走来。
东愕然地瞪着他靠近地身影。不明白他到底想干嘛。却见他拾起荷包胆大妄为地放到鼻下一闻。神情严肃得好像九门提督办案:“格格——这里头放地什么?”
“管管你屁事!!还我!”
“奴才该死!”
东一把抢过荷包,横眉倒竖的喝叱着。若是将她换身行头,长辫垂后,便是和曾经的“贝勒爷”相差无几了。
苏克萨哈愕然的一愣,将荷包奉还着痕迹的抿了嘴:想当年,格格为此没少挨王爷和夫人的罚,想不到四阿哥一走,她的本性就渐渐又露出来了。
“你闻什么?”东拍了拍荷包上的灰,没好气的问。
“奴才奴才怕格格犯迷糊,放了麝——放了香料在里头。”
“这——这管你什么事四爷都不曾这般神神叨叨,你倒一惊一乍起来了!莫名其妙!!”
“——那是四爷根本就没对格格上心。”
“你说什么??”正低头挂着荷包,他大为放肆的话惹得东一愣。
他公然胆大包天的说起了主子的好歹!就算他出身世家两代为将,且均出征过沙场。也不至于让他有恃无恐得连规矩都忘了吧?!
打量了他一番,想到他作为父亲的贴身侍卫,鞍前马后的跟老爹形影不离恐怕多少会受他的影响。
这些对叶布舒的抵触情绪,很有可能是从老爹那里得来的。她渐渐冷静了下来,再细细一想,老爹对叶布舒的偏见,还不都是因为心疼她这个宝贝女儿吗!
醒悟的抖了抖睫毛终于发现了老爹的心意,暗骂自己笨得可以!心情乍然平顺了。
“得、这些话不能乱说得传出去,对你对四爷都不好!
苏克萨哈抬起眼帘看了看她眼神深邃,不知死活的又冒出了一句:“格格被迫下嫁的苦才都知道,四爷从前对格格好,奴才没话说,可是接二连三的出事,奴才实在怀四爷对格格的爱——到底有几分诚意!”
不善言谈的苏克萨哈居然头头是道的数落起主子来,东惊异的皱起了眉头,实在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他口出说出的。
她扑闪着凤眼,僵在了那里,心中翻涌起了惑:他到底是那股神经搭错了线?叶布舒的爱有几分诚意,需要他来担心吗?他难道不怕这番话给自己带来麻烦?
苏克萨哈的视线扫过,似乎在掂量那番话在自己心里的重量,回过神来她厉声说:“主子的舌根也敢嚼!好大的胆子!闲话这么多也不怕惹祸上身?你别什么都听阿玛的!自己得有分寸!!”
“格格训斥得是!奴才该死!不过——”苏克萨哈顿了顿,低不可闻的淡淡补了一句:“果王爷当初肯采纳奴才的建议,格格根本不用受这些苦难,四爷——也不会有机会娶格格过门儿!!”
“够了!”东大喝了一声,气急败坏的左右一瞄:“你到底今儿是怎么了!阿玛好歹将你视为亲信、他待你不薄吧?!你建议过他什么?他没采纳过什么?这些话是能随便说的吗??从今往后再不许提及此事!”
“蔗!奴才知罪、奴才以后永远不会再提这个事了。”
目不转睛的瞪着他,东感到了不安:他只是一名贴身的侍卫,他建议过阿玛什么?难道他有这个资格,开口建议阿玛谋权篡位吗??阿玛到底是怎么看待他的?
一阵马蹄声骤起,府邸门外一片嘈杂,二等辖的通报声扬起:“承泽亲王到——”
苏克萨哈一愣,朝后退了一步,恭候在一旁,带起了
表情。东扭头看向府门。一顶官轿落定亲王监疾步上前,确认来人之后,快步朝书房走去。
轿帘一掀,硕塞弯腰跨出了轿那带着世故和精明的脸上,有着一股旁人难以窥见的谨慎,恐怕鲜少有人知道那一份谨慎,是由根深蒂固的自卑演化而来。若不是有“亲王”这个光环照耀,恐怕这一份“谨慎”就会变成让人笑话的“畏首畏尾”。
他的今天得来不易,所以他会加倍重视自己的仕途,不管能不能抹去母亲带来的那些屈辱,他的地位越高,聋子和瞎子就会越多!这一条定律早就摸透了。
东已来不及回避,只好落落大方的上前,在硕塞的惊喜中淡然的和他寒喧到:“五弟,你怎么来了?找阿玛有事儿吗?”
“臣弟跟四嫂真有缘,想不到你今天回了娘家。看来今天臣弟是不虚此行。”硕塞答非所问,着若有若无的笑意拍了拍袍子。
东尴尬的转过了脸去皮疙瘩掉了一地。恰好看到了后面还跟着一顶轿。看徽记应该也是他府上的轿,此时轿夫已将轿轻松的抬到墙边放好,至此,她才断定那只是一顶空轿而已。
她扫过眼看了看硕塞,心里打了个问号:他难道是来接阿玛进宫赴宴的?什么时候起他和阿玛走得这么近了?
“四嫂,臣弟是来接睿王进赴宴的可有异议?”
“我”不料,硕塞察言观色的功夫太到,立即就揣摩到了她的心思。东语塞的垂下睫毛,迟钝得不知说什么好。
“奴才苏克萨,叩见承泽亲王!”
苏克萨哈上前来打了个千东从窘迫中拉了出来。硕塞看了他一眼,复而看向东面色沉了沉:“得、起来吧!”
“主子——主子等急了吧!恕奴才无能、奴才该死!!奴才叩见主子、叩见承泽亲王!”
苏克萨哈刚起身,小德子满头大汗的跑了过来近跟前,被一大帮子人惹得懵懂的一愣即伶俐的认错在先,又捣起他那颗“葱”来。
东没好气的俯视着他:“得!得!瞎捣鼓什么呢!随侍处的人在磨蹭什么啊?不是让你催促着吗?人呢?轿呢?”
“回主子的话,轿顶无故内陷,轿夫们现在都忙着在补修!”
“啊?出府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是啊——可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它它现在就——”
“唉!得!那怎么不先用睿府的轿呢?我以前那顶轿呢?!”
“是啊、主子!奴才见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这不先过来请示您吗!那??”
“还‘那’什么啊!?我站得两腿都发软了、还不快去?!”
“蔗!!——奴才这就去!!”
“回来!”硕塞怔怔的看着主仆二人对话,冲小德子的背影喊了一声,将他叫了回来。他扫了苏克萨哈一眼,对着小德子说:“别去了,就让我的人送你家主子回府吧。也省得睿王担心。”
闻言苏克萨哈缓缓抬起了眼来,估量的看了看他,一欠身说到:“奴才奉命送格格回将军府,怎敢动用承泽王爷的官轿,还是就用睿府的轿吧。”
东看看右看看,被他们“二龙戏珠”的架势弄得郁闷了。硕塞也太狡猾了吧,没想到他直接拦住了自己的奴才,那自己哪里还好推翻他的话呢!那不是让“客人”丢面儿吗!况且他把阿玛也抬了出来,真是“计划”周密啊!
硕塞的狡猾,让她期期艾艾的想起了叶布舒,看来他们兄弟二人最相似的一点就是一样的——狡-猾!心底一丝酸涩飘过,她微蹙起了眉头:也不知道那个混蛋在湖广怎么样了?连封信都没有,心肠太狠了吧!
一众人都没了言语,气氛僵僵的,感到几道眼光唰唰投来,似乎是等待她开口选择。东收拾了情绪扫视了一眼。此时,她既不便当着外人的面让苏克萨哈下不了台,更无法回绝硕塞天衣无缝的好意。
听说有了身子的人,脑筋都不太够用,有的会傻上好几年。此时她是深有体会,傻乎乎的陷入了两难中。
小德子请示的眼神飘至,东翻了翻眼帘,立即递了个眼色给他。他转了转眼珠哈腰说到:“奴才替主子谢承泽王爷的好意,二位大人一个有命在身,一个盛情难却,奴才斗胆献计:主子就由苏克萨哈大人相送,乘王爷家的轿回府吧!”
“哈哈哈!四嫂、你可真会调教奴才,瞧瞧、多伶俐啊!这个计献得好!就这么办!”硕塞意味深长的扫视了众人一眼,扭头朝着他的家奴一挥手:“来呀!将四福晋送回雨儿胡同的将军府!路上谨慎点!快去快回!我逗留的时间不长,还等着和摄政王一同入宫赴宴呢!”
东干笑了两声,用眼神赞了小德子一把,随即却自己叫起苦来:这个计策当然献得好,既保住了客人的面子,又达成了家奴的任务!可是自己却落了个两面受夹;既欠了硕塞的人情,又给了苏克萨哈折磨自己脆弱神经的机会。谁来顾及顾及她呀?
抓住硕塞话里的缺儿,她开口做了最后一搏:“五弟,我看就算了吧,你和阿玛还急着入宫呢!别耽误了正事儿!”
“四嫂真见外!时候还早、那事儿耽误不了!既然臣弟都开了口,今儿必然是将四嫂送定了!想来睿王也不会责怪,他老人家对女儿的疼爱,那是出了名的呀——哈哈哈!”
【第八十章 欢喜冤家】
四福晋、您走好!”
东轻轻耷拉着头,丧气的瞄了硕塞的二等辖一眼,悻悻的干笑说:“得!快回吧!你家五爷还等着呢!替我谢谢你家主子!”
二等辖回了话,微微一欠身,招呼轿夫们离开了。冲着一干人等的背影,东这才露出了愤愤然的神情,为刚才被硕塞“设计”了一通,憋闷起来:好个硕塞,欺负自己脑子不灵光还是怎么的?一再堵上自己的嘴,让自己哑口无言不说,最后还把二等辖也支来。他眼中的估量分明是怀苏克萨哈和自己有什么不轨!!这二等辖怕是他用来一路跟随,探个究竟的吧?真恶心!
“你还不走?”扫了苏克萨哈一眼,东更没好气了。
“格格、奴才这就回了,您保重。”苏克萨哈不比她更舒坦,被硕塞的二等辖一路上侧目打量,惹得一肚子窝囊气。
听到他硬邦邦回话,再一看那黑沉沉的脸,东明白了几分,看来他们俩都被硕塞含着监视意图的行径弄得没了好气。不过,不过他苏克萨哈尚且有份让自己气结,此时便应送他两个字——活该!
一转身,东扔下句话,跨了府门:“回吧!你今儿横竖也完成了任务,不亏了”
身后的人僵的,好像有点受伤,不过东也管不了太多,扶着小德子的手臂头也不回的走了。倒是小德子感到主子对苏克萨哈的态度太恶劣,不由得频频回头挤眉弄眼安慰着他。
“福晋!您可回来了!奴才给福晋请!”
“承惠——你侯在苏勒居做什么?”
焦承惠快步从;门口迎上前来打了个千。一干婢女听闻动静也纷纷迎了出来:“福晋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呢!奴婢还以为您要留在睿府用膳呢!”
锦儿念着和绣儿涌了出来。小德子便可怜巴巴地被挤开了。叽叽喳喳地聒噪乍起。顿时将东地郁结赶跑。祝玉缓缓走在最后。手上竟然端着热气腾腾地一碗汤:“福晋!您地乌鸡红枣汤咱给热了一次又一次!快进屋把汤喝了再说!”
焦承惠白了她们一眼。要禀报地话只好咽了下去。随着东进了厅堂。她拂了袍面坐上了炕过汤碗喝了一口:“得!你们别闹了。我不过是出去了一会儿。闹得跟班师回朝一样!你们先下去吧。焦公公有事要禀报呢!”
焦承惠抿嘴一乐:“福晋英明!奴才记得不曾提及有事禀报啊?”随着婢女们离去。他哈了哈腰将信函递了上去:“也不是怎么急事!不过奴才以为——福晋多少还是希望能尽快看到这封信地!”
“信——谁地?啊!信?四爷湖广营地来地??”
“啪”地放下汤碗东抡圆了眼接过信函来。焦承惠识趣地欠了欠身退下了。房内静谧无声。东展着信纸地手竟有些发抖。一股冲鼻地酸涩在低头瞄到微微隆起地腹部时袭来。
“福晋,战局紧迫,耽误了爷书信报平安可曾挂记?也罢!兴许福晋乐得做自由自在的人,巴不得爷没有音讯。虽然如此,如今有了缓劲儿的机会,爷还是得来打扰福晋的宁静生活,家书是必然要写的!”
看到这里内心凄凉的琴声嘎然而止,眨巴着眼睛一愣,她蹙眉将炕桌拍得“啪啪”的响起来。他鬼话连篇说些什么啊!明明是他迟迟不见来信,害得自己担心,如今还好意思振振有词的挖苦!
“爷送给福晋的礼物,福晋带在身边了吗?玉可护身,就算不华贵也有它自己的价值说呢?另外有件事儿,爷得叨絮叨絮你!连你哥都知道你有了身子、爷却蒙在鼓里!你说、你这个福晋是不是当得太蹩脚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见你来信支个声儿,什么意思呐?”
翻了个白眼,东抖了抖手中的信纸叶布舒这通毫无文法可言的信,搞得失笑起来:这是才子写的信吗!尽是平日里说话的口吻他万恶的面貌挥之不去的展露在自己面前!
他显然还在担心自己没有悟出“珠玉”的道理,写信来提醒自己。不过怕是密封的家书,他也绝不肯直言不讳此看来,兴许他是故意弃文法不用,这样的小心谨慎不但能排除半道被**了信件的内容,也能排除他人模仿笔触撰写假的家书。
“自从听说你有了身子,爷终于可以放心了,至少三个人很难再花前月下吧!哈哈哈!爷还是不负众望啊!”
瞧他的得瑟劲儿!东刚接着看了两句,便看不下去了,红了耳根不住的暗骂着他:且告诫了他别再提及那个人他怎么就车轱辘话来回说呢!这近两个多月来,“那个人”也并没有趁着他出征做出什么逾越的事,甚至人家连照面都不曾和自己打过,他到底是聪明过头了还是怎么地!
莞尔,念及他的得瑟劲儿也是因为他这个一心一意守着自己的人,终于在二十好几的“高龄”有了做阿玛的机会,东抿嘴一笑,垂下睫毛看了下去。
“阿玛的军纪太严,爷可不敢随意使用‘六百里加急’传家书,想来这封信到福晋手里,至少得十天半月,那时天气恐怕也得转凉了,福晋别迷糊得跟个什么似的!厢房的火盆就放一个好了!别傻乎乎的差人搬好几个进来!觉得冷就把皮毛坎肩穿上!那一堆火盆闷在房里,是人待得下去的吗?”
不自觉的“恩”了一声,东慢慢喜欢上了这份信,虽然全无章法,却让人感到他就在身旁。想到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