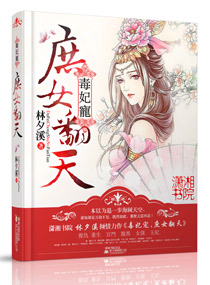公侯庶女-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含章自嘲一笑:“如此说来,我还是个有福的。”
赵昱清浅一笑,转开话题道:“我十二弟素日很好奇边关的事,碰巧今日进宫,就把他带出来见见你。有什么冲撞之处你不要见怪。”
含章揭开茶盖,拨了拨在茶汤上漂浮游动的青碧色茶叶:“王爷何必客气,我还要感谢十二皇子这番话。原来我们是不会被遗忘的人,我们所作的一切自有人会铭记感恩,哪怕这只是安慰之语,我听过之后心里也好受多了。”
赵昱听得心头一动,不动声色扫了含章一眼:“公道自在人心,史书上也会有后人公断。只是你今天似乎心情不太好?是不是我昨晚冒犯了你?”
含章手上一松,茶盖汀一声掉在茶盏上,略有些歪斜,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她伸手将盖合稳在盏上,意兴萧索地摇了摇头:“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想到一些往事也会情绪低落。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多谢王爷关心。”
听出含章话里的敷衍,赵昱眼中闪过一丝黯然,他幽幽叹道:“可惜在你需要别人宽慰的时候,我却没有在场。”
这话里大有深意,含章颇是吃惊,不由抬头看向赵昱,惊愕得忘了反应。
赵昱微微一笑,眼中煦暖和畅,眸光温柔看过来,有如春风拂面。
第六十二章扰纷纷。。。
含章似乎突然变成了哑巴,眼中少有地透出一阵茫然。赵昱仍是温柔和煦的样子,眼中淡淡柔情,如浅色的蜜汁一般沁甜溺人,几乎叫人生出几分被呵护的幻觉。
“你怎么……”含章回过神来,想发问,但话一出口却又顿住,她随意移开了视线,重变得粗糙的手指轻轻拂过茶杯,云淡风轻地一笑,换了说辞,“王爷对人都是这样细致体贴么?那与你相交之人岂非甚有福气?”提到有福两字,她眼中闪过一丝自嘲。
赵昱莞尔,他仪容不俗,温雅浅笑之下便如春阳照融冰,一片波光潋滟:“纵是细致,也只是对亲近之人,这世间本就纷繁,又哪来那许多心思来用。”
这话倒不假,依含章亲眼所见,他对赵慎君和赵昕几乎像是寻常百姓人家的兄长对待弟妹一般和蔼可亲。
对他话中亲近之意,含章却不以为意,只淡淡道:“诚然如此,王爷既是我的大夫,对病人花一两分心思倒也不奇怪。”她一向感情不外露,今晚只是偶然,但即便这样,最脆弱的时刻也已经过去,此时早已回归常态,仍旧是心防甚重,油盐不进。也许被赵昱说中了,含章需要别人宽慰的时候他已经错过了。
赵昱笑笑,不置可否,但眸中温情却渐渐凝固,目光也深邃起来,辨不出其中情绪。
含章没有见到他的回应,已是意料之中,她摇头一笑,闲适地靠着桌子,屈指在桌上断断续续轻敲,口中缓缓轻唱道:“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她声音本就微低哑,哼唱间自有一番悲壮苍凉之意,但这份悲苍并不像一个年轻的将领应有的那样,在风吹尽尘埃后仍能见百折不挠的内劲和慷慨,相反,风沙残烈将她的锐利和明亮磨去,只剩下沉寂黯然,但这又不是认输或是放弃,而是如同历尽劫波的老人那种看得透彻之后的索然无趣。
她虽然只有二十岁,可是心已经老了。
这份苍老是含章从战场死里逃生回来长久的昏迷中第一次醒来后就已经在心里萌芽,一个意气风发有的少年将领,与好友弟兄在草原纵马扬鞭,神采飞扬,手下几万兵马,意气风发何等豪迈,可是当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苍鹰的翅膀悄然折断,至亲的义兄身首异处,曾经所有的一切成为泡影。
她还太年轻,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只能硬生生将愤懑不平埋进心里。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些不甘逐渐萌芽出土,如同坚韧丑陋的荆棘盘踞在心底阴暗处,暗暗地呐喊着要让幕后黑手血债血偿。
在最初的时候她做得最多的梦就是自己提着大刀骑着快马,半空中一刀劈下,眼前敌人那大片的黑色人影血肉四溅肢体横飞,就像她单枪匹马去给亲兵报仇一般畅快淋漓快意恩仇,可是一梦醒来,残疾的腿无情地将现实摆在眼前,其他人眼中遮掩不住的怜惜更让她难堪。
经历了养伤那几个月的低迷消沉,沈元帅无奈之下将她送回京城,期望新环境能让含章有所改变,更希望薛家这棵大树能够为她提供荫蔽。这一举歪打正着,扑朔迷离的事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可是还不及松一口气,便发现事与愿违,明明真相就在眼前,却不能再前进。
在第一次看到那枚金葵花锞子的纹路时就已经隐隐有了预感,事关皇家,绝非普通官员叛国那么简单,只是她不愿放弃,还抱着一丝幻想继续查下去,但事实终究是残酷的,眼前是一座巨山,她撼不动,也无从着手。
她劝赵慎君放弃,可是自己的心里仍是在煎熬中,仇恨的荆棘被硬生生砍断,只有一点根还顽强地留着,于是心头满目疮痍,徒留千里荒凉。
赵昱静默了一会,背了手,慢慢踱出了屋。屋外一轮月已然升起,月华如练。
等待七日的苦药喝完的那几天,赵昱照旧来督促含章服药,却注意着不再有特别的言论。那晚带了几分暧昧的情愫被对方的冷淡反应压制下去,两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恢复往日的相处模式。
赵昕和袁任仍是时不时就来串门,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含章不像传说中的偶像那样遥远不可捉摸,而是一个触手可及的人;便带着好奇来亲近。赵昕灵秀内敛,袁任直率爽朗,这两个人给太医局里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喧闹声和不同的色调,但含章却是渐渐寡言少语,越来越像一片荒漠,静默荒凉。虽然她没有刻意说或者做什么,其他人仍是感觉到她身上那浅淡的疏离,又或者,只是一种从内而外散发出的深深疲惫。
这日本来约好要在小院里比试射箭的,袁任却迟迟不来,直到日上三竿才姗姗来迟,进了门便挠着头解释说家中有事故而来迟。
赵昕本来在教含章玩双陆,听了这话便关心道:“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袁任噎了一下,他不自然地瞟了含章一眼,见她正抚着下巴专注看着棋盘,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便蚊子般哼哼道:“大嫂回家了……进门的时候就晕倒了,家里忙着请大夫。”
含章抬起头:“她病了?”
两人目光相对,袁任一个激灵,忙转开视线,难以启齿中夹杂着些微矛盾的喜悦之情:“她有身孕了。”他顿了顿,忙补充道:“才两个月呢。”亲近一点的亲朋好友对袁信为兄弟戴孝一年的事都略有耳闻,如今距离期满之日只剩短短一段时日却传来这个消息,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脸了。袁任强调时间,也只是想让自己哥哥不至于太难堪。
两个月前正是中秋节前后,含章目光微微动了动,将手中的棋子下在棋盘上,展颜道:“后继有人乃大幸事,真要恭喜袁二哥了。”
只可惜这两天便要开始断腿重续,这些日子怕是没有机会上门道贺了,况且薛定琰怕是不会欢迎自己登门,也没有必要去给他们添堵。
袁任小心翼翼觑着含章表情,见无什么不妥,这才松了口气,笑道:“沈姐姐你开心,大哥知道了也会高兴的。”
兄长是长子,他的后嗣是家里的大事,父母早先为此事不知操了多少心,如今总算得偿心愿,家中上下全都喜气洋洋,这段时日因兄嫂闹别扭而让全家上下惶惶不可终日的憋闷郁沉一扫而空,自己也才安了心。况且沈质并没有死,卢愚山又非嫡亲兄弟,戴孝大半年情理上也说得过去了。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情绪,若袁任是个外人,见了袁信这样大概还会腹诽几句言而无信,可是毕竟骨肉至亲,心中的天平一开始就向着哥哥倾斜了,小侄子即将诞生的消息就足够他欢欣鼓舞不想其他了。
含章仍是淡笑着,和赵昕下完棋便携了弓箭去比试。她的箭术是卢愚山手把手教的,虽然比不上养由基百步穿杨,但次次红心也并非难事。
这次比试是袁任提议的,他本还有几分跃跃欲试,因为自己箭术在玉京里也数得上名号,便想趁此机会挑战一下含章,但见了这情景也不由得心悦诚服。
几人切磋了几轮,含章自是箭术精湛,袁任却也不遑多让,不愧为将门虎子。最让人意外的是赵昕,他虽不能次次红心,却也能保持在八环以内,倒让人刮目相看。
最后一箭射出,赵昕放下弓,言笑晏晏:“献丑了。”
含章笑了笑:“很不错。”这位皇子先天不足,身体单弱,能有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听到含章的赞赏,赵昕眼中一亮,两眼笑得亮晶晶的,大概对每个少年而言,战场总会是他们在某断时间里魂牵梦萦的地方,好男儿总盼着身带吴钩沙场征战,建功立业,无关身份,无关身体强弱。
“十二,该回宫了。”赵昱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他一袭白衫立在柳树下,乌发白衣,随风而动,一派风神秀彻。
赵昱在这两个少年心目中颇有些威望,赵昕忙应了,恭敬行礼告辞,跟着侯在一旁的宦官离开了,袁任依依不舍地看了眼还没有分出胜负的箭靶子,也放下弓告辞走了。
含章将弓都拢在一处,道:“王爷今日怎么又有空来?”
赵昱沿着鹅卵石的小路慢慢走过来,笑道:“今日在太医局里办事,听得你们这里很是热闹,便顺路过来瞧瞧。”
含章微侧了头,目光扫了一眼围墙那一边平王别院里的亭台楼阁,意有所指道:“只怕不是顺路吧?但另一位也曾与我有一面之缘,来看我却过门而不入,难道是我有什么不妥?”
她方才看得仔细,那跟着赵昱一起偷看的人正是寿宁长公主的幼子梁俭。
被含章一语道破,赵昱却并不显得很惊讶,他也顺着含章视线看了一眼绿树掩映间别院小楼的一角,方才自己和友人正是在那小楼里远远看过这处小院,不想仍是被含章发现了:“隔了这么远也能察觉,沈小姐眼力果然极好。”
含章一笑,半真半假道:“练箭者视小如大,视微如著,在纪昌眼中悬虱都能大如车轮,更何况是两位比虱巨大千万倍者?”
纪昌学箭,在五年间练出了将虱子放大到车轮大小的眼力,终于学成箭术。
赵昱一愣,哑然失笑道:“如此说来,我等在小姐眼中岂不是巨如金刚?”
含章摇了摇头,不置可否,将弓箭分门别类挂在屋檐下的兵器架上。
赵昱负手慢悠悠走过来,仿佛漫不经心道:“阿俭是来和我通传一件事,之后闲聊了几句便走了,所以不曾来此。”他停了一下,见含章没有反应,只是在整理箭翎,便继续道:“十四妹就要定亲了。”
含章手上不停,顺口应道:“那可要恭喜十四公主了。”她和赵云阿并不融洽,几次见面都有些火药味,这些玉京里知道的人怕是不在少数,所以在赵昱面前也不必遮掩。
赵昱眸中流光一闪,缓缓道:“未来驸马便是起居舍人程熙。”他一边说,一边静静看着含章。
含章恍如未觉,一丝不乱理好弓箭,回身笑道:“程大人与我也算相识一场,他与公主也是一对如花美眷了。”她谈笑自若,风神磊落,并无一丝异样或勉强的情绪。
赵昱冁然而笑,他点了点头,不再多说,垂目间看见桌上未及收拾得双陆残局,白棋已经全部占全位子,而黑棋被逼得局面四散毫不得法,赵昱的手扶在桌沿,白皙细长的手指敲着桌面,摇头笑道:“执白棋的必是十二。”
含章走过来,道:“何以见得?”她并没有兴趣多问此事,但对方既然有这个兴趣,不妨看看他想说什么。
赵昱抚袍坐在放在赵昕坐的位置,点着黑棋道:“小十二心思缜密,多思善想,总能将对方杀得惨败,下双陆他是高手。”
说赵昕心思缜密含章倒是同意,但对于赵昕,她也有些许疑惑,便趁此机会问了出来:“不是都说宫禁森严的么,怎么十二皇子总能出宫?”尤其是如今皇帝身体欠安,身为幼子自然是随侍在旁,不该这样频繁往外跑。但涉及皇帝身体状况,这话含章一个外臣总是不便说出口的。
赵昱自然明了她的意思,便笑道:“父皇已经大安了,又说宫里感染风寒的人比宫外还多,怕十二也染病,便叫我常带他出来散散心。我那府里空荡荡的没有意思,不如带来太医局,这里医者众多,若他有个症候也能及时发现。”
原来如此,含章又想询问赵慎君的近况,但话到嘴边心中念头一转,最终也没有问出来,对于赵慎君来说,如今只有越低调越好,自己的关询只会让她引得别人关注。
赵昱见她低眉沉思,便手一拂弄乱了双陆棋,黑白棋子纷纷倒在黄花梨木镶嵌螺甸的盘上,四散滚落,咚咚乱响,一粒青玉填朱砂的骰子滴溜溜滚过大半个木色棋盘,咔啪一声脆响掉落在汉白玉石头桌面上,他唇一弯,笑道:“来一局,如何?”
第六十三章喝酒(上)
这一日恰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小雪。淳龙二十二年的冬天是个暖冬,直到现在都只比寻常秋日寒凉一两分,虽是小雪,却连雪的影子都没见着,只有一轮温软的日头挂在天上,晒下些又凉又暖的光。
中午时分,临街的酒肆望仙楼很是热闹。这座酒楼有三层,底下两层都是大堂,人满为患,而楼顶一层则是用半人高的白绢乌框屏风隔开的雅致小间,比起楼下的嘈杂要清净许多,堂中坐了个三弦师傅,旁边一个秀丽的红衣小唱女正微摆柳腰、轻启朱唇,将一曲湘妃怨唱的酥媚入骨。
古时舜皇南巡死于湘水之滨,化为湘水神,称湘君,两位妻子娥皇、女英一路寻到湘江边,泪洒斑竹,双双投水而死,死后成为湘水女神,称湘妃。这一番浓烈的痴情,几千年后听来仍是哀怨缠绵,勾人心弦。
那小唱女正是二八年华,容颜鼎盛的时节,肌肤饱满,眉目灵美,一双黑水晶似的大眼熠熠生辉,顾盼生情,惹人垂怜。待檀口轻张,唱到“尽叫得鹃声碎,却教人空断肠。”一句时,她微合明眸,似瞧非瞧,似多情似含怨地扫了堂下众人一眼,那娇媚的摸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