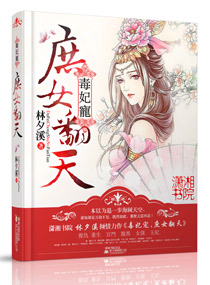公侯庶女-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耗?
但袁信眉目深凝,意志已定,含章知道自己改不了他的想法,又势单力薄,帮不了对方,便从腰带上取下明月胡乱往他手里塞:“那你拿着这个,无论如何,要留下命来,你的孩子,你还没有看到他出生呢!”言语间,不自觉已有泪水滚滚而落。
提到儿子,袁信眉目柔和了些,他看着含章咬牙忍泪的样子,低低道:“他有你这个叔叔,我不担心。我知道你不喜欢薛家,不喜欢定琰,但是看在我份上,你绝不会不管你侄子。”顿了顿,他又道,“老三,别怨我。”时间紧迫,已容不得多说,于是他狠下心,拂开含章双手,三步并作两步迈出了屋。
含章站在一片狼藉中,眼睁睁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只觉得背后满是凉意,想要抬步去追,手脚已僵硬难动,想要张口呼喊,却发不出声音来,只能不甘心地睁大双眼,看着那抹锁子甲的幽深光泽消失在夜色里。
作者有话要说:
╮(╯_╰)╭,我说了我会勤奋的,二更补偿大家这段时间等更的郁闷,╭(╯3╰)╮
袁信的谢幕以及含章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懵懂少女情怀。
第七十二章养寇的闹剧
不知过了多久时候,屋内火盆散落的炭火在地上忽闪了许久,渐渐熄灭,再没有一丝暖意,风从敞开的门吹进来,冰寒彻骨,吹得一地炭灰扑腾乱飞,对面一墙之隔的平王别院里也安静下来,火光已灭,呐喊声也小了,只不时被风吹来些断断续续的呻吟。
小六扶着含章立在屋中央,眼见自家小姐脸上泪痕犹在,却血色全无、面无表情的样子,他不免有些害怕,嗫嚅着道:“小姐……”含章冰凉的手指动了动,慢慢抬起胳膊将明月插回腰带上,一把抹去脸上湿痕,发哑的嗓子低声道:“把桌椅都扶起来吧。”小六忙应了,声音极轻,像是怕吓到她一般。两人关好门窗,把桌椅扶正,小六从小药炉里掏出燃着的炭重新生炭火,含章便坐在床前脚踏上收拾地上的衣物,许多都被踩踏得不成样子,她一样样捡起来,仔细叠好放置,行为并不反常,只眼神有些发木,手也是机械地动着。
小六把地上药渣和药罐碎片扫起,忧心含章还没有服药,犹豫片刻,匆匆出门去太医局药房寻药。
屋内含章手上动作愈发迟缓,最后彻底停了下来,整个人静得像尊石像,当年卢愚山在眼前阵亡时,她脑中满是疯狂恨意与斗志,恨不得立刻化为烈火与狄人同归于尽,而此刻却是脑中一片空白,不知所以。
含章至今摸不透袁信或者袁家到底在这些事中是怎样的角色,回京后两人寥寥几次会面都来去匆匆,言谈间也甚多保留。
但经历了这些事,了解了那些内情,含章再不如以前心思单纯。
战场之人,原本是朝不保夕,不知何时就会马革裹尸,早于生死之间看淡,但若真是死于敌手,忠心殉国,死得其所,也只会豪情壮烈,慷慨满怀,不会有丝毫怨愤。
可卢愚山身首异处,死得惨烈,虽是为国战死沙场,却实是被己方奸细所害。这一个血染就的忠字,不知已被污了多少可笑色彩。昔日的袁信,何尝不是一个胸襟壮阔不下卢愚山的骁勇之将,厮杀征伐间每每身先士卒,何曾畏惧过生死,但他今日之所为,协助反王谋逆,乃十恶不赦之首罪,彻底与忠字无缘,只落得逆贼一流。
忠与不忠,都是同样下场,做了别人棋盘上的棋子,鼓掌间的尘埃,可悲之极。含章看着自己未愈的腿,突然深感茫然无措,她不知道自己腿伤愈后,回到边城,又该以怎样的心态来守卫国土。
为民?在位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争权夺位下又何尝不是无数百姓死伤。君若不爱民,将又有何用。
为君?君王之威,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位高者如祖父也只能如履薄冰,正面对敌要殚精竭虑,背面对君亦要战战兢兢,位低者如卢愚山及众军士,不过是命如草芥。
为国?什么是国?百姓与君耳。
含章脑中陷入一个怪圈,无论怎么想都是死结。她心里隐隐有着恐惧,一直以来的从不曾动摇的纯忠之心,终于经受不住长期的疑问和惶惑,满是细碎裂纹的表面又绽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
沉思中的她警惕性降低,没有发现墙后的密室门不知何时又开了,赵昱从中缓缓走出,看了看屋内凌乱,皱起了眉头,抬步走到含章身边。
含章察觉到异样,忙收敛心神,把手中叠好的衣服放在一旁,低声问道:“今晚之事,王爷事先知道多少?”赵昱在密室中也能察觉敌人已走,定是有机关可以探听外面动静,方才那番混乱必然已知晓。既然之前他已经承诺过会知无不言,含章此刻正有满腹疑问不得纾解。
赵昱有些意外,原以为她此刻伤感不安需要有人宽慰,却不料她这么快调整思绪,已经用心思猜到一二,他略一犹豫,道:“今日在城外遇见有官兵盘查,察觉不对劲,便带着小十二绕路回了城。”
“哦?”含章往后微靠在床沿,淡淡道,“王爷没有趁乱避走,而是赶回了城,看来已是胸有成竹,这场叛逆必不会成功。”他们兄弟从郊外皇陵回来,遇上这事,有两条选择,或是进城,或是赶紧避开逃走。若以常理,逃难定是远离是非之地才好,而赵昱却反其道而行,偏往危险处去,实在是太过冒险,须知若是对方谋逆成功,一朝封城,那便是瓮中捉鳖,任他插翅也难逃。
赵昱思量片刻,他与含章虽是相识,但彼此立场截然不同,若要实话实说,未免有交浅言深之虑,但他无意隐瞒含章,直言道:“此事已走漏不少风声,相关人等并非没有准备,只没提防到竟是提前发难了。”
听得言外之意,这叛乱早不是秘密,含章纵然事先有过怀疑,也不免一惊:“皇上可知晓?”
皇子揣测圣意乃是大忌,赵昱不便直接回答,只低叹一声,道:“父皇虽身体略有不适,但也还耳聪目明。”
如此说来,怕是这叛乱最后只会成为有心人眼中一场可笑闹剧。含章听得舌头发苦,她周围之人几乎都参与其中,似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唯独只有她事到临头才得知。
“既然知道宁王有异心,为何不早些将他拿下,非要等到他做下这些恶事连累这么多人死伤?”自古谋逆乃大罪,今夜的事,已断送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而事情平定后,受牵连者更不知凡几。
赵昱沉默着展平衣襟,慢慢低□坐在脚踏另一侧:“玄武门之变,太宗受尽天下人唾骂,郑伯克段于鄢却无人非议,占尽了仁义之名。如今有人也想效仿郑伯。”
这便是某些人想坐实了逆谋事实,一举除掉对方。说白了便是养寇二字,容忍甚至推动对方做大做强,待到时机成熟,一举歼灭。于王权争斗上实属兵行险招,但若用得好便能一劳永逸,只是对百姓而言却是一场横祸。这也印证了含章关于京城开赞唐太宗之事的猜想,明面上是反王为叛乱造势,但在暗地里不知有多少人各怀私心在推动。
外头越发夜深风疾,一道烈风呼啸刮过,冲得窗纸哗哗作响,隔壁院子的哭叫声听起来更尖利了些,似是近在耳边。含章和赵昱两人坐得极近,呼吸相闻,她几乎能感觉到对方身体的热度,却毫无温暖之感,只觉得自己周身一阵一阵的寒气,忍不住偏过头仔细打量赵昱,眉目是已经熟悉了的,但又透出几分陌生来。
此时这屋内危险并未消除,而赵昱仍是沉静端方,举止有度,毫无一丝失态,但在含章看来,只觉得说不出的讽刺。
自从她发现那片残纸后,许多原来奉为至高准则的东西接连被颠覆,今夜这些□的真相更是清楚直白摆在眼前,即便想掩上双眼捂上双耳假装没看见没听见,也是不可能了。两人静静听着,待那哭声渐渐小下去,含章方徐徐问道:“王爷今晚特地来我这里躲避,是因为知道前来搜查之人是袁信么?”
“我手下人中出了两个奸细。”赵昱知她必有此问,也并不说是与不是,只解释道,“事出突然,不知那奸细供出多少别院的隐匿之处,思来想去也只有这里还算秘密。”他略顿,又解释道,“我并没有……”不知想到什么,眼光微暗,话说了一半,终究没有说下去。
对这半隐半藏的话,含章并无兴趣细问,她此刻心里只关心另一桩事,眼神似是绝望中燃起一点希望般矛盾,咬了咬唇,道:“王爷和皇子今夜逃过一劫,全是袁信的功劳,待到事情平息,不知能否为他求情。”
赵昱垂下眼帘,默然片刻,终究不愿骗她,低声道:“只怕已经晚了。”
含章心一沉,整个人从脚踏上弹了起来,绷直了立在一边,直勾勾看着赵昱,似乎连发丝都在发抖,赵昱无言以继,只能用目光坦然以对,他眸色极深沉,不像初遇时那好似一成不变的温善,此时便如两泓深潭水一般柔软包容,毫无一星棱角锐利。含章看了半晌,慢慢软了下来,是她强人所难了,袁信选了自己的阵营和道路,便已经注定了要承担的结果。
含章颓然垂下头,无力道:“是我失礼了。王爷请见谅。”
作者有话要说:卡了下,改了好多遍。
第七十三章心思无人知
赵昱眉头皱起,他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疏远的气氛,似乎两人之间无论说什么都已经显得多余,但今日事情实属突然,走到这一步非他所愿,但一时也想不出弥补之法,低头沉思间,眼角余光扫到床角边一样事物,不由微怔。
“哐当”,小六怀里抱着个小包袱,夹着一股凛冽寒风闪身进了屋,回头一眼看见赵昱竟在屋内,不免眼中闪过惊疑。
含章松开紧咬住的唇,问道:“外头如何了?”
小六去了这许久,不但把药煎好了抱回来,还顺带探听了一圈周围的动静,他吸了吸红通通的鼻子,道:“太医局的官兵都撤走了,旁边王爷别院中的也撤得差不多,只各个门口仍有人看守,不准人进出。”
那队人的目的本就是为了平王兄弟而来,如今见目标有了下落,自然不会在这地方多浪费人手。目前看来,这里已经安全了。
含章点头,又问赵昱:“不知王爷如今有何打算?”
赵昱拂衣起身,道:“只怕事情一时之间不得了结,还需搅扰几日了。”
含章并无异议,也未多问其他,只说:“也好。”
赵昱见她意兴阑珊,便告辞退回了密室内。墙又轻轻放下,了无痕迹。
小六撇撇嘴,把小包袱里抱着保温的药罐取出,把药小心滗到碗里,捧给含章。含章接过,一仰脖喝了,还碗时见小六额角密密一层细汗,便提起袖子给他擦净了。小六嘿嘿一笑,放好了碗,去整理屋内东西。
含章腿伤未愈,站立这些时候已经隐隐作痛,便坐回床头,抱着膝盖看小六在屋里忙碌,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压在心头不那么冰凉。
小六弯腰把甩在屋角的包袱皮拾了起来,却连带着骨碌碌滚出一个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个画了夔纹的精致小鼓,他随手包进了包袱里,继续收拾东西,含章闻声淡淡扫了两眼,敛了眉,又收回了视线。小六把东西都清理好,放回衣箱,但总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他疑惑着又翻检了一遍,见重要的东西都不曾少,只道是自己多想了,便关上箱子去干别的。
见小六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又拿了盆去屋檐下取炭,含章思绪微动,便从枕头下摸出那片干枯的穿心莲,开了箱子,打开包袱,把叶子和那夔纹鼓收在一起,之后抚平了痕迹,回了床上睡下,只从腰间摸了明月塞回枕下。
京城的局势果然如预料的一般,到了第二天就来了个大反转,黎明时候从城外进来一队人马,和南衙禁军合力,在皇宫前长宁街与叛军战了一场,叛军大败之后京城八门都被封锁,勤王之军分散和四逃的叛军展开巷斗,京城的百姓们住在天子脚下,养尊处优惯了,记忆中哪里经历过这样的事,全都紧闭门户,缩在家中,听得厮杀械斗之声就近在门外,浓浓的血腥味隔着门板传来,利刃刺入的声音清晰可闻,兵士们死亡前的惊惧尖叫如在耳边,似乎还有苟延残喘的人在临死前挣扎着抓挠自家门板,又或者有叛军慌不择路下破门而入进了邻家门,勤王之兵穷追不舍,双方就在隔壁院子砍杀起来,刀兵之声清脆入耳,间或夹杂着邻的惨叫,吓得人胆战心惊。
到了下午时候,声音渐渐安静下来,但各人仍是战战兢兢,在自家屋里却连大气都不敢出,就怕一不小心引祸上身。再过了一两个时辰,全城成了一片死寂,眼见太阳已经西斜,终于听到有人敲着锣走过街道,沙哑着嗓子高声通知,只说叛乱反贼已被平定,如今街市巷道已经清理,晚上仍要戒严,但各家不必再畏惧。
听了这话,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便有人大着胆子开了门,果然外头街道空无一人,连混战后的尸体也已被清走,只留地上墙面大片大片暗红的血迹,腥臭扑鼻,墙角门边散落着一两根残断手指或是小半边脑壳,一团黑色长发上还粘着灰白的脑浆,无声地诉说着这场乱局的惨烈。脸色惨白的百姓们只得忍着恐惧恶心,将残肢扫在一起点火烧了,又从井里提了水冲洗门前血迹。
百姓的命向来便如草芥般微不足道,却又有着春风吹又生的韧劲,叛军被镇压的第二天,茶馆酒楼就开张了几家,路边也有小贩试探着摆摊,只是还不敢大声吆喝。过了中午,眼见一切如常,便有更多的商铺开了门,百姓们陆续上街,彼此常交头接耳,低声密语交换着消息,若非众人眉梢眼角未消散的惊慌之色显得有些异样,京城仍是熙熙攘攘一如往日。
这场所谓的叛乱,终究也只有一夜而已,快得就像秋风扫过的树叶,摇曳一下就掉下枝头。刚刚开始就已结束,日后史工笔下,不知是多么可笑的一幕。
小六带了消息回来时,含章正靠在床头发呆,察觉有人进了门,慢慢抬起头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黑沉沉里泛着红,看不出一丝情绪。
小六被她的眼神看得心悸,犹豫地不敢进门,手有些不自觉地在身上搓了两下,眼睛躲躲闪闪四处乱看,像是在找什么人,这个时候,哪怕是有个不相干的人来打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