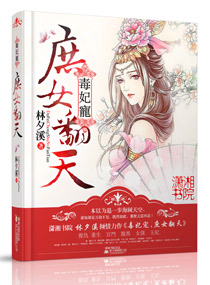公侯庶女-第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只手握住了她的手腕,虽然并没有用力气,但含章却不敢挣扎,程熙勉强睁开眼,摇了摇头,虚弱笑道:“已经没有用了。”
含章心如刀绞,眼中渐渐盈满泪水。程熙看着她的泪,笑了笑,又低低道:“我有两件事对不住你,第一件是窦叔的事,他兄长是明姨的故旧,不得已做下那些事,我知道你怀疑他,又不想窦叔有事,就将他迁走。第二件是我知道你想回边城,可我想留下你,所以才将你引到得月楼,让你察觉英王的秘密。谁知竟然碰到袁信,揭露了你的身份……”
他说得越多,气息起伏越快,背心伤口的血便越流越多,几乎要将他的血流干,他的生命也随着这血液流逝,程熙的脸越发惨白如纸,显出透明之色。含章看得心惊胆战,忙道:“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说了。”
“我想为妹妹报仇,就去利用公主,明姨养大了我,可我最后还是背叛了她,我还害得妹妹惨死。我想阻止这一切,偏偏什么都办不到,我就是一个如此自私又无能的人。沈含章……含章,你不要怪我……”程熙说着,手上摸索着摸到樱草的手握住,最后看了含章一眼,温柔一如当初,但这双眼睛慢慢失去了光泽,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深深的喟叹,终于停止了声息,胸口的起伏渐渐停止。
含章眼睁睁看着,待到他的身体再无一点生命的迹象,方才慢慢伸出手,将他不曾闭上的眼睛合拢,泪中带笑,道:“我好像还欠你一顿酒呢,你这样,叫我怎么还呢?”
呆坐良久,含章缓缓起身,收好明月,将桌上油灯取了,一步一步走出了这间小地牢。沿着狭窄的陡峭楼梯走上地面,才发现这是程家一间屋子的床下,屋外森森翠竹,犹自哗哗作响。屋里的家具东倒西歪,床也被掀翻,四周到处都是暗红血迹,不远处倒着一个人,身形魁梧,身上没有血迹,眼睛闭着,脸色却铁青狰狞,舌头外吐,颈上紧紧勒住一条绳索,是金掌柜的模样。
门外厅里歪着两个人,那位仆人程叔和樱兰,都已经气绝身亡。这间屋子里曾经发生过的什么,已经随着所有人的死亡而成为永远的秘密。含章默默看着,走到后面厨房取了所有的油和木炭来,又摊开屋角存折的用来做鼓的干燥牛皮,放上木炭浇上油,点燃了火。火苗很快腾起,慢慢点燃了房梁,含章一步步后退到屋外,眼中倒映的火苗越来越大,直到半间房子燃起,火势再无可阻挡,她才回身,拉开门走出院子,干燥有风的夜晚,熊熊的大火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但在这个夜晚,这并不显得特别,因为整座京城已经成为烈火炼狱。
远处皇城因为爆炸而引起的火不但没有熄灭,反而越演越烈,巨大的火舌腾空而起,仿佛要点燃天空低垂的黑云,滚滚浓烟蔓延开来,在整个京城上空形成一片薄雾,狄兵和盛军在往日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展开巷战,厮杀惨叫之声此起彼伏。
百姓们试图携家带口逃离此地,却遇上迎面而来的狄军,对方猩红着眼一刀劈下,无论男人或是女人,立刻身首异处,倒在街边,他们的细软金银被搜刮一空,襁褓中的孩子被狄人哈哈笑着挑在刀尖活活刺死,老人们走不动,缩在墙角苦苦哀求着,却也没能逃脱被虐杀的命运,最终横尸街头。鲜血染透了玉京城的大街小巷,比当初宁王夺位时惨烈百倍。狄军在做他们最喜欢的事,屠城。
程熙的住所在京城东北方,离被破的西门有很长一段距离,狄军还没有攻过来,只有寒风刮来凄厉的哀嚎和惨叫。她迷茫地走在路上,身边挤满惊慌失措的逃难百姓和官员们的车马,他们都是往北门而去,因为那里有盛军拼死打开的一个突围口,只有那里才有一条活路。
人流如潮水般越来越汹涌,推推搡搡,所有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都城破了,皇帝死了,国要亡了。人们哭喊着奔走逃命,不时有人被挤倒,尖利哭号,但立刻就被人群的嘈杂声响淹没,其他被吓坏了的人并没有停下脚步,踩在跌倒的人身上往前奔去,含章也几乎被挤倒,却被背后一个人牢牢扶助。她在一片推挤中勉力回过头,只见薛崇礼冲她笑了笑,带着她挤出人群,进了旁边一条无人问津的小巷。
巷子里散落着逃难人遗落的鞋子、衣服,甚至女人的簪环首饰,一片狼藉,薛崇礼紧紧握着含章的手腕,带着她穿过这些混乱,他再病弱也是男子,手上力度便如铁钳一般,将含章手腕牢牢锁住,她无可无不可,并没有挣扎。到了巷子里一座小门边,此时四处静寂无人,这所宅院也是门户大开,满地零落的杂物,含章在这里住过许久,看过几眼便认出这就是薛府的后门,皇帝虽然下旨夺爵,但由于时间仓促,薛家人还来不及搬出,这里依稀还是往日模样,只是油漆黯淡剥落,到处显着一股没有人气的荒凉,早不复当日的光鲜。含章冷眼看着这一切,当日那一幕幕悲喜剧仿佛才发生不久,薛崇礼一言不发,带着她穿过后宅,直往正房而去,偌大的府邸空无一人,一路上的房檐都挂着白布和白纸灯笼,在空荡荡的府邸里飘摇着,发出单调的咿呀声,含章记起薛家老夫人似乎刚过世不久,这样也好,省得受这番波折痛楚。
终于到了侯爷的正房,薛崇礼停下脚步,指着虚掩的房门道:“你进去吧,去看看他。”
他话里的悲痛难忍和压抑不住的哽咽声音已经说明了屋内是怎么样的情景,含章很想转身离去,毫不理踩这些,但最后她只是闭了闭眼,缓缓上前,伸手推开了门。
迎面便是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对面的墙上,原本挂着的书画对联早已被撕扯,散落在地,光秃秃的白墙上只有十六个鲜血写就的大字:国都既亡,帝死社稷,臣亦有罪,以死谢之。
鲜血淋漓,触目惊心。含章心头剧震,一颗心提到嗓子眼,她视线扫了房间一圈,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满地的鲜血和碎纸片,一个一个血洼往内室而去,含章忙顺着血迹走进,刚进门便一脚踩在大片血泊里,湿泞泞飞溅染红了衣摆,似乎还是热的,没有冷透,但她却毫无所觉,一双眼睛只盯着床上躺着的一人,那人本来爽朗清举的脸上满脸蜡色,死气沉沉,脖子上开了一条巨大的伤口,皮肉翻皱。这个在后宅里怯懦逃避了许多年的男人,却在城破关头选择了用生命为在朝者的错误谢罪,死得如此壮烈。
含章慢慢走近床边,居高临下看着他。薛崇礼慢慢走到她身后,道:“父亲生前,除了深感有愧于国,还念念不忘你。如今你能来看他一眼,他在天有灵,一定很欣慰。”
“是么?”含章唇边挤出一个冷淡的笑,却比哭还难看。薛侯爷念念不忘的有侯夫人,有薛崇礼、薛定琬、薛定琰,甚至还有他的兄弟和侄子侄女,当然,也会有一小块地方留给薛含章,只是这里面有多少是因为愧疚,又有多少是真真正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呢?
人死如灯灭,再追究这些微末小事也无意义。就如同含章已然冷却多年的左胸口,再不能被他暖热。她抬起头去看薛崇礼:“你留在这里做什么?”侯府的人必定是都去逃难了,薛崇礼出现在人群中,定是送他们出了城再回转。这样的时候逃出一个是一个,为何又回到这个冷冰冰的宅院里。
薛崇礼看着父亲,道:“为人子的,怎么能看着自己的父亲死后无立敛,就这样暴露在人前呢?”他俯□坐在床边,将薛侯爷背在背上,又对含章道,“若能平定狄乱,不妨让人去府中后花园的水池里看看,让我和父亲得以重见天日。”
含章大惊,一把抓住他的袖子:“世子,你……”她微张着嘴,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牢牢抓住他的袖子,另一只手取出腰上匕首,斩钉截铁道,“我带你出城!”
薛崇礼一笑,云淡风轻地摇了摇头,轻声道:“含章,你保重。”说罢不再看含章,只负着父亲起身,含章还要阻止,却见薛侯爷手臂因着惯性垂落,紧握的拳一松,掉出一个被血染透的纸团,落在含章脚边。
她拾起纸团打开,一眼便看到末尾署名处的三个字,沈灵霞。这封信何等眼熟,正是当初樱兰拿给自己看过的,生母沈灵霞的绝笔。她心一颤,忍不住看向沈侯爷,他在人生的最后,选择以死殉国时,身边还带着的,是被他辜负了的女人生前的绝笔,看着那个女人生命最后的无怨无悔,不知他心头是何感想。
含章握紧信,一直压抑着的情绪像是突然被蚁穴洞破而溃的堤坝,忍不住悲从中来,呜咽而出。
薛崇礼顿了顿步子,不曾回头,又向前坚定地迈出了房门。父子两人身形相近,容貌相似,就这样一个背着另一个一起缓缓走远。含章连忙起身,几步追到门前,扶着门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泪流满面。
作者有话要说:终于赶出来了,本来想在上一章说一下今天还有的,但又怕自己万一写不完岂不是又开空头支票?所以还是写完再发了。
第八十六章何去又何从
寒冷的风呼啸而过,卷起一片尘沙,灰头土脸的流民三三两两携家带口往南而去,他们已经跋涉了两天,虽然脚力不快,但此处离玉京已遥遥百里,狄族的阴影暂时减退,使得他们暂时有时间喘口气,平复一下像满弦一样紧绷的心绪。
玉京已经享受了近百年繁华,这样一个盛世都城居然就这么仓皇间毁于一旦,任谁都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城破得实在太突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玉京素来就是以城墙坚固著称,有些不如它高大的城池都能被围数月而仍然坚守,却不知为何这国都反而不如。
但亲眼所见的事实让人们无法自欺欺人,皇城里那犹如惊天重雷般的爆炸,还有那通天的烈火,都彻底焚尽了人们心目中的最后一丝幻想。皇帝已经自尽谢国的事犹如卷残云的风,迅速在流民中席卷而过,对于这样的君王,人们在悲壮的同时,更多的是茫然和绝望。一个国家,国都没了,君王没了,不就是亡国了么?即便有平王临阵即位的消息,但这对于人们崩溃消沉的心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但无论内心多么无望,命还在,家人还在,就得挣扎着活下去,死亡的阴影还在笼罩,没有人知道狄军会不会再南下,会不会就此占领整个盛朝版图,这在以前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连最不可能发生的都已经真切地发生了,还有什么是真的不可能的呢?他们不敢想,更不能想。于是只能逃避地麻木自己的思想,用最卑微的渴求,最渺茫的信念继续走下去。
可是上天似乎并没有垂怜这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在第二天夜晚,忽如其来的北风夹着春寒的雪,簌簌下了一夜,天寒地冻,附近村庄的人早闻风而逃了许多,只剩下少数走不动的老弱守在家园,食物短缺,流民们纵有金钱也换不到粮食,更何况他们匆匆离家,随身携带的钱财并不多,饥寒交迫下,又没有足够的地方避寒,只能砍了树木取暖,但即便是树木,对于人数众多的流民来说也显得稀少,这个夜晚,许多老人和孩子悄无声息倒在了路边,被白雪覆盖。
第三天清晨,初春的朝阳洒下温暖光辉,总算让人们千疮百孔的心稍稍得到一点抚慰,他们彼此扶持着,想要翻过眼前的山,到达下一座城。但也有很多人,身无分文,不被准许入城,他们被饥饿和寒冷所迫,找来锄头和菜刀,开始打劫要入城的富贵人们的车队,若说以前这些贵人们还是自己仰望和臣服的对象,那么现在是什么也顾不得了,那些可以避风雪的华丽马车,和那沉甸甸的辎重,无不是众人垂涎的目标,虽然有许多护卫提着刀剑守护,也阻挡不了被饥饿和寒冷折磨到走投无路而集结在一起的流民们。
当含章站在山腰远眺的时候,发现了不远处的山脚官道上一队正在被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民围攻的车队,这车队七八辆车,都是貌不惊人的普通车马,看上去并不是大富之家,却不知为何也被流民们看上,守卫的仆人们在拼死抵抗,车上的妇孺的尖叫啼哭凄厉可闻。
含章淡漠地看着,她看得出来这二十多个仆从中夹了五六个颇有武艺的人,应该是上过战场打过仗的战士,能得这等人相护的,非富即贵,绝不会如外表所展示的这么不起眼。而他们的战斗力也远胜于这些饥饿虚弱的流民,即便取胜只是迟早的事。她站了一会儿,便要转身往前去,却听得一片杂乱呐喊声由远及近,似有许多人正往这里而来。
含章循声望去,树林里闪动着许多人影,不多时,又一批集结的几十个流民将这车架重重包围,这百多人都绿着眼睛对着马车虎视眈眈,如此一来,力量天平顷刻便往流民一方倾斜,只怕这群车马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含章微微皱了眉,便听见被包围的人群里传来一个变声期少年愤怒的喊声:“敢动我嫂子和侄子,先从我尸体上过去!”
这声音好生熟悉,袁任?含章一愣,忙仔细看去,果然那些仆人都有几分眼熟,而从掀开的车帘惊恐往外看的半张小脸,依稀便是薛府里明眸纯真的六小姐薛定瑜。
这是薛府的车马。
真是孽缘,含章长长叹了口气,从山腰上疾步而下,她在山上修养将息了两日,体力比先时好了许多,此刻便将明月从腰间抽出,却不出鞘,只用银链为鞭,从人群中劈出一条路,闪躲腾挪间便到了袁任身边。
那倔强的少年提了一把长刀,带领众人迎敌,他正和一个流民头领模样的人拼杀,虽勇猛有力,但临战经验不足,几次进攻都被对方躲开回击,并且对方手上握的不只是什么宝刃,凌厉气势甚是逼人,袁任渐渐落于下风。
眼见那头领一剑就要劈向他腰腹,含章手中银链银色光芒闪过,已经缠上了他的脖子,她就势将匕首抵在他喉管处,沉声大喝:“都给我住手!”
场面突生变故,陡然急转,其余流民皆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被含章制住的流民头目满是脏污的脸上一双明亮尖利的眸子转了转,嘿嘿冷笑道:“别管这小娘们,她的匕首还没出鞘呢,怕是连刀都不敢握得,咱们把这些狗崽子们都宰了,把这些女人都抢回去,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