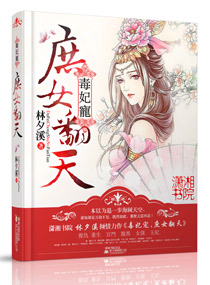公侯庶女-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青袍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从袖中取出一把玉骨折扇,点了点子疏的头,摇头晃脑道:“你这小子兵书看多了,成天脑子里胡想八端的,你口口声声说边关东狄人危险,但你可知道东狄盘踞边境已是两百年光景,从前朝至今从未断过,但也从不曾见他们有那本事入侵中原。我朝军力比前朝只强不弱,更有几员大将镇守边关。哪里需要你这般杞人忧天?”
子疏怒极反笑,努力睁大着快要撑不开的眼睛:“大将?!什么大将?沈老元帅已经年近七旬,陈友道是个痨病鬼,我哥哥被调回京师,代替他的那两个新将军有什么能耐玉京人谁不知道?”他说着已是清醒了些,满眼热泪,“若是年初那仗……若是那仗无碍,只怕如今东狄早已不成气候,绝不是我大盛对手。”
“你也知道是‘如果’,”说话的是一直没做声的最后一名男子,他侧身端坐,侧面的轮廓正好被含章看得一清二楚,几乎与薛侯爷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含章眯了眯眼,沉默地看着,薛侯爷嫡长子,薛府二爷薛崇礼手中揉捏着青瓷白玉杯,淡淡道,“袁任袁子疏,你既然是将门子弟,当知为将帅者当谨言慎行,一言既出,军令如山。更应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如今不过些不知哪里来的传闻,便让你这般失态,既不顾及自己酒量,喝多了便活像个市井愚夫般胡乱嚷嚷。幸而在座的都是你兄长的至交好友,若是这些话传出去只言片语,只怕要给你父兄惹来数不尽的麻烦。”
袁任通红的脸陡然失色,变得雪白,他似是有些惧怕薛崇礼,一句话也不敢分辨,呐呐地低了头,薛崇礼低咳了两声,随手将酒杯掷入池中:“本是傅襄好意,见你年纪大了也该出来交际交际,便带了你来喝酒。谁知你连这些小事应酬都做不好,我看你最近也别出门了,先去把酒给解了,再回去让你哥哥好好教教你,什么时候教好了再出门吧。”
袁任大气也不敢出,只得低头道:“是。”说完,便转身,由赶过来的仆从领了下去解酒。
见他避鼠猫儿一般惶惶不安地走了,紫衣傅襄和青袍朱嘉一个瞠目结舌,一个忍笑忍得满脸通红。待袁任身影都看不见了,朱嘉终于大笑出声,指着薛崇礼道:“果然那难缠的小子只有你能镇住。”
11
11、第十一章相见。。。
薛崇礼另取了一只冻石玲珑蕉叶浅口杯,倒了些菊花浸的黄酒,浅酌一口,道:“总是阿信这些年在家的时日少,没尽到做兄长的责。”
朱嘉摇了摇头,又问傅襄:“袁信到底为何没来?他三个月前成的亲,纵有多少甜言蜜语,这一百来天也该说完了吧,我好容易从南边回来,他也不出来聚聚陪我说话喝酒,真够没义气的。”说着又瞥了眼薛崇礼,继续怒其不争地摇头晃脑。
傅襄脸色一僵,小心偷看薛崇礼,欲言又止,朱嘉狐疑地顺着他目光看看薛崇礼,又看回傅襄,催道:“快说!要不然我现在就找上门去,横竖他的新娘子是崇礼的妹子,与咱们的妹子也没两样了。”
朱嘉向来有些胡闹,这话他说得出未必做不到,傅襄无奈,只好苦笑着道:“横竖你们早晚也会知道,不如我做了这个恶人吧,袁信那小子年初时就说过,卢将军和沈小将军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有同袍之情,既然他们两个在沙场上马革裹尸了,又没有亲人朋友戴孝烧纸,那自己就以兄弟之礼为两位同袍守孝一年。也算是全了那六年边关结下的情分。所以从年初至今,他一直闭门不出,在家守孝呢。”
“一年?!守孝?!”朱嘉目瞪口呆,“那小子三个月前刚成的亲,那岂不是?!”他小心翼翼将目光看向薛崇礼,若是守孝,那断不可能同房,这样一来,那新嫁过去三个月的薛家四娘子岂不仍是完璧之身?这可不是小事,却从也不见人提起,只怕连薛崇礼自己都不知道……
薛崇礼素来苍白少血色的脸仍是面色如常,只是唇色更白了些,他顿了一顿,一口将杯中酒饮尽,淡然道:“情义难两全,既如此,就叫袁信好生守着吧。但若是日后他亏待了我妹妹,便不要怪我不念旧日的友情……”
含章听得寡然无味,意兴阑珊地回身,却不妨一个没注意,踩到一枝掉落在地的月月桂枝,“咔嚓”一声低响。
“谁?!”一声厉喝。身后传来脚步声。
走已经来不及了,四周也无可藏身之处,含章索性将手笼进袖子里,好整以暇地等着。
果然,几个呼吸之后,便见紫影一闪,一个颀长身影突然出现在眼前。来人一身紫衣,面容俊美,只是此刻脸上风华尽敛,水墨般的双眼冷厉地睁大,狠狠瞪着含章:“你是谁?”含章微抬了头与他对视,却是静默不语。
傅襄心头闪过一丝惊异,只冷哼一声,一手牢牢攥了含章胳膊,推推搡搡往亭子而去。
薛崇礼与朱嘉已经动身走了过来,傅襄一把将含章推到他们面前:“崇礼兄,此女是何人,你可知道?”含章被他推得险些摔倒,她立稳身姿便先垂着眼眸抚平微乱的衣角鬓边,一派镇静,丝毫不慌。
薛崇礼上下打量了她几眼,见她衣着虽不华丽,料子却都是上好,显见得是位小姐,只怕是府里女眷的客人,便摇头道:“不是我府上之人。”
傅襄与他对视一眼,已是下了定论,虽然那月洞门与亭子隔得甚远,听不到什么,但此人鬼鬼祟祟,只怕有别的内幕,看来有些棘手。
他们的表情动静,含章都看在眼里,她轻叹了口气,上前一步对薛崇礼抱拳行礼:“见过二哥。我初来乍到,不知府中路径,一时迷路到此,还请二哥差人将我送回清樨斋。”
薛崇礼三人都吃了一惊,薛崇礼又仔细扫了她几眼,眉间微皱,沉吟道:“你就是含章?”
含章点了点头。
朱嘉一直冷眼旁观,听了这几句话,突然恍然大悟道:“你就是沈元帅的外孙女?薛家的二小姐?”
沈元帅散尽家财以为军饷,将唯一的外孙女送回昌安侯府,此事近日已在玉京传得沸沸扬扬,连带着昔日沈元帅之女与侯爷之间的旧事也被人重提,众人都饶有兴趣想看薛府的好戏,谁知他家却是一派安宁,让许多好事者大失所望,失望之余便调转枪头,大肆议论这位离家出走十四载的二小姐。
只是这传说中身有残疾的小姐自回京后从未出过府,所以众人也无缘得见其庐山真面目,只能越编越离谱,将她说成了既像无盐女一般奇丑无比又像墨团般黑的人物。朱嘉以前与人聊起时,还大笑不已:“若真是墨团般黑,那黑夜里若是不点灯岂不是连人都看不见了?”此时他忆起自己曾经的笑语,忍不住仔细看了看本尊的脸,皮肤确实不白,应是被太阳晒的,算不上黑,只有些蜂蜜般色泽,五官端正,眉目爽朗,却也算不得丑。
含章也知他在打量自己,大大方方看回去,口齿清楚回道:“家祖名讳确是沈三。”她说的是三,而不是山,民间百姓不识字,以讹传讹间都将沈元帅大名误以为是沈山,却不知这位传奇元帅原是孤儿出身,无父无母,只知道自己姓沈,行三,便以沈三之名参军,以沈三之名成名。
薛崇礼听得“家祖”二字,不由皱紧了眉,嘴唇抿成一条线。正这时,远远来了几个人,薛崇礼的婢女陌行领着正房里的许妈妈和樱草一路飞奔而来。到了跟前,许妈妈便慌忙秉道:“二少爷恕罪,今日清樨斋小聚,二小姐初初回家不晓得路径,也不知道二少爷在莲池这里宴客,她从桂树林迷路到了这里,若是冲撞了几位贵客,还请贵客们不要怪罪。”
樱草已是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慌忙站回含章身后。
薛崇礼眉头仍未松,盯着含章看,含章神情自若,淡淡垂眼。过了一会,薛崇礼道:“去吧。”
许妈妈如释重负,忙领着含章走了。三人看她远去的背影,果然一条腿行动不稳,步履略带蹒跚。
朱嘉“啪”一声打开扇子,故作姿态地摇了摇,惋惜道:“可惜呀可惜,沈元帅一世英杰,唯一一个嫡亲的外孙女却落得这般凄惨光景,真是可惜了……”他口里说着可惜,眼中却全是笑意,毫无一丝怜悯可惜之色。
薛崇礼闭口无声,只沉着眼看着,朱嘉不敢惹他,便用扇子敲了敲傅襄的肩膀:“诶,傅世子,你准备何时上门迎娶?”
傅襄面上冷色未褪尽,犹自沉思,忽听得此语,不由一愣:“迎娶?”
朱嘉忙不迭点头:“是呀,人家是侯府千金,外祖只怕会封公,这般女子被你大庭广众下抓着手臂推推搡搡,方才还连个歉也没道,难道就不该给个交代?”
傅襄彻底呆了。朱嘉好脾气地继续补充:“你不是最为崇敬沈元帅的么?如今娶他外孙女,也不算亏吧?横竖你家里那个河东狮子太强悍了,不如索性休掉,换一个好相处的,又和崇礼结亲,不是更好?”
朱嘉吊儿郎当地靠在傅襄肩膀上絮絮叨叨,真如几百只苍蝇般轰轰震耳,傅襄一听他提起自家老婆,一身气势顿消,就跟见了狼的兔子般蔫了,与方才冷厉判若两人。朱嘉仍是不肯放过他,还待继续絮叨,忽听得薛崇礼冷冷道:“既如此,我这便告诉李家弟妹去。”说完便转身回亭子。
朱嘉大惊,傅襄家那只母老虎若是知道此事,只怕吃不了兜着走的就该轮到自己了,他忙改口赔笑道:“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傅襄被他变脸般的表情变化给逗得发笑,摇摇头,跟着薛崇礼而去,朱嘉只好跟在后头不住解释。三人重回了亭子,仍旧喝酒闲聊不提。
含章跟在许妈妈身后,穿过游廊,绕过几座假山,又过了两道垂花门,直走了两刻钟光景,方到了一处院落。
许妈妈边引着含章进安泰院,边和颜悦色解释道:“这会儿已是饭点,老太君上午听说姑奶奶们和几位小姐都出来了,心里高兴,特地交代让都来安泰院用午饭,侯爷也说前几日因为姑娘身体不适,所以没出门,今日既然出了门,也该来老太君这里请安。老奴本是去知会小姐,谁知绕了个圈子费了些时辰,此刻里头只怕已经开始用饭了。”
含章只跟在她身后,应了个:“是。”许妈妈偷偷看了眼她的神态,只觉得竟如木塑泥捏一般看不出分毫变化,不由心头疑惑,这小姐到底是心思太深让人辨不出端倪,还是本就心思粗犷听不出自己话里意思?
从院门到内,走路也不过一会儿光景,许妈妈心头一分神,不觉已是到了院里正房前。
一个玫红坎肩的小丫头正侯在门边,见她们近前,便秉道:“二小姐来了。”说着,打起了万字不到头的锦绣门帘。
12
12、第十二章明斗。。。
紫檀木六扇金玉满堂的屏风依旧金碧辉煌地耀人眼,厅里变得安静许多,沉厚的瑞脑香,略显压抑的气氛,与刚入府那一天的情形分外相似,含章垂下眼,缓步绕过紫檀屏风。
还不曾拐弯,迎面来了个穿豆绿色葱黄镶边坎肩的丫头,她眉间微蹙,悄声问许妈妈:“老太太和小姐们都用完饭了,怎的才来?”她说着,眼角瞥了一眼含章。
许妈妈面露惊慌之色,为难道:“这……”她眼神一闪,也去看含章,试图用目光传递讯息,这里都用过饭了二小姐才到,岂不是不恭?若依着老太太的脾气,只怕又是一场是非。二小姐心里有数才好。
含章半垂了眸子,似乎并不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倒是樱草瞪大了滚圆的眼睛,害怕地往后缩了缩。
里头老太太还等着,青雀和许妈妈也没多停留,引着含章往内而行。樱草想了想,往墙根边站着,和正房里的婢女们站在一起。
厅里满满坐了一屋子人,都是女眷,各自坐在位上安静喝茶。老太君仍旧是正中大座上,身边空处各坐了个孙女,正是薛定瑜与薛定珞,见她进来,薛定瑜忙展颜一笑,薛定珞则畏缩缩地团了团身子。
两边太师椅上坐着侯夫人和崔夫人,两人面容平静,唇角带笑,好似上午那场为了木樨雅会而生的闲气纯属子虚乌有,其他小姐们都坐在锦墩上,薛定琬紧挨着坐在侯夫人身边,笑容满面,隐隐得意之色,薛定瑾却不在人群里。
有伶俐小丫头放好锦垫,含章沉默地给几位长辈磕了头。刚立直身子,老太君便发难了,她冷笑一声:“原来我竟不知你架子这般大,请你来这里用饭竟也如此不赏脸。”
含章垂手立在厅上,低着头一言不发,旁边都是略熟悉了些的姐妹,气氛倒比彼此陌生时尴尬了许多。侯夫人见此情形,忙打圆场,唤许妈妈道:“怎的才来,可是路上耽误了?”
许妈妈忙回道:“回老太君和夫人的话,二小姐在林子里迷了路,误走到了莲池那里,正好碰上二少爷,兄妹两个聊了几句,二少爷还特地吩咐让奴婢好生送小姐回来。”
侯夫人眼中闪过一道不明的情绪,点头笑道:“原来是遇上礼哥儿了,”她回身向老太君道,“老太君,他们兄妹重逢,高兴了些,一时多聊了几句,耽误了老太君屋里赐的饭。老太太就看在礼哥儿面上,不要责罚二丫头了。”
老太君听得面色稍霁,正待开口,忽听崔夫人扑哧一笑:“今日不是礼哥儿纳妾之喜么?听说要在莲花池塘那儿摆一桌酒请几个朋友,怎的,二丫头也去吃酒了?”
老太君沉下脸:“是今日?”
一直侍立在旁的大少奶奶接口笑道:“确实是今日,前儿个弟妹还来老太君这里告罪,说今日要去城外庙里求一个送子符给新姨娘,老太君忘了么?”
老太君年岁大了,又安享富贵,百事不用操心,这些儿孙事便记得不是那么清楚,经大少奶奶提醒,才确定了事实如此,她咂咂嘴,问侯夫人:“怎的又纳了一房?这都第几个了?”
这语气颇有些不赞同和责备之意,听得侯夫人心头一颤,这两年来每次说到这个话题,总会让老太君不痛快,再加上崔夫人在一边旁敲侧击明赞暗讽,更是会僵了气氛。但子嗣事大,自己总得为儿子考虑,所以,虽多少会受些责备,但薛崇礼屋里的妾室却是雷打不动每年都会多上一两个。今日已是侯夫人做主纳的第五个姨娘了。
薛定琬见母亲低了头、脸红耳赤。她虽性子直鲁,也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