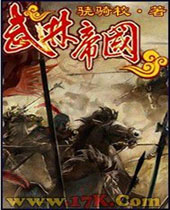��ɯ������-��1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ʲô��˼����������ЦЦ������������߲��̡���
�ҿ�������
������һ�κ�ϸ���������ã�û�жϡ���֪�������Ϲ������ǰ�Ҹ����������࣬�����������Ǵ��м�Ͽ��ģ������һ��Ǽ����ˡ�������ʱ������Щ��������Ц���X����Щ���졣��˵�Ǵ����������ӣ����������̨����ȥ�������Ժ�С�����ͱ����������
���������й��ˡ�������ô����˵��
��˭������
�������������
�Ҵ��Ź�����¥������С�����Ļ���������Щ��Ц���������й©��������ʵ����Ϊ��Ҳ��֪����
�ڶ��죬�����������������ؼң�����ʱ����ԼԼ������������˵�����ҰѶ����������ϣ�����һ��һŮ��������Ů����С���̣������˵������ܶ��죬����һʱ�벻������˭��
���ŵ���һɲ�ǣ��������˺���һͬ�ס�ˡ�ɳ���ϵ��Ǹ����ˣ���Ȼ����ҽ����С�������������ߡ�
����������ؿ���С����������������ǰ������ͷ����Щ���ң��۾����ģ������ӹ�Ƭ�̻��ҡ�
�꼾��ө���
����ƻ裬�ҿ�����һֻө��档��ľ��ס��ҽԺ�Ļ�������деİ�����������ĵط��Ź�â����������һ�������������䵽�˷��䡣
ľ����Ƚ���������֧�Ź��ȣ�һȳһ�ڵ������ǵ�ӨӨ�ģ�����ɫ����Ĺ⣬�浽�˽������ֲ�����ǰ���·����Ǵ���������
���ᷢ���ө��ө���һ�㶼���۵ģ�����ͨ�����ֹ������������������ԡ������Ǻ��۵ģ�ÿ������ֻ�֣ܳ�������������Сʱ����ө���ɳ���٣�����Ҳ�ǣ��dz��̣�ֻ�����쵽���������������ڣ����ʱ���ڣ�����ƴ�����⣬�����������ԣ���β��ֳ��Ȼ��������Ҳ��Ҳ��Ҳ����˵���ղ����ǿ�������ֻө��棬�������������ڣ��������ˡ������������ʽ�IJ���¥��ȥ��ľ��һ�������ظ����ҡ�
�����Ķ������ģ���
��ʮ��ʮ��ʮ���Ϊʲô�����������ң�Сʱ��ȫ�ġ�ʮ���Ϊʲô������Ȼ����³´�л������ĺ��������ȥ������Ȼ������ʵ��Ҳ�Dz��ࡣ��ľ�������ͻȻ��Щ���ۡ�
ľ���������ܲ��ã�������ϣ�����Ȳ���֮����������ѧ���꣬ר��������ȥ���ô����飬ѧУ��������ϵ���ˡ��������¸绪��һ���к����ķ��ӣ��������㣬����װ�ޣ�ר�ŵļ��������������ݶ��Ļ�¶̨������ߵļҸ������ɵö࣬��ֵһ·���������ֵ��ǧ���Ԫ��
��С褣���ɵ���㲻ȥ���Ƕ����ӳ���������ˡ������������ǰ���ҽ����Ѿ�û�з����ˣ����������ף�������ĸ�������ȴ�÷�꼾������Ȼ����ҵҵ����ƤΧ��������Ź���̬���������ӵ�������ǰҧ���гݵؽ�����������õ��ɫ�ں측�ڽ�ĺ�Ƥ�ϣ�����һ�ִ������·������ո�ҧ������ֻ���꣬����һֱ���ϸ��ҹ�˾�Ĺɷݣ�����������һ��Ҫ����������ɷݣ�������ʳ�ӡ�����
ľ���붨������ڴ��Ϸ���һ�������Ͼ������������������ˣ������飬̾������
�������������Ұ������˰ɡ����������ҡ�
��ҡҡͷ���������ֻ�����Ѫ����ľ��������ñ�ķ���찾���������Ǻ�����Ǽ��㣬ÿ������һ�����ϴ�����ľ����˼����û�ɽ�������������������Сʱ�ļ���������ȥ�ʹ�����Ѫ�����ɵ��ǣ�����¶¶�պø����һ��ȥ�μ�����湫˾��һ��չʾ�������ȹ���ϲ�С��Ū��һ�����ۣ��������þƾ���ʳ��Ϊ��������Ѫ���Ǹ�ʱ���ڶ����εδ����������Ū������ȹ��һ����⣬���ֻ�û���һ������ȹ�ӳ����������˵������üë����ľ���ܺ���ô׳��������ֻ�»����컭��ͼ�ޡ���¶¶�ʡ�ʲô�л���ͼ�������Ц���������ʹ�������¶¶���һ�£�û�����ң������ҵ��DZ���һֱ�쵽������
����û�п��������ˡ�����÷����������Ǽ��ꡣ
����ϵĸ���
��վ��ľ�㲡���Ĵ�ǰ������տն������·���Ļ������һ��δ֪�����磬��ϸ������ؼ�ȴ����ز�������˿�������������߱��Ƴ�һ�ž�������������ض��������������ص��˸С�������������Щ�����ķ����Ϲ���һ���ں����ķ��壬�����и�ð��һ������һ��ûһ��ط����۶۵Ľ�������
�и��������ҵĶ�����������𣬡��Ҳ�ϲ�����˶������š������Ҽ������̽���ȥ�����Ҳ�������㡱����һ����ǰ�������꾰������ʶ����������������ǰ�������ҵ��Ҽ�������Ǹ�����һ�������������������ͷ������������ĸо���
�������Ѿ����߹��ң��Լ������ֳ��ԡ�ʫ�������һ���ϲ���룬����������һ��ϸ�����������������ġ�Ҳ��������������һ��ϸ������������������Ȼ�����ĸ��ײ��뵽����ѩ���������Һ�˼�����š�
�����������������룬��ʲô�أ���
��û��û��ʲô����
�����Dz��ǣ�̸��̸��̸�����ˣ���ľ����һ�ֵ�Ƥ���ƻ���Ŀ�ⶢ���ң��⻬�Ķ�ͷ������̨�ƵĹ��������������ʱ��·����ֳ����������Կ��ҵ����¡������������ĵط��ǣ������������ҳ����κ����飬�����أ��ͱ����Ĭ�ϡ���Ҳ��������С��һ����ĸ��Ϊǿ�ƣ����¶��Ƕ�í��í�ļ�ͥ�ﳤ���йء�����һ�麣�࣬������ĵ���ᄀ����ȡ���������˿������ģ����ͱ��˺��ӵĶ���������ө���˲��ĻԻͣ������ҽ���ֹ����뺷����µ�ijЩ�ɰ�����˵�ҽ�����Ǹ�С������ʵ���Լ������С����С������������һ����Ը��
����˵�ҵ�ͷ����������һ�㣬����ԵñȽϳɣ����죿�����ʡ�ľ�������ڿ��ǿ�ʼ��С���ӡ���֪��������ʲô��
����ʲôʱ��ȥ���ô���ķС÷һ�ߺ��ż�����һ���ʣ����Ƶ������Ϻ����˵����飬�۾���ȧ�����������ת����������Щ���ģ�����ȥ�˼��ô��Ҳ�����Ҫ���ҹ�����ľ��ҵ��ӵ㹤���ôǹ����ϼҼ��ˣ����Ѿ���ӦС÷�����Ժ�ȥ���Ҹɻ
����֪����Ҳ��������Զ����ȥ����ľ��գգ�۾������Բ����һ��Ц���������ҡ�С÷�ѽ�ؼ���һ���ֺõ�Ц�ݣ�������ں�������������ľ��ĸ����֮ǰ�������ꡣ
�Ǹ�ɲ����������������ĸо���ľ��Ҳ����Ļ�Ϊ���ҽ������������У����ҵĽ��һֱ��֪����������������顣ӵ�и߹���������ĺô��ͻ����ǣ����������Ϊ��һЩ������翵Ķ��������ഺ���������С�
����������ҪǮ������Խ���Ҷ��٣���С÷��ȥ��ˮ����������ֻʣ���Һ�ľ�������ˡ�
�����ٶ��ɣ����ԡ���
�����硭������Ҫ��ʮ���أ���
ľ����۾���������Բ�ˣ��������ָ��ӵı��顣
������������ʮ��
�ҵ��ͷ��
�������㣬����������ʮ��
����š�����ʮ���Ҹ��������Ͽ�������Ϣ�������һ�¡�
���������𣿡���ûͷû�Ե��ʡ�
���߲ݵ�Ĭ��
�����������ҽ�����������Ȼû�У���
����Ǯ����
��Ҳû�У���
������Ƿ��Ƿ��Ƿ�˸���������ľ�����ͣ�ټ����ʣ�����˼ά�ܱ���ͷ����ģ�Ҳ����;�����ô���ɵġ�
л��л�أ���û�������Ƿ��μˣ����Ǵ��������ڲ����ϣ��ѡ����Ͼ�������ƨ�����棬������ȴ��ҵ����ġ����ҵ����ľ�������в�ã����˿��ǧ�������֪�Ӻ�˵��
¶¶��ʱ���ҼҺͽ������ζ��̸����Щ������������������Ҳ����������¶˭˭˭����۳����������һ���ٷ�������˭˭˭������ȥ����磬��������ʵ��������������ѡ��Һ�ľ��֮�䣬���ǿ���Ц�����������漰���飬�������Լ����ǶԷ���������������������ӡ����˵Ů���ǻ��������Dzݣ���ô���Һ�ľ��Ҳ�������ֺ��߲ݣ�����Ҳ�����������ش�̽���ǵ���˽�������߲ݺͺ��߲�֮�䣬�����½��Ĭ���ģ�����߶�ű˴˵��徲��
���ǣ�����������������������һ�죬�ҵĽ�㣬�����ز�����Ҫ���ܶ�Ǯȥ���������𣿡�
���㣬��㣬��㣿��ľ�����ͻȻ������ɫ������������������������������
�����Ǵ�ȷ�����
����ŷ����������������죬���ڴ�ͷ��������ˣ����㲻Ҫ�棬�����⣬���ֱȷ����ã��ò��ã���
����˵��������˰����������صػش�Ϊ�����ֽ�����ɵ��װɵ֮���̬����Щ������
ľ�㶢���ҿ���һ�ᣬ����������������ɫ�ָ��糣��������չ��һ���ƻ���Ц����������������������ָָ�����ߵ����ӣ�ʾ���Ұѻ�ƿŲ�������ᣬ�������ӹ�������
����ȻҪ���Ұ�����ƽ�����ǰ���������Ӯ��������Ӯ��
����������Ӯ��Ӯ�ң��ҲŻῼ�������Dz���Ҫ�裬��Ǯ���㣬����һ��������˵������Щ���������Լ��Ķ��䣬ľ��ı���ȴ������������������ʤ����
ľ����һ˫�����Ӳ�������֣���Ϊϲ�������г�ԽҰ������ӲӲ�ļ룬��ֱ���Ͷ�������֡��ҿ����Լ���ָ���������ף�ָ�ؽ�����ͨ�죬ľ�����Ҳһ·���°ͺ����˶�ͷ����һ�һ�μ��κ���ʽ�ľ����������˸��ˣ�ȫ��Ͷ�룬���ײ��ϡ�
��һ��ľ��Ӯ�ˣ��ڶ�����Ӯ�������֣��ұ����۾���ȫ���ע�������ϣ��������еļ���һ���˶���������ľ�����������Ǹ�ɲ�ǣ��ҵ���ǰ������������������ĬĬ�أ���Щ���˵ؿ����ҡ�
�����Ӻ��ҵ�������ʵʵ�ر�ľ�������ѹ�����ϡ���ά�����Ǹ����ƣ�һ�������ض����ҵ����Ц��
�����ȥ��ļ��ô�ɣ�����ͻȻ����һ�־����ŭ��
����Ȼ�����ҵ����Ц�������ڻ�ζ����ؾ��Լ���ʤ����
�Ҷ�ݺݵذ��ִ����������������������Ƕ�����Ц��
��������Ц���Ǹ�������Ц�����Ѿ�ת�����������ţ��������ߡ�
ľ���ס�ң����������ȣ��ȣ���������˼��ô��ҾͰ�Ǯ�������㡣��
������ʤ
��վס�����ع�ͷȥ��ľ���Ϸ��һ���ػ������������ƿ�ͨ���飬һ˫�۾������е�����ģ��촽��������һ���ÿ��Ļ��ȣ�������Ȼ����һ˿�ղŵĵ��⡣
������˵������Ǯ���ң������ʡ�
���϶��ص��ͷ��
���㡭������ô��Ǯ�𣿡�����ֵ��ҳ����ˡ�ľ�����Ȼ��Ǯ�����Ǿ�����֪�����Ĵ���֧�����Ƕ���ȥһ�������˻���֧ȡ��
���ֵ��ͷ��Ȼ��˵����������ã��ã��ø����ң���Ǯ������ȥ�ɣ���ʲô����
���ҽ������������飬��������Ѿ�ͣ�ˣ�ͥԺ��һƬʪ���������⣬���컺�������Ļ����һ�������ө����ˡ�
ľ��ĬĬ�ؿ����ң���Ҳͬ���ؿ�������˵��֮������ƽ���˺ܶࡣС÷��ϴ�õ�ˮ���������ϣ�ľ���ӹ���һ���Ұ��Ե��㽶���Լ�ץ��һС�������촽����ȥ����������
ľ����꼸�����ѣ��۾��������ת��Բ�ܣ����㣬���Ժ���ô���㣿��
���Ժ�
���磬�������������������ѹ���������������������С÷�������������裬��ҪǮ���������ƣ���������Ҫ��ѧ�����⣬����û��û�и�ĸ������ľ�������Щ���ʣ�����ȷ����������ͣס�ˣ��۾������һ�ֱ������侲������Щ���Ĺ⡣
���ң��ң�������ֻ�����Ż������¡�������ľ��ı����£��ҷ�����֪����������
ľ�㲻������ȥ�������ϵ�����������ĸ���ǶԽܳ������˵Ļ���ȴû�����ǵ����ͱ��ˣ��ղ�����ô˵��ֻ��Ϊ�������ҡ�
�����۹��������������ֹ���һ��Ц������ʵ�գ��ղţ�����ԣ�Ӯ��Ӯ�ҵģ���������һ�����ѣ�������˵�����Ӯ�ң�����䣬���˵ġ��㣬�㣬����������������
�Ҷ���ЦЦ��
���ɣ��ɲ������������æ��������Щ����
��ʲô����
��������һ�ȣ����Һ��ˣ�����Լ�������������ȥ�档��ľ����������̪��ˮ������㡱��������ü�����������
����ȷѡ�˸����ʵ�ʱ�����Ҫ�������ܾ�����ʱ���Ҳ���������һ�����ɵ����װɵ��
�������������о����֣�����ţ�̵����ԣ�����ǰ���桷���ٰ���ǰ�С��顷�ٰ�����������������ֳϵͳ�����Ķ���������������ʿ��һ���о�С��ԡ�20885����������ҽʦ�����˳���11��ĸ��ٵ��飬��Щ��ʳ�õ�����Ʒ��Ҫ������֬�̡�ȫ֬�̺����ң�������1012�����Է���ǰ���ٰ��������ص��ң��ϰ�����һ������ȥ�ܿ�ѧ�Ŀ���һ��һ�۵����š��������ʼȥһ�ҵ�̨�ʹ�����һ���С���ҽ��ʱ�䡱��ҹ������ר���Ŀ����һ�ν�Ŀ������ţ�̺�ǰ���ٰ��Ĺ�ϵ��
������𣿡��������ɳ���Ͻ���������Ů���أ�ţ�̶�Ů����û�и����ã������Ķ�ͷ��������Ƭ���ʣ������۾���ѹ��һ��ʪ��ĺ�������������������������˻ƹ�Ƭ�������ۡ�
��Ů�Բ������ҵ�ר�ⷶΧ�����ϰֻش𣬡���Ҫ�����������������
�����Ȼ������ش�ܲ����⣬���֣�����ô˵���±���Щţ���̺�����������������ѧ�������о��������й��Ĺ�������ʵ�����𣿻�����Ϊʲô����Щ����ʵ���Եģ��������ڲ�����Ȥ���
���������Ž���ʵ���Եģ��������ڵ�����̫���ˣ����ϰַ��¸��ӣ��������ڵĽ�Ŀ����Ҳ���˰ɣ���ֱ������ͳ��������������������
�Һͽ�������ǵ���Ŀ���̲�סһͬЦ���������������ϰֺܲ����ˣ����������������������ڴ�绰��ȥ���ϰֽ�������ȣ������ʡ���ҽ�������ġ���Լ��������ϰֽ��ⷿ��Ƶ�ʣ����˾��ʡ���ҽ������ÿ�ܷ��´�Լ���Σ����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