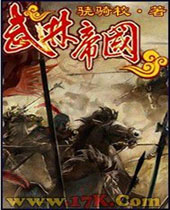温莎的树林-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天晚上,楼上那一家闹得翻天覆地,叮叮咚咚从家里一直吵到楼道,说是吵,其实大半是那家的胖女人在唱独角戏。
“住不下去了,住不下去了,这栋楼风水不好啊!”她在楼门口拉着一个居委大妈模样的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着,“上上下下的人家,没有一家太平的,可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她的嘴咧成个咬了一半的大饼,“我家那个死老头子………………”她的女高音飞上云霄又打个转回来,“我家那个死老头子在外面也有人哪!………………”
“唉,你什么意思啊,什么‘上上下下的人家,没有一家太平’,说话注意分寸!”五楼的英语老师推开窗子高声抗议,把一句“神经病”关进了窗户。
“现在啊,女宁像钞票一样越来越不值铜钱,年轻轻小姑娘来勾引一只死老头子,呸,不要面孔!”那个女人激情满怀地骂着。
“死老太婆,啥宁叫侬格腰身像通货一样越来越膨胀,小姑娘哪能啦,人家就是比侬好,比侬漂亮,比侬……有味道,哪能啦?”那个平时唯唯诺诺的秃顶男人站在对面林医生家的阳台上,气势汹汹地和老婆对骂起来。
真假
陈医生这回真的活腻了。
他站在我家阳台上宛如火山爆发般地对着自己的河马老婆叫骂之后,两栋楼间鸦雀无声,万籁俱寂,“连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大家像同时被武林高手点了穴,僵在那里,直愣愣地瞪着他。
五分钟后,陈太太歇斯底里坐在对面楼前地上要死要活,一堆人围在边上劝她;陈医生脸上方才的亢奋慢慢消退,慢慢转成一种介于拉稀和便秘之间的神情,老爸拍拍他的肩膀,陪着他回到我家客厅,“美美,倒茶,国栋,拿热毛巾来。”
我把热毛巾递给老爸,老爸将它敷在陈伯伯被他老婆用梳子在脸上砸出来的一大块淤血上。
姐姐端着新沏的黄山毛峰袅袅婷婷地走来,嘴巴往两边耳朵深深一咧,做了个鬼脸,伸起右手做了一个敬礼动作,“向您的觉醒,致敬!”陈伯伯的脸色越发尴尬,老爸瞪她一眼,“都回房间,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我做完作业出来喝水时,老爸和老陈伯伯并肩坐在客厅里,透过北面的窗子,天边还残留着一点紫红的火烧云,雾霭罩着城市的芸芸众生,远处一栋栋大楼闪起千家万户的灯火。
“老林,没想到,从你家看夜景这么美。”。
“是吗?”老爸回答。两个中年男人的背影,远远看去,居然让我联想起老片子“英雄本色”里李修贤给周润发疗伤那一段– 当然,小马哥的伤不是让老婆给打的。
“你有福气,家门和顺,夫唱妇随。你看你太太多好,温柔贤惠,出得厅堂,入得厨房……”陈伯伯感叹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爸说。
“没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我家那本经不仅难念,还会打人啊!”陈伯伯挠挠光头。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他讲了两句,嚷嚷起来,“小姑奶奶,老夫同你们远日有怨吗?……近日有仇吗?……啊,开玩笑?哎呀,……那么多楞头青,你们为什么偏偏要来拿我这个老头子开心呢?”他痛心疾首,“我告诉你们,谁再敢开这样的玩笑,我让她……我让她,我让她下回实习去太平间值夜班!”
“不像话,医学院那些学生……”陈医生嘟嘟囔囔地摇着头苦笑,“明知道我家里老婆厉害,隔三差五发莫名其妙的短信过来,还说是开玩笑!”陈医生上课时风格活泼,和学生打成一片,她们大约是听说他有惧内的名好,故意来开他玩笑。
这个时候老妈开门进来,楞了一下,“老陈怎么了?”
老妈听了陈伯伯的诉苦,展开一个慢条斯理的微笑,“真的是学生开玩笑啊?”
“当然,那几个学生都有男朋友的,怎么,弟妹,你不相信我?”
“我怎么敢不相信你,不过你们男人……”老妈淡淡地微笑着看了老爸一眼,“谁知道呢。”
“弟妹我对天发誓……”陈伯伯还没发完毒誓,老妈已经悠悠地换上拖鞋,转身往房间走去了。
请帮我想标题
陈主任在我家沙发上睡了一个星期,终于接到太太的电话,表示既往不咎,欢迎回家,母河马破天荒为自己的不明真相先开火道了歉,陈伯伯提着内装脏衣服破短裤的马夹袋再三感谢老爸收留之恩,临别赠言,给我的“小林,以后娶老婆,一定要好好选择,一失足成千古恨啊”,给姐姐的,“美美啊,我看你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以后嫁老公,嫁给他,就要善待他,要知道,男人很不容易的”,我和姐姐连连点头称是,一待关上门,不约而同捂着嘴哈哈大笑起来。
姐姐的手机响了,她一看号码,立刻换了一副脸色,正襟危坐,“是,Steve,‘苏南世家’的报纸和杂志插页广告已经全部做好,以环保,舒适和个性为主题,宣传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高贵起来’,对,对,方总已经全部看过,提了几点建议,不过总体非常满意,说下一期还给我们做……应该是后天……哪里哪里……谢谢Steve!”
她关上手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终于搞定了!”那个“苏南世家”是姐姐最近在做的大项目,平面设计由蔡雨霏的姨妈负责,看样子,做得很好。
“什么叫人才,这就叫人才,蓝印花布谁没见过啊,人家就是能够把它天衣无缝地结合到设计里面,又小资,又优雅,还印刷节约成本,由不得你们不服气吧……”她又在饭桌上教训手下。
“她到乌镇去了?”老妈问。
“嗯。就是为了这个设计。”
“什么时候?”
“……两个星期之前吧。”
“乌镇……听说很不错,什么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玩吧。”老妈提议。
“都是炒作出来的,那种地方,辛辛苦苦跑去了,看不了半个小时就腻了,”姐姐不以为然,“要去你们去,我不去。”
“对了姐,你觉得什么样的蛋糕好?”我问姐姐。在这个场景下,这个问题是有些突兀;但这个问题好像在任何场景下问都有些突兀。
“什么样的蛋糕好?”姐姐反问,“什么意思?”
“做……生日蛋糕……要别致一点,浪漫一点的。”我们家每个人过生日都由老妈操办,总是去附近的一家蛋糕店订一个大大的水果蛋糕,但姐姐说过那里的蛋糕越做越差了。
“你要给谁做生日?”她饶有兴趣。
“是有个同学,要给女朋友过生日 ……确切说,还不是女朋友,他想用这个蛋糕向她表白。”
“哦………………”她的嘴唇拢成一个圆圆的O型,眼珠朝天划了一圈回归原位,“要我说啊,最浪漫的,莫过于……叫你的同学自己做一个!想想看,”她的眼珠煜煜发光,“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温柔地抚摸着,洁白的面粉像云一样在指尖舒展开来,慢慢地,慢慢地,融合成一块……多好的创意啊……”
“你应该设计让两个人一起做蛋糕,男孩的手抓着女孩的手,揉啊揉,捏啊捏,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有些不耐烦了。
“对啊,多好的创意!”姐姐很激动,“果冻,you are so damn smart!”
“不敢当,”我懒洋洋地回答,“‘教父’第三季。”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爸放下报纸瞪了我们一眼。
我承诺过木鱼这个星期要打听清楚姐姐喜欢什么蛋糕,看来要失言了。
吃过晚饭,接到木鱼的短信,叫我马上到他家去。
第三节
走进木鱼的房间,我不由一愣,那张土洋结合的明朝古董大床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地上的一个床垫,电视机放在靠墙的床边,里面正播放着“教父”第三季。电视机和床垫之间放着一个黑色的皮箱。
木鱼打开皮箱,一堆亮晃晃的红纸扎眼而来。我看着那一叠叠整整齐齐码好的钱,足足有半分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有生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钱。木鱼的庄重神情告诉我,这笔钱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小数。
“你……哪儿来的?”问出这个问题时,我突然明白了答案– 他一定把那张床卖掉了。
“我把它卖,卖,卖了二,二十八万。”木鱼的眼角划过一个有些狡猾的微笑。
“那你爸回来……”
“他一时不,不会回来,”木鱼抹一下额头,“他现,现,现在心思都在那,那个女人身上。”木鱼爸爸的小老婆在温哥华怀孕待产,等到年底,木鱼就要有个小他很多的弟弟或者妹妹了。他爸爸和二奶住在温哥华西区一栋别墅里,他老妈住在一栋更加豪华的别墅,天天打电话去用最恶毒的话咒骂那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小孩。
“不,不要紧,”木鱼不紧不慢地分析,“如,如果是个男孩,我爸他高,高,高兴还来不及,根,根本不会有心思来管我,如,如果是个女孩,那我,我爸他更,更加会觉得我重要,也不会来管……”
木鱼的父亲和许多中年发迹的大款一样,年轻时由于生活压力错过了风花雪月的机会,加上几乎由父母包办当了人家的倒插门女婿,有了钱之后,对女人的兴趣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十几年里招惹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口味由浓到淡,眼界由低到高,浓浓淡淡,高高低低,最终还是只剩这么一个,从二十岁开始,断断续续跟了他十年,并不特别漂亮,也没念过多少书,本来在一家洗脚城上班,认识了木鱼的父亲之后就一门心思跟着他,最大的优点是听话,不吵着结婚,只有一个心愿,想生个孩子。
木鱼父子之间的坦诚让人感到难以置信,去年木鱼一满十八岁,他老爸立刻带着他频繁出入声色犬马的场所,理由是“是个男人,迟早总要过女人这一关”,此次二奶生孩子,也事先征求过木鱼的意见,而木鱼的回答叫他老子刮目相看明白了什么叫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你可,可以离开她,或者让她,她走,可既,既然你们决定在一起,那么,就,就,就不该剥夺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基,基本权利”。
儿子这句话让老男人几乎热泪盈眶,义无反顾地很快就让二奶怀了孕。当然这些事情,他的母亲都蒙在鼓里。
“你,你,你爸爸和你谈,谈这些吗?”
我摇摇头。我们家没有类似的谈资,有点遗憾,也不失为幸运。老爸老妈的为人处世让人觉得方方正正,没有什么不可示人的。
第四节
“那……你,不担心?”我忍不住问,“我是说,你爸爸又有了一个孩子,将来和你抢财产?”
木鱼沉吟一下,嘴角慢慢展开微笑,轻轻地摇了摇头,“那,那个小孩,毕,毕竟比我小,小十九岁,等,等,等到他长大,”他拿起桌上一罐百威倒进嘴里,抹掉唇边的泡沫,“我应该早就接了我爸的生意,当然,我不会亏待他。我不会和他争,但属于我的也不会放弃。”最后一句话他没有口吃,讲得清清楚楚,掷地有声。
木鱼这个人,有时候显得很单纯,有时候又出人意料地显得十分世故;他的世故,像一口味道醇厚的摩卡冰淇淋蛋糕,虽然冷,但绝不让人讨厌。这个时候,电视里面Andy Garcia骑在马上,干净利落地一枪干掉了仇人,我看着木鱼眼睛里坚定而漠然的神情,恍惚间,真的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万分荣幸地刚和几十年后胡润富豪榜上说话不太利索的某一位进行了一席谈话。
后来,姐姐问过我,“你凭什么觉得他会适合我,我会适合他?”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她,反问,“你不觉得他本质上和你有点像吗?”
木鱼说,他想来想去,最终,还是要去国外的,打算念工商管理,不仅是为了让他父母高兴,更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否则,我拿,拿,拿什么和别人竞争。”“人家”,指的大概是他父亲二奶的孩子。
“那我姐姐呢?”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我总是……等着她的。”
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突然发现,木鱼是一个思想理智而会善待女人的人,这样的男人,可遇而不可求。是的,虽然姐姐总说你们这些还没跳出puberty的小屁孩也TM配自称男人,但我们环顾周围那些大我们十岁二十岁甚至更多的男人,并没有觉得他们特别高明。
那天,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电光一闪,非但觉得木鱼和姐姐很合适,甚至开始有些恐慌,姐姐的脾气我知道,倔犟起来九头牛也拉不转,假如她不愿意,或者木鱼改变了心意,或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错过了,实在很遗憾。
“我姐姐说喜欢男孩子自己做蛋糕。”我有些为难地告诉木鱼。
他再一次展开神秘而有些得色的微笑,“来。”
我随他走进厨房,巨大的花岗岩流理台上摊开着几本装帧豪华的书,仔细看,都是菜谱,翻到教做蛋糕的章节,旁边的玻璃大碗里盛着一堆稀糊状的面粉。
“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那家伙恬不知耻地问。
就在木鱼继续努力学做蛋糕的那个晚上,我喝完了三杯水,终于下定决心,去和老爸谈谈。
客厅的电视里放着“士兵突击”,那是老爸的最爱,他却一个人坐在北边的阳台上看着夜色默默抽烟。老爸很少抽烟,基本都是趁妈妈和姐姐不在的时候偶尔过过瘾,在她们回家之前迅速掐掉烟头刷牙洗脸消灭所有罪证。
“爸。”我走过去,关上阳台门,叫了一声,老爸居然肩膀一抖,一截烟灰掉落在手指上,他的肩膀又一抖,我也忍不住跟着抖了一下。
第五节
“什么事?”老爸把手上的烟灰隔过阳台抖落下去,声音恢复了平静。
我鼓起勇气和他谈起给雨霏换肾的事情,“钱没有问题。”
老爸有些疑问地看看我。
“木鱼,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到我们家来,来吃过一次饭的,他愿意借钱。”
“借钱?借多少?”
“二十万,哦,更多也可以。”
“借给谁?”
“借给我。”
老爸的眼光透过眼镜片激光一般直射过来,久久地凝聚在我身上,经过仿佛有半个世纪那么久,几乎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烤熟了才离开,又投向远处的万家灯火。灯影里,我听见他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你喜欢那个女孩子,是吗?”老爸问,语调十分温和。我以为他会质问一番,但他的口气像是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