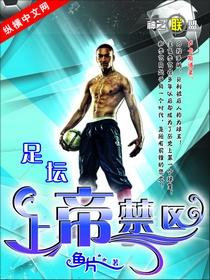紫灯区-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摆着酒柜!你活得舒舒服服、逍遥自在。你有城堡、农庄、树林。你今天去山野行猎,明天去巴黎旅游……”
他低着头,不说话。
我继续说:“可我呢?就为了你看我一眼,朝我一笑,就为了听你说一声谢谢,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什么都可以出卖。可以用双手去做工,可以沿街乞讨!你很清楚,要不是你,我的生活本来会很幸福!又有谁逼迫你来和我好?过去,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就是刚才,你还这样说……你刚才吻了我的手,现在还是热乎乎的。喏,就是在这里,在地毯上,你跪在我脚下,发誓永远爱我。两年之中,你让我做着一个最美丽、最温馨的梦……你还记得吧?我们出走的计划?哦,还有信,你那封信,把我的心都撕碎了!可现在,我又来见你,来见一个富有、幸福、自由自在的人,求你给予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的帮助,同时带来我满腔的爱情,却被你一口拒绝,因为这要让你破费三千法郎!”
“我没有!”他的声音颤抖着回答,眼泪充满了眼眶。
我本该摇摇欲坠地冲出门去,却被他失误的表演弄懵了,只能呆呆地望着他——他说最后一句台词时本应是冷冰冰的,却颤抖得流下了眼泪。
他怎么会演错呢!
他的泪像一剂迷药,使我剧烈地颤抖起来,紧接着就泪如泉涌。我望着他,感觉着从他的泪眼发出的、迷漫了整个舞台的暖流。那暖流终于窒息了我,一下子倒在了舞台上。依稀听到了人山人海的观众里爆发出剧烈长久的掌声。掌声使我一下子清醒起来,意识到自己也演错了,维凯的本子里并没有晕倒的情节设计。
大幕拉上之后,几个人把我扶起来,搀到后台。我头晕目眩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紧闭着眼睛。维凯赶忙打开一瓶矿泉水,送到我嘴边。我喝了几口之后,感觉好了一些。
人群散去后,维凯的目光变得深不可测。
我垂下眼睛,哽咽着说:“你怎么失误了?怎么哭了?”
他似乎在逃避着什么,艰难地说:“别问了,已经演完了。”
“告诉我!”
“也许真情只在戏里。尽管演绎的是别人的爱情,使我动心的却是你!”
我的泪突然就像决堤的江河奔涌不止。
他很快收敛了情绪,淡漠地说:“千万不要被我感动。戏已经结束,什么都没有了。”
没等我擦干眼泪,“大胡子”却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他并不了解我和维凯之间的恩怨,当然也不了解我难言的伤痛,顾自狂乱地说:“紫蝶,你天生就是块演戏的料!上帝眼睛瞎了?到现在才让维凯发现你!看吧,这次你会轰动本城的,会出大名的!”
“大胡子”又激动地转过脸去,对维凯说:“我看下个片子就叫紫蝶演主角!娜娜是个俗胚,观众不会接受的!相信我,维凯!”
维凯沉思了一会儿说:“大胡子,先别忙,容我好好考虑一段时间。”
我不容置疑地说:“不必考虑,我这一生只会演这一场戏!”
“大胡子”急了:“没那个道理。相信你能演好任何角色!维凯让我担任那部新片的副导演,我有话语权!”
我再次说:“我不会再演了!”
第二天,本城的各大媒体开始出现关于春季艺术节的热烈报道。我和维凯演出的《包法利夫人》片段竟真的成了媒体的焦点。其中一家大报的一个记者竟看出了我晕倒在台上是情感过于投入所致,并对之大加褒扬。
紧接着,不少热心人打来电话问候我的身体是否恢复,为什么会那么投入地演戏,以前是做什么的,现在在哪里工作……甚至还有人问及我的个人隐私。舒鸣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从美国发来E…mail,委婉地警告我,不要活得那么张扬。
从此,我把家里的电话线暂时拔掉了。我真怕还会有什么奇怪的电话打过来,把事情闹大了。
一个星期之后,维凯打响了我的手机,约我出去吃晚饭。
“我对你还有什么用处吗?”我说。
“为什么总像小女孩一样任性?”他意味深长地说。
他的话使我浑身发冷,牙齿开始失控地打颤。
他非常敏感,马上温和地说:“你冷吗?是不是穿少了衣服?”
我的眼睛热了,喉头也哽住了。
“出来吧,我带你去好好吃一顿。”
他带我去了一家粤菜餐厅。面对着一桌子的海鲜,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两个人只是慢慢地喝着啤酒,彼此对望着。
我忍不住一直压抑在心底的委屈,狠狠地说:“你冷血!”
“对于女人,我早已没有热血了,没办法,请你理解我。”
“但你为我流过泪!”
“我再说一遍,那是在舞台上!”
我直觉得心如刀绞,咬着嘴唇,不再言语。
他抽了几口烟,又沉重地说:“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的心曾透明得没有一丝瑕疵,简直就是为艺术和爱情而生的。但是,半辈子过去了,这世界给我的只有累累伤痕。做导演之前,我是个穷小子,没有女人正眼看我。做导演后,漂亮女人像成群的苍蝇一样围着我,争相献身,为的是角色。那些下贱到骨子里的女人们教坏了我、毁了我。既然她们一个接一个毫无廉耻地送上门,我何不拿着鞭子把她们当牲畜驱赶?我和任何女人都只有一夜,和你是两夜,足以证明你在我心中的分量了。”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疯狂地说:“别再说了!我讨厌你!”
“那是对付下贱女人的办法,我绝对不会主动招惹规矩女人。”
“我也是下贱女人吗?”
“你既然不傻,一定看得出我喜欢你,哪怕只有一闪念。但你更应该清楚,我不可能和任何女人天长日久。”
我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说:“所以,在你不想结束的时候,我必须结束。”
我拿起皮包,站起来说:“叫我出来吃饭,就是为了侮辱我?”
“不!想和你建立长久伙伴关系,我们做爱的感觉确实不错。你丈夫不在家,我是单身,都需要滋润。”
如果第一次喝茶时他说这些话,我也许一拍即合,但现在听起来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我顿时感到羞愤难当,低声喊道:“别做梦了!”
他按灭烟蒂,正色说:“还有一件正经事,希望你能答应我,出演那个新片的女主角。”
我立刻想到了娜娜,心中升起深刻的厌恶。如果我是个狭隘的女人,即便纯粹是为了和娜娜赌口气,也要接下角色。但是,向我提出要求的人是维凯,操纵角色的导演也是维凯!我不能重蹈覆辙,再次做他手中的木偶。
我决绝地说:“我不会再演戏。”
“你想清楚了,那可是一部电影!一部有影响力的电影!”
“不,我已经说过了。”
“娜娜确实不适合那个角色。并且,那部片子的男主角不是我。”
“哼!”
我站起身,抛下仍在喋喋不休的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餐厅。
一个月后,关于艺术节的事情彻底平息下来。世界是势利的,人们的遗忘能力历来比记忆能力要强得多。
日子在慢慢流过,仿佛为了让我疗伤,格外放慢了速度。
第二部分 什么都可以出卖第13节 我三十一岁的生日
我三十一岁的生日来临了。百合刚好出差在外地,我一个人在家里伤感地度过了一天。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对我表示祝福。他们或者从没记住过我的生日,譬如舒鸣;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我表示祝福的资格,譬如我的初恋情人慕┱堋…
谁来祝福我?谁能来抚抚我的肩头?我们天生就要受到伤害吗?我们这些做女人的人!
我拿出化妆品,打扮起来。在嘴唇上搽了亮色的口红,那是今季最流行的色彩。我得用时髦掩盖年龄,不能在小宝面前有一丝懈怠。我没有忘记带上那包花花绿绿的保险套,那是属于我和他的象征。我要还给他。关系已经结束,我不想再看到那些乌七八糟的提示。
一出门,才意识到外面在下雨,但我没有折回去拿伞,也没叫出租车。我有一种别样的欲望,想造成一种效果,要小宝看见一个湿漉漉的我。很久没有这种自虐的表现欲了,也很久不愿意制造那么浓重的浪漫了。
缓缓地走在雨里,我回想着自己的情感经历。从初恋的十六岁到三十岁生日之前,我只经历过慕哲和舒鸣两个男人。他们一个担负了我的初恋,一个担负了我的婚姻。前者痛苦,后者平淡。三十岁那年,我经历了小宝和维凯。对于我的婚姻来说,他们两个的性质和意义是等同的。但是对于一个纯粹的女人来说,他们又是截然不同的男人。小宝开启了我欲望的闸门,维凯承载了我一次短命的爱情。我不能肯定明天还有什么发生,但可以肯定维凯绝对不会是我最后的男人。
雨中的行人除了我之外,一律行色匆匆,没有一个的脸上不是烦躁、疲倦和无奈。看着他们的脸,再想着虚无缥缈的爱情时,心头不禁涌起无尽的惆怅。在杂乱无章的大街上,爱情显得奢侈而脆弱。大街上的行走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为生计而奔波之类,他们向世界展示的是疲倦的外壳。那样的一张张脸,很苦。
来到小宝的服装专卖店里,天色暗了下来,街上已经灯火点点。我站在店里打着哆嗦,像我期待的效果那样,被雨淋得湿透,浑身直往下滴水。
因为下雨,店里空荡荡的没有客人。消瘦的小宝蜷缩在一张椅子里听音乐。他看见我后,赶忙把耳塞拔掉,关切地迎上来,摸着我的衣服,疑惑地说:“怎么回事?淋得这么湿?”
我怔怔地望着小宝,眼睛微微发热。百合说得没错,他瘦了很多,鲜活的美已不复存在,像一棵树正在被风干。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哽咽着说。
“难看了是吗?当初我要是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喜欢?”
“富婆的一次骗局就可以把你折磨成这样?”
“那只是事情本身。仅仅那件事,不会给我这么大的打击。”
“还有什么呢?”
他沉默了一阵,摇了摇头。
我们都不再说话,只是哀伤地看着彼此。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见面了,他的目光有些陌生。他可能会以为我是来找他消费的,我似乎没有第二个来找他的合适理由。
“今天来只是想看看你。”我忙解释。
他有些窘,接着,仍然职业化地笑着说:“你随时可以找我。”
“不,我不可能经常找你,做不到。”
“是的,没有女人会把真心掏给我这样的男人。你是个好女人,把我当人看。我是什么?是鸭!”他说话时神色凄凉。
我浑身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拉着我走进店里的一个虚掩的小门,那是一个小小的休息间。他拿出一件厚T恤和一条长裤让我换上。我被包裹在他的衣服里,只觉得周身发出奇异的热。那是一个做鸭的男人给客人的温暖——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他为我拿来一片纸巾。我轻轻地揩了揩脸,心情开始舒爽了些,同时,理智也开始恢复。我突然觉得不该这么夸张地来找他,我和他的关系经不起任何推敲,一切苛求都显得可笑。
他让我坐在沙发上,倒了一杯热水。关切地说:“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呢?”
“我还死不了。”
“可身体是你自己的啊。”
“对不起,也许我不应该来找你,没有理由。”
“别那么说。不要把我们的关系看得那么绝望。也┬怼…我们可以相互抚慰。”
“我们?”
“当然。因为我们都是游魂。”
“但我们不能相互依靠!”我激动地说。
“能相互抚慰,就足够了。”
“人为什么要长一颗心?我真羡慕那些没心的人。我就不能像给你钱开店的那个富婆一样,没心肝地用钱满足自己的需要。”
他点上一支烟,沉重地说:“其实,这世界上有许多人比你更悲哀。譬如我。”
他消瘦的面孔和深不见底的眼睛刺痛着我。我理解他,他才二十出头,是个有心的男人,一生都抹不去可怕的创伤。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后说:“理解我说的话吗?”
“也许吧。”
“理解,也只能是一部分。你还没有看清真正的我,也不希望你看清。”
“你还有什么?”我疑惑地说。
“有时什么都了解才是残酷的。让你看清我,只会把你吓跑!”
“你在说什么?告诉我!”我断定他心里藏匿着某种不可告人的隐衷。
他紧绷着嘴唇,不再说话。
我陡然感到非常无趣。为什么要追问他的隐秘呢?他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该走了。
外面的雨已经下得铺天盖地。我从皮包里拿出那些花花绿绿的保险套,递给他说:“这个还给你。”
他接过那包保险套,吃惊地说:“我不是交代你要用这个吗?你没有用?”
“和你断了之后,我只糊里糊涂地和一个男人做过两次!”
他哀伤地低下了头。
我呆望着他,憔悴的脸渐渐虚化。
他揉搓着那包保险套,猛地抱住我说:“我们可以再用掉一个。”
“不!”
“我,我不要钱!”他火一般地说。
“这东西早失效了。”
“那就不用它!”他的声音微微抖着。
“记住,我从没嫌过你。”
“那就让我们无拘无束地贴近一回吧!”
我拒绝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