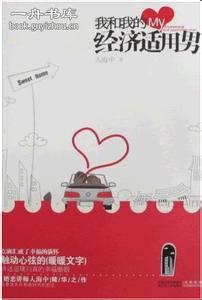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秦晖-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秦晖
第84期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有坐火车经验的人都知道,一列火车从一个轨道转到另一个轨道非常简单,有一个动作叫板道岔,但是一个社会列车,它要从一个轨道到另外一个轨道就非常困难,那叫做转轨,今天主持人阿忆就给大家请来了清华人文社学学院的秦晖教授,由他给我们带来一场讲演,这个讲演的名字叫〃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现在秦教授就坐在我的左侧,请大家鼓掌欢迎。
主持人:谢谢您。
秦 晖: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认识秦教授是在一次一个朋友请客,这个朋友非常有名,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叫蒯大富,他请客是每年的五月初,就是咱们校庆的时候。请秦先生之前,我还有一点特别奇怪,我经常看到有一位叫秦晖先生写经济史,还看到一位秦晖先生写教育,还有一位秦晖先生写的是农学,我就不知道怎么咱们国家秦晖先生一下子那么多,后来一问秦老师才知道,那是一个人,您怎么涉猎这么广啊?
秦 晖:惭愧惭愧,这也可能就是学无专长,所以喜欢乱发言吧。
主持人:您别老那么谦虚。
秦 晖:不过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说说也无妨,只是大家别拿我,别拿谁轻易的当个权威,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是讲话难免片面的,不过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思想史的进步就是由许许多多的片面的深刻而构成的,只要每一种片面都可以畅所欲言,在各种思想的交流,在不断地切磋之中,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智慧就会得到一种积累。
主持人:片面的深刻构成了我们的思想史,多么掷地有声啊,鼓掌!好,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履历。秦晖先生,1953年生人,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我要说错了的话,您可以及时纠正我。读首届研究生是在兰州大学。方向是土地制度与农民战争史,这很奇怪啊。关注的时代是在明清,明清的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八十年代后期,转向经济史,有一个括弧,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1992年任教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4年是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哎呀,我发现您研究的领域很多,您的职业跳动也是很怪的。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和广义农民学,越说我越听不懂。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像费孝通同志那样,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农民学?原来没有吗?要为它临时建立吗?
秦 晖:应该说我并没有这么说过,但是有些人是这么说的,叫做《农民学丛书》的这些书,我大概是头一套吧,但是在这套书中,本身我对农民学的源流就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
主持人:咱们现在就闲话少说,马上归入正题,我们的正题是〃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有请秦老师。
秦 晖:谢谢大家。这个经济转轨,具体地说,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就它的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很久,像六十年代的苏联的利别尔曼建议以后,在苏联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但是大规模的转轨应该还是我们通常说的所谓的剧变以后,几乎所有的前计划经济国家都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应该说提早了十年,中国的1978年就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进程。那么到现在为止,不管是东欧还是中国,都已经是十几、二十几年的历史了。东欧系统的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和亚洲的这几个国家相比,像中国、越南这些又构成了一个比较的单元。那么,可能人们更关注的是后者,因为欧洲的这十几个国家,尽管有的是所谓渐进的,有的是所谓激进的,有的是所谓左派执政的,有的是所谓右派执政的,但是,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都经历了经济的滑坡过程,而中国,亚洲的一些国家就没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成了一个转轨经济学讨论的核心。
大家知道,转轨经济学到现在,前几年在国际上是以古典自由主义的学派,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主流,那么到了后几年,就是以新凯恩斯主义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像斯蒂格利茨这些人成为主流,一方面,大家知道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战是〃古已有之〃了,一方面强调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强调国家调控的必要性。那么,双方都以这个来对东欧和中国,对很多国家的经济转轨现实作出自己的一些判断。但是我认为,这种争论是在欧洲经济发展的框架下进行的,那么在欧洲经济发展的框架下,所谓的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自由放任和国家调控的这种二元争论,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是不太适合原样的移到转轨经济国家的。
那么,谈论到转轨经济国家,我想,在我时间有限的演讲中,指出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很多人以前注意得不够的。
第一,就是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好像有一个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二元划分,而没有注意到,被他们称之为计划经济的那些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很多区别。而且尤其是亚洲类型和欧洲类型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倒是像崔之元先生他们非常之捧,非常强调鞍钢宪法,崔之元先生对鞍钢宪法的评价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而且可以说是有针锋相对的不同。但是,他看到了这两者的区别,我觉得还是很对的。鞍钢宪法的对立面就是我们文革的时候批得很多的所谓的马钢宪法,也就是说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整整那一套管理企业运作的制度。
大家知道,同样是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和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当然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流行过所谓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做一些道义上的判断,就是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善,资本主义是一种恶,基本上要讲的道理就是这个。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作为计划经济,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基本上没有涉及的。真正涉及到所谓计划最优化问题的,是以所谓最优化模型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而数理经济学在苏联得到了非常高度的发展,大家知道,前东欧国家,唯一的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坎托洛维奇就是搞这个的。而且,苏联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学的主流已经是数理经济学,而不是计划(政治)经济学。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仅仅从形式效率而言,那么这种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你说它的效率是高还是低,这的确是很难说的,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讲的所谓效率是指物质生产的投入产出系数,而不是指整个社会的效用增益,也就是说福利增益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计划经济,甚至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可以做到每一个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既不过剩,也无不足,所有的经济参数都通过线性规划,通过运筹学,达到所谓的最优。
这种经济,如果说有缺陷的话,主要的缺陷不在于没有效率,而在于极不人道,因为这种经济的构思基本上是把人当做一些机器来看待的。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这个经济它可以给两千个人生产出两千双鞋子,既不多一双,也不少一双,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绝不会浪费,而且它可以根据这两千双鞋子设计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提供多少橡胶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也都可以做到环环相扣,效率的确是最高,但是它唯独不能考虑的就是这两千个人是不是喜欢这两千双鞋子。那么,就生产两千双鞋子而言,它可以做到效率最高,但是它能不能使消费者的主观效用达到最大的满足呢?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了。但是,这样一种经济,如果仅仅从效率的角度讲,我认为,可以说它是一种次优的经济,就是说它不如运作成功的市场经济,但是它比人类遇到过的其它经济类型恐怕要强。比如说,它比在亚洲地区更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而是基于农业社会的农民战争中,成长出来的那样一种浪漫主义激情,以及长官意志,从这种原则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经济结构,就是所谓的命令经济,或者说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对这样两种经济来讲,它在效率上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区别。
嘉宾:所谓马钢宪法是什么呢?马钢宪法比较极端地表现了苏联继承的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传统,这样的一种理性主义传统,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科学主义的计划经济概念。为了排除这种鞍(马)钢宪法的影响,六七十年代,中国曾经提出来一些创造,其中就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鞍钢宪法。实际上鞍钢宪法确立的那一套经济体制,整个来说就是和马钢宪法基本上是对着干的,马钢宪法强调经济核算,鞍钢宪法就强调政治挂帅,马钢宪法强调一长制,那么鞍钢宪法就强调党委制。马钢强调的是专家治厂,那么鞍钢宪法强调的是政工治厂,马钢宪法强调的是科层管理,鞍钢宪法强调的是群众运动。那么,这对当时的中国经济的确是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两种经济,虽然都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它们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我前面讲了,如果就效用增长的效益而言,这两种经济可能都不如市场经济,但是就实物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而言,这个理性计划经济可能是很有效率的,但是命令经济是很无效率的。那么就积累效率而言,这两种经济可能都相当有效率,就是它都可以让大家勒紧裤带,提高积累率,那么对亚洲和欧洲的这些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都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个对创新效率而言,如果就创新效率而言的话,我认为理性计划经济是最无效率的,正是因为它强调环环相扣,因此任何一个环节的技术突破,在整个经济流程中,都会引起紊乱,因此,它是不太鼓励创新的。而命令经济呢?在这个方面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不讲总量平衡,大家知道我们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学界曾经兴起过几次浪潮,来批判所谓的平衡论的,正是因为不讲平衡,所以它不太考虑整个经济流程的那种平衡性,所以它比较容易提出一些极端的口号,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但是这种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创新,绝大部分都是伪创新,因为这个经济中,缺乏一种验证创新的理性机制,因此,这种创新,往往是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那么,真正对一个创新的验证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是通过市场来确定的。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一个确定机制。
总而言之,在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就是实物生产效率,效用生产效率,积累效率和创新效率这几个方面,这两种经济都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走出理性计划经济的过程,因此也就极大的不同于走出命令经济的过程。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苏联联盟一级,有三千多个经济参数都是用电子计算机解最优化方程的办法来制定的,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一中断,会给整个经济造成极大的紊乱。但是对于那些命令经济的国家来说,他们基本上不存在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这种问题,命令经济机制,尤其是我国改革以前,文革中存在的那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那种形式,应该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无代价的可放弃性。也就是说,只要你放弃了这种经济,不管你回头来搞理性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你都会有绝对的正增益。你搞市场也会有增益,搞理性计划也会有增益。
这一点,邓小平在南巡讲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精彩,这句话在纸媒上我没有看到,但是在关于小平同志的电视纪录片中放了这句话,他说我们的改革其实在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整顿〃,大家经过1975年这段时间的人大概都知道,1975年的整顿根本就没有任何市场的色彩,所谓〃整顿〃就是把文革废除了的那些马钢宪法的那些内容恢复了一部分,也就是说把命令经济放弃了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些苏联式的管理模式。但是,就这么一点动作,中国的经济在1975年前后就有了很大的转机,这种优势只有中国才有,东欧国家是绝不可能从这方面得益的,因为他们在理性计划经济方面已经走得非常之极端了,已经可以说是理性得不能再理性了,那么放弃理性,他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都经历过一个市场(计划)调节失灵了,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又没有健全,那么样一个(混乱)时期,但是我们不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在运动经济时代就是一个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时代,所以不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时期,这是在效率方面。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理性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在可放弃性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肯尼斯·阿罗、斯蒂格利茨,很多人都曾经提到,历史上的经济转轨过程,实际上是个契约转换过程,就是人们从一种约定,过渡到另外一种约定,什么叫做约定呢?大家知道,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不光是计划经济,包括中世纪的那些农村公社,各种各样的一种束缚性体制,都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束缚性的共同体,它如果要稳定的存在,它必须在束缚功能之外,具有相应的保护功能。也就是说,我接受你的束缚,我接受这个体制的束缚,是以我得到这个体制的保护作为对应的,可是在共同体的束缚保护机制的对应性方面,亚洲的转轨国家和欧洲的转轨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像中国和俄国在开始集体化的时候,这个集体化主要都是起到一个提供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作用,那个时候是不太讲什么保障的,但是,把农民束缚得很厉害。但是,俄国通过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