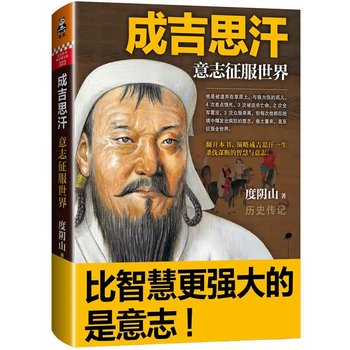寻找成吉思汗-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术珍宝被肆意破坏。史家并没有留下蒙古人杀人为乐的证据,只是理所当然地以为蒙古人丧心病狂,主导一幕幕的悲剧。但是,在蒙古人的史书——《蒙古秘史》中却说明得很清楚:作战的目的是俘虏敌人,抢回他们想要的女人、马匹、牛群以及金银财宝,把壮丁收归己有,惟一要摧毁的只有敌人的头目。蒙古人并不想反复杀戮。他们甚至会收养敌人的孩子,被击溃的部落也经常加入蒙古大军,成为他们往外推进的征战主力。成吉思汗就用这样的方法组织他的洲际远征军。蒙古人进入回教圣城不花剌,也是把当地的珍宝财富劫掠一空,与侵略蒙古其他部落没有两样。醉醺醺的蒙古大汉冲进清真寺内,扔掉珍贵的可兰经,因为他们要装可兰经的木匣来当马匹的秣料。喂马的时候,他们招来吓呆了的穆斯林学者给他们牵马。几个星期之内,穆斯林壮丁整编完毕,成为蒙古人的盟友,继续往前推进,展开下一场毁灭性的战役。
第二部分胡乱编派宗教信仰
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扭曲蒙古历史,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一个他们企盼已久的基督教救世先锋。这个谣言还流传了好一阵子。卢布鲁克和卡庇尼之所以不远千里赶到蒙古,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找到传说中捍卫基督教不遗余力的游侠——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祭司王是中古时代的传奇人物,在公元12世纪风靡一时。据说他是博士(Magi)的后裔,在遥远的东方统治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兵力强盛,无可匹敌,如果能与他联结,将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大支柱。这个误会大概是源于在撒尔马罕与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作战的喀拉汗(Kara khitai)。喀拉部落是一支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崛起前散布在蒙古高原间。喀拉部落在这场战役里,把塞尔柱土耳其人打得溃不成军。由于塞尔柱土耳其人信奉回教,西方人就一厢情愿地说,喀拉汗是基督教徒,其实,喀拉汗应该是异教徒或是佛教徒。
教皇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这位攻无不克的祭司王约翰,希望跟他讨论彼此信仰上的异同。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为争夺圣城耶路撒冷,十字军东征,与回教徒反复作战,相持不下之际,自然而然地又想起这位在东方的神秘基督教领袖。祭司王约翰的传言,于是在中古欧洲的君王间广泛流传。他们总是说,在回教徒统治的领土外,有一个可以联盟的强大盟友(当然就是不朽的祭司王约翰),只要使臣找到他,东西夹击,就再也不用怕回教徒了。成吉思汗在中亚崛起,处处与回教徒为敌,中亚强权望风披靡,这些事件经过有心人的渲染,辗转传到西方,他们就以为苦候已久的祭司王约翰或是他的孙子——大卫王(King David)终于出现了。
卡庇尼很快就察觉到这传言不大对劲,野蛮残暴的蒙古人怎么看也不像圣明祭司王的麾下。他碰到的这个部落,崇拜偶像,在帐棚中还悬着牛羊乳房的模型,蒙古人跟他说,这样可以保佑牲口多生产、多泌乳。除此之外,这些人对日月星辰、草木水火、土地天空,无所不拜,谈到了成吉思汗,更是崇拜得无以复加。一位俄罗斯王公,因为信奉基督教,拒绝向成吉思汗的画像下跪,蒙古人竟然一脚踹在他的肚皮上,把他踢个半死,然后拖出去砍头。卡庇尼于是推测,可能是这批异教徒把祭司王约翰的后裔从中亚赶到了印度,也许他应该去印度看看。卢布鲁克虽然一肚子狐疑,但是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在克剌和林找不到祭司王约翰,就自作主张,把成吉思汗编排成基督教徒,硬说他曾经受洗,是基督教徒,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戴着有色眼镜的卢布鲁克,在克剌和林到处寻找基督教的标志——蒙古包外无意搭成的十字架、不知道哪儿传来的钟声,都会被他认为是克剌和林有教堂,蒙古人尊重基督教的符号。
其实卢布鲁克也不算错得太离谱。蒙古的两个部落——克烈和乃蛮,的确深受聂斯托留教派(Nestorian)的影响。聂斯托留教派是基督教的旁支,起源于公元5世纪,经过波斯修道士的传播,盛行于中亚。许多克烈部的贵族都曾受洗,成吉思汗的一个妃子还到过流动教堂做礼拜。也许是受到这个妃子的影响,蒙古的第三任大汗,克剌和林的统治者蒙哥,有一天还叫卢布鲁克去找他,把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表演给他看。卢布鲁克兴冲冲地带着绘图圣经,训练了一个诵经团,恭恭谨谨地诵经,唱圣歌、赞美诗,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就把圣经里的插图呈给大汗过目。蒙哥看了插图,觉得挺好玩的,但也仅止于好玩而已,而且旁边还有一堆随从喝得烂醉,大煞风景,肆意破坏当时神圣庄严的气氛。大汗把圣经乱翻一通之后,“爬上他的大车,向诵经的教士挥挥手,就走了”。从此以后,卢布鲁克再也没有听说蒙古贵族对基督教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如果卢布鲁克再切合实际一点,他就会发现蒙古大汗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基本上,蒙哥信奉的是伟大的祖先成吉思汗以及古老相传的萨满教,只是他也不排斥别的宗教,有雅量随它们去发展。所以,蒙哥允许基督教、回教、佛教,在他的宫廷中传播。卢布鲁克看到在宫廷里的基督教徒,大感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半点神学修养。他说,聂斯托留教派的修士,连叙利亚文的圣经都看不懂,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放高利贷、娶了多房妻室,帮人举行宗教仪式,乱敲竹杠买卖神职不说,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遥远了,五十年前,才有主教在这里,所以,卢布鲁克宣称此地的主教拥有非常处置权,可以巡回乡间,替孩子主持涂油礼(anointment),即使孩子再小,也可以破例。卢布鲁克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教士来源。
卢布鲁克其实不用那么义愤填膺。聂斯托留教派的教士心里很清楚,不管是讲教义,还是道德劝说,蒙古人只会把它当做耳边风,他们还是信奉祖先传下来的规矩,碰到了疑难杂症,他们宁可去求萨满巫师。卢布鲁克压根瞧不起萨满巫师,说他们是“卖卦的”;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蒙古人清楚的解答,不管是扎营的地点,还是何时要开战,只要把祭品放在祖先的灵位前,诚心祈祷,巫师再用羊的肩胛骨卜筮,就会得到答案。先把羊骨收拾干净,然后放在火上烤一会儿,有道行的巫师就可以从骨头上的裂痕,看出天意,就跟看手相的人从一个人的手掌纹路,就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部分乃蛮之地
在接近葛鲁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卢布鲁克向蒙古人传教的心情。那天是7月27日,“大夫”跟我们说,我们已经踏上乃蛮故地,也就是信奉聂斯托留教派的那个蒙古部落的根据地。我们一路上看到好几个一圈一圈的石头遗迹,石头圈包围的面积都不算小,颇具气势,这是乃蛮宫廷旧址,面向一望无际的杭爱草原。天色将暗时,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墓穴,想来是一个乃蛮王公的沉睡之地。
葛鲁特已经在草原的另外一端向我们打招呼了。我们走了六十多英里,没有看到半栋永久性建筑,任何屋舍都会让我们眼睛一亮。仔细地打量这个小城,其实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方行政中心。哨子和害羞鬼想要回家,我们也就不耽搁他们了,索性连城也不进,就在这个地方向他们挥手作别,这两个人可以省几步路,收拾好他们的马匹,直接打道回府。我们才跟他们道再见,苏木中心就派人出来跟我们接头了。这个人说,我们的马匹快准备好了,不过集合地点不是在葛鲁特,而是在十英里外的曼陀罗(Mandal)喇嘛庙附近。所以,保罗、“大夫”、我搭上苏木的卡车在附近逛逛,阿乌博德、巴雅尔和戴尔哲三个人去把我们的马匹赶回来。
曼陀罗寺让我们发现意外的惊喜。我们在一个牧羊人的废弃帐棚里草草过了一夜,正盼着我们的马时,有个年轻人骑马经过,怯生生地问我们要不要看看附近的圣像。后来,我们才弄明白这个小朋友今年十六岁,想当喇嘛。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喇嘛教恢复流传了,他学了一些喇嘛教的教义,今年秋天就要剃去头发,换上喇嘛服饰,正式当个小喇嘛。我们问他,他父母知道他要出家之后,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没有半点迟疑——“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
我们的营地扎在一个小悬崖的避风处。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弟弟,领着我、保罗与“大夫”,绕过悬崖底部,走了大约半英里路,就看到了几个矮小平坦的石头,表面上刻满了西藏经文。我们的小向导说,这都是曼陀罗寺喇嘛刻的西藏佛教经典。曼陀罗寺是蒙古最渊远流长的喇嘛庙圣地,庙中高僧无数。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经文,散布在石头间。然后,我们就在山壁上,见着第一尊在莲花上打坐的浮雕佛陀,隐约可以分辨出红、蓝、棕色,那是昔日彩绘的痕迹。又走了一会儿,在一条小溪的山脚上,是一尊更大的佛陀像,旁边是一尊骑在龙狮身上的降魔尊者,再过来就是天女(Ayush Baksh)。我们数了数,像这样的石雕总共有九处,可是这两个小朋友告诉我,应该有十八处才对。这些雕像应该是19世纪以后的艺术品,时代不久,但是曼陀罗寺喇嘛发了偌大心愿,才把这些垂直山壁雕成不朽的佛像经典,让他们的信仰巍然长存。我们正要重拾旧路,打道回府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往上一指,我们看到了五十英尺左右的上方,有个白晃晃的东西挂在山壁上晃荡着。他告诉我,那些都是人骨,僧侣死后,把他们的骨头挂在山上,好像给山壁挂上了一串项链。
我们回到营地之后,备马已经送到。除了马匹之外,还招来了一大堆好奇的当地牧民。把辎重补给放在半野生的蒙古马上,自然又是一片混乱,我们的营地顿时热闹非凡。其中有两个牧民,应该是我们的向导吧。看到他们手脚利落,安排行李,有条不紊,我觉得很高兴。我站在一旁,看他们要分哪一匹马给我。他们终于挑定了一匹马,马主人看起来颇有忧色,他原本就担心他的马胆子太小,现在又害怕我们这些外国人会恶整他的马——跟其他的蒙古牧民一样,他也认为外国人不会骑马。我一再向他保证,我们会好好对待他的马匹,但他还是围着我打转,一脸狐疑。我拿出我的马鞍,他坚持要替我放在马背上。我这副外国鞍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牧民们簇拥过来,好奇地打量我的时新行头。我还拿出了我的马尾皮带(crupper strap),告诉马匹的主人,要怎么从马鞍的后端拉出皮带,再绑在马尾巴的根部。蒙古牧民好像被我的话吓坏了,他这辈子还没看过马尾皮带。我请“大夫”替我解释,为了防止马鞍往前滑,马尾皮带是少不了的设计。“大夫”费尽口舌向他解释了半天,竟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皮带根本就是恶搞,会把他的马弄坏的。他的马匹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东西。”
“跟他说,我很坚持。全世界有许多国家,都用这种附有马尾皮带的马鞍。没有这种皮带,上山下山,马鞍就会很容易滑下来。”
从牧民的表情看来,他们觉得我根本是胡说八道。但是,我的态度坚定,牧民看我一副认真的模样,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但他要亲自绑这马尾皮带,于是,我教他怎么从马鞍的末端拉出马尾皮带,怎么样把它扣到马匹尾巴的根处。他小心翼翼的把马尾巴拉起来,再把皮带拉到马尾根处,但是,他实在是太迟疑了,马儿感觉到他的不安,一溜烟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牧民只好再试一次,不过还是笨手笨脚的,依旧没有成功。看到一个一生与马为伍的老牧民,居然拿马尾皮带无可奈何,其实蛮好笑的。这牧民以为挑的马匹不乖,这次他挑了一头小马,还把它妈妈拉过来站在它的身边,让它安分点。但是,这个牧民实在太不熟悉这种设计了,连小马的尾巴都拉不起来,简单的任务再度受挫。我尽可能地维持礼貌,从他手上接过马尾皮带,拉起小马的尾巴,轻轻松松地把皮带固定好、就定位,这匹马连动都没有动。马主人看起来相当惊讶,围在旁边看热闹的人都哄笑起来。我请牧民亲自上马感觉一下,他就试了起来,跑了几圈。他还是认为马儿会受不了马尾皮带,频频下马,拉拉扯扯,看坐骑会不会不舒服,没有想到马根本没有异样的感觉,最后,他高兴地点点头,总算是认可了。
在木栅后面,总共只有二三十顶蒙古包,在喇嘛庙被摧毁之前,曼陀罗设县只是为了宗教理由。如今,构成喇嘛建筑群的主体的,只剩下佛塔了,青绿的塔顶自然成了此地的主色调。掺杂其间的建筑,原本可能是讲经堂、精舍、山房和储存杂物的地方,但是,年久失修,一片荒烟蔓草,已不复昔日风采,建筑功能也不可分辨。屋顶上面长满杂草,横梁脱离了原先的接驳处,斜倒在一旁,屋顶上的磁砖大多脱落,在一旁堆得好高,土墙被人打了洞,显然是把庙宇的内部当做牛棚。不过,恢复旧观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毕竟没有受到推土机的全面破坏,虽然破败,屋舍大抵完好。
有一小群僧侣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宗教社区,使这里重拾原先的功能。连大喇嘛一并算上,这里有六个喇嘛,庙社无法住人,他们就在原先的主建筑间搭了一个蒙古包,簇新洁白,醒目得很,上面还挂了一个招牌,告诉大家,这里正是曼陀罗寺僧暂时栖身之地。
我们打算上路了。庙里的老喇嘛与其他寺僧拐着脚,坚持要送我们上路。他们排在蒙古包的前面,向我们挥手道别。有几个喇嘛实在太老了,连腰也直不起来,得靠手杖才能勉强站着。他们站在阳光中,穿著鲜丽的僧袍,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布斯卓的观察,“深红、亮橘、隐隐泛光的淡肉桂红”,一群喇嘛站在一块儿,会让人想起“一畦鹦鹉郁金香”。
第二部分贫瘠的草原
离开曼陀罗寺的道路的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