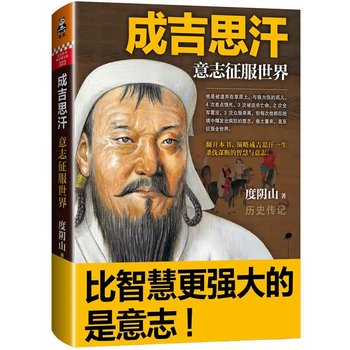寻找成吉思汗-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还能说出她师傅的名字,他们叫山格烈和马格奈,就是这两个人引导她承接萨满传统,一步步地引她入门。她的父亲德尔扎也是萨满巫师,但是自己并没有插手教导。她神奇的力量或许来自德尔扎的遗传,但教她如何运用的,却是她的两个师傅。我问起训练过程,她的答案有些模糊。她说,他们俩教她吟唱、念咒,不断地鼓励她。那她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她身上的萨满力量呢?“十三岁。”她突然从床边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靴子,往前蹦跳了三四步,就在我错愕之际,她开始解释了,“我的身体里有股力量。打从小开始就坐不住,晚上睡不着,非起来跑不可。晚上,他们把我关在蒙古包里,我就从天窗钻出去,跑啊,跑啊,一个劲儿地跑。我喜欢在夜里跑步、爬树,学猫头鹰叫唤。我跑得太快了,没有人抓得住我。有时候,他们干脆放狗来追我,但是,连它们也追不上我。”
现在的医生可能会说她是个多动儿,但对珊嘉来说,她成为萨满巫师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事情,老萨满在她身上见到了萨满巫师的特质,找上了她。真的要问她原因,想来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坐立难安的本性跟想要爬高的欲望,是萨满巫师的典型特征。萨满巫师的启蒙仪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小巫师爬竹竿,象征他拥有与上天精灵沟通的能力。以蒙古包的天窗为门户,也是萨满巫师的看家本领。《蒙古秘史》记载,不只泰伯—腾格里(Teb…Tengri)是从天窗出入,就连成吉思汗的祖先据说也是这么来的。书中说:“每夜都有黄白色的人,借着天窗与门额上露的光,抚摸我的肚皮。”这位夫人就因此怀孕了。在蒙古的传说中,萨满可以在天空翱翔。珊嘉虽然不识字,却会说一种奇特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是口头语言。也许她是跟哪个博学多闻的吐瓦学者学来的,但看起来实在不像。珊嘉回顾她的过去,解释她的能力,神情语调都是那么自然,看不出半点心机,实在没法相信她在作假。
第三部分老婆婆的魔法(2)
珊嘉的女儿递给她一大瓢奶酒,她狼吞虎咽,两三口就喝完了。酒精唤起了她的记忆,少年往事,一一浮上心头。“还有一个萨满——库斯忽,也教过我不少东西。他在我身上出现了奇异的力量,把它引到正轨上去。我‘看’得见,这不是我的愿望,但就是自然地会了。我必须要飞,却也免不了摔在坚硬的石头上。这种生活很奇怪、很辛苦。”她实在忍不住了,伸手又讨了一大瓢奶酒。
“我的父亲很宠我。他有两匹马,一匹白的,一匹黄的。我喜欢骑着这两匹马在草原上奔驰,我喜欢那种飞奔的感觉。我骑在这两匹马上,没有人拦得住我。有一天,有个老头带着两大口袋的奶酒,来找我父亲,问我父亲可不可以让我嫁到他们家当媳妇。我跑开了,但是一个留胡子的汉子一路把我拖回他家。我丈夫是个好猎人,也当商队向导,常常会从遥远海边带些红盐回家。”
“大夫”在这个地方插嘴,告诉我说,珊嘉说的商队可能是越过天山山脉,到中国海边去买盐的贩子。珊嘉一点也不在意,还是不断地喃喃自语,突然间,“大夫”的脸色一变,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停下他的翻译,讲了一段他自己的感受,让我也吓了一跳。
“刚才她说得很起劲的时候,插了一段跟前文没半点关联的话。她突然问我,在我家里是不是有一副连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眼镜,然后她又开始讲她的童年往事了。”
我知道“大夫”为什么吓了一跳。前一阵子,我们在他乌兰巴托的家中打包时,我看到一副眼镜。我顺手把眼镜递给“大夫”,但是他又还给我,说不是他的。“大夫”说,那么眼镜一定是保罗的?可也不是。这副眼镜于是被扔到一边,没人再理会它了。这当然有点蹊跷,在物质贫乏的蒙古置办一副眼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眼镜丢了,谁都会花点工夫去把它找回来。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珊嘉却晓得。当然,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她可能胡乱猜中的,也许是他们这行惯用的把戏。我始终自我克制,不敢轻易要求珊嘉展示她的特异功能。而她一路娓娓道来,也没有弄过什么玄虚,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好像她知道有那副眼镜是天经地义的。
她的蒙古包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还有点寒酸。帐棚里面也没有看见她有特殊的行头。蒙古包里没有装饰,就靠一根没怎么修整、打磨的木头,撑起蒙古包顶的伞骨。简单来说,这里没有半点特殊或神秘的地方。这个简单的蒙古包里,挤满了孩子和珊嘉的近亲,每个人都睁大了好奇的双眼。珊嘉那个当老师的孙子非常担心我们没有清楚体会珊嘉的超能力,还特别向我们强调:“她可以预知未来。”她孙子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在说她下厨的手艺很好。“布里兹涅夫(Brezhnev)死前十天,她就知道了。有人来拜访她,她也知道,会预先告诉我们。哪个方向会出大事,她也能未卜先知,就算再远,她也会有预感,就好像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样。”
“你能预知家中的事情吗?”我问她。我避开了敏感的问题,没敢直接问她有没有预知到我们来拜访她,因为这样的测试未免明显了点。
“不能。”珊嘉说,“我惟一预知到的事情是我妈妈过世,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在怎样的状况往生。”
奶酒好像发挥功效了,她的话越来越多,从这个话题跳到那个话题,没有半点理路。
“我根本就不想要有这种能力,我常常想,时候到了,该走了,不要再活下去了。但是,人们舍不得我,一直把我留在尘世,他们需要我。大家在外面累得像条狗,我会飞到他们身边,援助他们。我精神好的时候,可以飞好几个山谷,到他们身边帮助他们、安慰他们。”
“你的法力什么时候最强?”我问道。
“每个月的第九天,或是在新年。”
她的孙子插嘴了,问我们要不要在她奶奶太累之前,请她表演萨满的招灵仪式。“如果她有意愿的话,”我答道,“如果她太累了,就不要勉强。也许现在不合适,这个地方也不方便。”
珊嘉根本不理会我的回答,她性急得很,一定要在客人面前露两手。“如果附近有电力,或是光线太强的话,会影响我作法,没法凝定心神。”她说,“不过,很抱歉,我现在没有合适的行头,我父亲传给我的手鼓铃多年前就坏掉了,我一直没有替换。萨满巫师的服装也破破烂烂,穿不得了。我这么老了,不想再做新的了。不过,没有这些行头一样可以作法,我只要我的帽子和连枷(flail)就行了。”
第三部分萨满招灵式
她站起来,她的女儿帮她戴上萨满教的头巾,在头巾和发梳之间,用一个十字形的装饰拴住。这副头巾有一个长长的后摆,可以遮住脖子,头巾的上端缝了一排珍珠状的扣子。珊嘉还在前额绑上一条粗粗的带子,像一顶前端有些磨损的烂假发。这副不齐的行头穿戴起来,顿时让一个居家的老太婆变成了邪里邪气的怪物,与格林童话中的巫婆有些神似。
但是,吐瓦小朋友一点也不害怕。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他们的婆婆做她常做的事情而已。他们在一旁静静等待神灵降在她的身上。珊嘉开始喃喃自语,低声吟唱,身体开始摆动。她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蒙古包的角落,嘴里还是在念咒,她的脑袋东摇西晃,慢慢地跪下来,身子还是抖个不停。她的手中握着小小的连枷,大约有一英尺长,顶端绑了些破碎的白布,还有一个亮晃晃的透明球体,不知道是水晶还是玻璃。她一边唱,一边把连枷前后摇动,还蛮有韵律的。有时,她会休息一会儿,等气喘过来,再开始念咒。突然之间,她停了下来。她的女儿就站在她的身后。珊嘉还是跪着,手慢慢伸向身后,她的女儿赶紧递给她一个点燃的烟斗。珊嘉把烟斗放进口中,猛抽了一口,朝蒙古包的角落喷去;没一会儿,她陡然把烟斗插向背后,她的女儿顺手接了过来。这位老妇人很艰难、很痛苦地站起身来,从女儿手上接过一勺子的马奶,把马奶往空中一洒,奉献给空气中的精灵。这个动作她重复了三次,接着,在蒙古包的几个角落里祈祷,又洒了点马奶驱邪。然后她坐在床边休息了一阵子,身子又抖了起来,也许是因为累吧,要不然就是假装的,我没法确定。
她突然又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吓了我们一跳。虽然,她曾经说过,她在太亮的地方没法凝定心思,但她还是走到亮晃晃的阳光下,跪了下来,身子越弯越低,脸几乎挨到了膝盖。正对着蒙古包门处,有一个黄铜火盆。珊嘉又吟唱起来,连枷前后晃动。她的女儿赶了上去,朝炭火里撒了一些灰,又从一个大水壶里倒了些马奶在杯子里,用手指点了点,四处洒洒,祭祀天空与炉火中的精灵。珊嘉霍地站起,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蒙古包门里,她的女儿还是跟在她身后,托着那个铜火盆。最后,珊嘉又在蒙古包内巡回一次,她在每个成人的鼻端前面,放一搓烟灰,在他们面前摇摇连枷。连枷摇回珊嘉那一头的时候,她会把脸伸进连枷头部,深深地吸一口气,不停地嘟嘟囔囔,好像要把那里面的空气吸尽似的。终于,珊嘉退回床边,坐了下来,筋疲力竭。
我从头到尾都看得很仔细,我觉得也许珊嘉不是道行很高的萨满巫师,但是,她绝对不是作假。她展现的撒满仪式,看起来也是有所师承,只是我们弄不清楚,她到底是看着别人的样子学会的,还是经过系统的教导。举个例子来说,珊嘉进出蒙古包的方法,就是正统的萨满规矩。她经过门口总共两趟,每一趟她都要转个身,倒着进去。我第一次见到她在刷锅子时,她是正面向前,跟一般人一样进门的,但是,当她化身为萨满巫师,她的言行就变了,变得与常人常态相反。还有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例子是,她是从背后接烟斗的,跟一般人从面前接是不一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倒行逆施”始终是萨满教的传统。萨满巫师一半活在我们的世界,另一半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他们的精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遨游,是出神去跟精灵对话。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反的,上面在下面,里面是外面,前后也是全然相反,就像照镜子一样。有的萨满巫师甚至把衣服翻过来穿,或是把手套翻过来戴,变成毛在里面、皮板在外面的怪相。我想,珊嘉头上那毛茸茸的黑色硬边,可能也是象征头发是倒着长的萨满信仰。
我觉得这次的访问应该到此为止了,珊嘉已经尽力告诉我,萨满教是怎么一回事,再接下去,我很难不冒犯这家人、辜负他们善意的邀请。珊嘉告诉我,她怎么当上萨满巫师的过程有根有据,也不像在撒谎。她小时候正是萨满教盛行的时期。从外表上看来,她展现的萨满仪式不像她自己捏造出来的。她不经意地提到一件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那副无主的眼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
第三部分法力干扰
两个月后,我回家了,这时,我才发现还有一个现象也没法解释。珊嘉作法之前,曾经提到两个会影响她集中注意力的因素——强光和电力干扰。我们窝在她那小小的蒙古包里时,我悄悄地拿出迷你摄影机,拍摄她的作法过程。虽然在帐棚中有些昏暗,我却不敢拿出头灯补光。珊嘉说得很清楚,强光与电力会影响她作法。但是,迷你摄影机终究是要吃电的,只是我没有告诉珊嘉而已,它用的是六枚三号电池,我那时并不知道机器已经有毛病了。聚光镜坏了,微型马达把高频闪光转成持续不断的沙沙声,记录在影片的声带上,出现了煎培根般的声音。冲完片之后,我才发现,在蒙古拍的影片都免不了有这种电波干扰,只有珊嘉那一段例外。珊嘉在摄影机前手舞足蹈,杂音却明显小得多——干扰仍然在,不过却变得若有似无,不仔细听,听不出来。我的直觉是:这个异象和先前珊嘉提到那副眼镜一样,不是巧合,就是珊嘉真有萨满法力。萨满在作法的时候,最讨厌电力在一旁捣乱,所以,她的精神力量压制了附近的电波干扰。
但这只是后来的臆测,我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做点简单的实验,以搞清楚珊嘉的“法力”是怎么回事。说实话,真要这么硬干的话并不怎么得体。珊嘉的言行叙述很有说服力,而我也得到一个好机会,一窥成吉思汗时代的遗产,这就够了。事实很明显:珊嘉的家人、族人,都把这位“老婆婆”当成萨满精灵的化身,我看不出她有假冒的嫌疑,或是打着萨满的名号行骗。在部落族人的眼里,珊嘉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遇到疑难杂症,可以找她商量,她是他们信赖的朋友。珊嘉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也因为人们的这种信仰,使珊嘉保存了成吉思汗以降的萨满传统。
珊嘉的家人非要保罗帮他们拍张相片,否则不放他走。他们面带微笑地排成一列,这会儿的珊嘉换上吐瓦的传统服装,怀里还抱了个裹着襁褓的娃娃。保罗跟我的感觉一样,都很喜欢这个不造作又和气的老人家。他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要尊重自然,因为你就是自然!照顾好给你水喝的小溪大河,照顾好让你暖和的空气,照顾好养育你的土地!”看来,这位吐瓦老婆婆的箴言真有流传的价值。
也就是北美所谓的prairie dogs。
这又是一个土耳其文在蒙古人间流传的例子,卢布鲁克用的sogur这个字并非蒙文,而是土耳其文——原注。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
他著有《瘟疫与民族》(Plagues and Peoples,Qxford;1976)——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