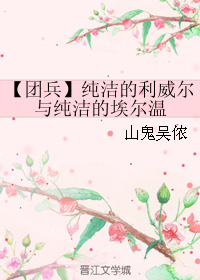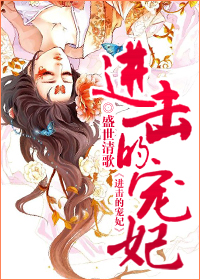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我就阅读了有关他的文章,就是第二天的那些文章。因为我觉得名人死了时候的那些文章总是非常漂亮的,正如俗话所说,鳄鱼们总是充满一种高尚,做出的悲痛,一篇适度的诗歌,一种仁慈……你给他死一个重要人物,他就会拿出他自己最好的东西人道。这是认真的,并不是论战,我是说真的:当某个神秘人物死了时,我们都很美,使我们面貌上自然地有一种姿势,某种态度,一种明确的阴影……我们突然变得优雅……动情……可以说就是要让我们这样做的:埋葬大人物。
我就是这样在那里阅读那些文章,并非我真是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的狂热者,我不能说我是,但是由于阅读带来的力量,使我产生了一种如此不可抗拒的怀念而直至一分钟前客观上这是不存在的那点悲伤也就足以使我站起来在那些唱片中寻找那张唱片。当然并没有找着,而很明确的感觉是,如果我找不到它,我就会出去,就会去买它,因为如果我听不到它,我就会发疯的。在那张唱片里他演奏的是加卢皮的作品。
加卢皮名为巴尔达萨雷,本是威尼斯的一位作曲家,属于人们几乎不再记得的作曲家之一,在十八世纪出生和去世。他写了许多东西,其中有许多属于键盘乐器演奏曲,其中之一是C大调,也就是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演奏的那个作品。如果不是他演奏了那个作品,那么那个作品大概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上帝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一大堆东西中捞出了那一个作品,并且演奏它。于是,谁也不会再忘记那个作品了。
开头是个天堂曲,这个我记得准确。开头就让你吃惊。读读那个作品,是一种极为简单的音乐,根本没有什么。左边是个非常通俗的阿尔贝尔托低音,右边是弯弯曲曲的音符一个接着另一个,没有高低8度,只有这里或那里的某些胆小的美化,整个儿是行板(实际上就是天堂曲)。读着那作品,你会觉得那不值两个钱。但是必须听听他如何演奏这部作品。他打开了这部作品。他演奏得比应该的还慢,他所演奏的就是《让光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你所能获得的那种东西,只要你善于让光通过。他用钢琴演奏,一个一个地打开那音符,好似在开阔的大海中那帆船的舷窗一样。这也是荒唐的,如果我们好好地想一想的话。因为善良的加卢皮连见都没见过那真正的钢琴,而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用他那台施泰因威牌的钢琴,就像抓到一个小手工艺品,他打开每一个音符,我不知道怎样,也许他用踏板来操纵,也许是碰一碰就行了。而那里的那个声音我在别的地方肯定从来没有听到过,事实上到最后不再是一个小手工艺品,而是一片林中空地。一片林中空地,就像正是在世界森林之中切出来的一片林中空地。一种拯救。我终于相信,甚至具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因为我听那个作品已经多年,我在寻找正确的词语来称谓那个音乐所讲述的感情的细腻,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我向任何人都可以发出挑战去找到它,我也可能错了,但是在我看来没有那个词语。是更站在喜悦一边呢还是悲痛一边呢?你也不太明白,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一种你认识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与怀念有关但又不是怀念,与惊奇有关但又不是惊奇。你所知道的惟一东西就是使你着迷的东西,这是确实的,但是那里那种感情的名字你没有。而这是真正的天才演奏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名字来的一种东西。贝内德蒂·米凯朗杰利演奏了许多这类东西,但我将记着那里的那种杂技般的那场演奏:在绝对简单的几个基本音符的演奏中说出一个不存在的名字。
/* 17 */
世界的起源
要坚强,挨饿,活着
最后一篇《巴南姆》专栏文章。我是认真说的。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巴南姆》专栏文章。事实是这样的:你在那里做一件事情,你力求尽可能做得好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心里想到第二件事情,你继续做那第一件事情。但与此同时那另一件事情又让你产生幻想,最终到了这样一天,你停止做第一件事情并试着做那另一件事情。这就是这样的一天。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最近在这个专栏版面上,要用作新闻纪事,就是如此。
①斯普林斯汀,美国摇滚乐歌唱家和作曲家译注。最后一篇《巴南姆》专栏文章不谈什么。我喜欢这样一些影片:在这些影片中,结尾是一个固定的图像,那里不发生任何事情,简单地从音乐里传出一首歌,稍后即是片尾字幕。那个图像你们自己选。我选择了一首歌。没有什么特别讲究,就是斯普林斯汀①(头儿)的最后一张唱片的最后那首歌。在我看来,那首歌非常美。而我也不很清楚为什么,但是对于就此结束、结束这一切来说,那首歌是恰到好处的。
歌名叫〃Thishardland〃,这里是无法翻译的,因为英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而意大利语则要逊色。大意是这样:《这片硬土地》。而你们很清楚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我觉得可以翻译成意大利语,题为《这片操蛋的土地》。头儿开始口吹口琴,没有打击乐器,没有键盘乐器,只有一把吉他,弹得有点儿乱,然后他离开口琴抬起头来,开始用他那种会让你们大家都去那个地方的声音唱起来。他唱的歌词大意是:〃哎,先生,你不会告诉我我播种的那些种子究竟怎么回事儿。先生,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什么都没长出来?那些种子飞到一个又一个城市,最后回到这里,重新落入我的手中,又回到了这里的这片操蛋的臭屎土地中。〃在这个时候,吉他继续乱弹,头儿慢慢地说〃comeon〃,我想像是说转过一点,对其他人说〃comeon〃。结果发生的情况是,打击乐和键盘乐全都起来,你感到背上有点打哆嗦,而从你屁股下面走的是摇滚乐。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最优秀的、可爱的老摇滚车放下了小窗户,全速前进,也不拐个弯,围绕着数十公里的硬土地。
旋律,那个旋律我不能写,因此必须听它,或者想像它,但不管怎样,是属于摇滚舞蹈的旋律,有点儿伤感但很有力量,在不怎么样的一种谐音中整个儿混合在一起。斯普林斯汀给我们唱我无法翻译的那些故事片段,但总是惟一的一个故事,那就是这么一个人的故事:在那片硬土地上到处旅行,到所有能去的地方,寻找自己的一个位置,如此等等。他不时地给我们吹口琴,他知道,这可以刺激一下心脏。最后,低声唱最后一节。在最后一节中,那些舞曲总是吸引来一位朋友,这家伙是个老朋友,年轻时候你就与他喝醉酒的那位,把你的姑娘骗走的那位,每个星期三买报纸来念给你的那位,在那里就是这类朋友。而事实上,弗兰克这位朋友也到这里来。必须用他的声音、头儿的声音来想像:哎,弗兰克,今晚你为什么不把所有东西都装在行李箱子里,到我这儿来,在下面逍遥宫?兄弟,只好给你一个吻,然后但愿我们去转转,一直转到我们再也走不动,我们都倒在地上。我们可以在田野里或者在河边睡觉,然后早晨我们再想出点东西来……不管如何,如果你不能,那也没关系:stayhard;stayhungry;stayalive;ifyoucan;如果你能,你要坚强,挨饿,活着,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我们将在这里的这片操蛋土地的一个梦中相会。
然后其余都是摇滚乐,没有歌词,只有大量的口琴、吉他和打击乐器。速度加快,走了,在立体声中消失在远处,越来越远,走了。我发誓那很美。并不像原来觉得的那样悲伤,摇滚乐从来就不是真正悲伤的,它不可能做到真正悲伤,也许差一点就到了,但只是一种感触而已,悲伤则是另一回事。
不管怎样,就这样结束了。
片尾字幕。
一个人总在注视着那片尾字幕,因为保证露出但愿是在理发师中或售货员中的某个非常美丽的名字,总是有一个SanteSalutiddio;或一个亚伯拉罕·林肯,或一个Jim〃BuckBack〃Sunrise:对这类爱好者来说,真是一个矿藏。
好吧。片尾字幕。
要坚强,挨饿,活着,如果你们能够的话。
完。
/* 18 */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美国高速公路是笔直笔直的一种东西,如此你会产生许多奇怪想法。从盐湖城到旧金山的那条高速公路叫八十号,它特别直,因而使你产生特别奇怪的想法。就是在那里,使我想起美国人是多么肥胖,进而想到他们那丰盛饭食的整个一系列形象。我到达旧金山时已积累了数十个形象,于是我想到:如果后来我还记得那些的话,但愿我能把它写下来。我记住了那些形象,至少其中一些。
有一次,我去看一场棒球比赛。洛杉矶的多得格斯队对我不知道什么队。真让我惊奇。我不相信怎么能存在一场如此令人厌烦的比赛,真的。还有要说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竞技表演,总而言之,厌烦得真叫人难受。于是我就问了问周围的人,以便弄明白他们找到了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后面那么热闹。有一天,一位先生对我说:〃如果你能正在吃着东西的时候观看,那棒球就是最好的东西。〃后来我在电视机前作了验证,我可以确认。不可能吃着东西观看一场足球比赛,篮球赛也不行,田径比赛也不行,水球比赛也不行,但是如果有棒球比赛,则似乎他们恰恰是研究好了的。这是一个节奏和停顿的问题。他们所做的不是玩球,他们在以你的汉堡包节奏跳舞。我想,他们把一次行动与另一次行动之间的等候时间调整到去厨房,在冰箱里拿另一瓶啤酒,再回到座椅上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最后我明白了棒球。于是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如此肥胖。
美国人如此肥胖,以至小号尺寸几乎不存在。相反,你可能碰巧找着XXXL号的短袖毛线衣,转换成体重公斤数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事儿不容易弄明白,因为人们一般想像美国人是可怕地健康和过分地喜欢体育运动的。至少会想像美国人都穿着短裤衩、戴着小帽子跑步,像总统那样。我的英语教授(目测为XXL号)有一次对我解释说:〃我们跑得很多,但是从来不走路。〃的确,他们只是从家里去车库才步行,其余都是汽车。一辆汽车的座椅就是那要特大号的屁股的最佳座位。
他们吃饭,但方式奇怪。例如:奶酪。迟早你会自问:怎么会在一个牧场、奶牛、牧马人的国家里,实际上只有一种奶酪呢?没有任何人想到隆巴迪大区的奶酪〃斯特拉基诺〃,可能吗?我不说要达到顶级的帕尔马奶酪〃帕尔米吉阿诺〃,但是那种鲜奶酪呢?那意大利南方的奶酪〃卡奇奥卡瓦洛〃呢?什么也没有。美国奶酪是一种,只有一种,用来放在汉堡包里的切成薄片的那玩意儿。当汉堡包里面有这玩意儿时就变成干酪汉堡包,更容易吞下去,不那么需要用番茄酱或者用可口可乐来润滑它。
噢,可口可乐。关于它,你在美国可以学到许多东西。第一,更容易找到百氏可乐。第二,避免要像樱桃味那类糟糕的变种。第三,戴亚特(Diet)更好喝,它跟我们这里有的那种东西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也是根本的一点就是:可口可乐加冰喝。在这方面,恐怕在意大利需要给餐馆、酒吧、公路餐馆的人办进修班。在这里,当你要求给可口可乐加冰时,毫不客气的回答是:那是冰镇的。这有什么关系?要一劳永逸地说一次:冰块是用来稀释可口可乐的,而不是要它变凉的。劳驾,这并不难明白。用来稀释它的。你们别加那柠檬片了。谢谢。
这一章是汉堡包。汉堡包、干酪汉堡包、香汉堡包、金汉堡包……在卡斯泰(南达科他州)我还找到了布朗托汉堡包。在一个游乐园里卖,那个游乐园是献给卡通片里的《祖先》的,〃弗兰斯托尼斯〃、〃威尔马,给我棍棒〃,全都在模型里,但全都是〃汉纳和巴尔贝拉制片公司〃那石器时代的东西。花四点九九美元买一个布朗托汉堡包。那原汁原味的汉堡包你在那个体育场里知道,那里卖给你面包夹肉饼,然后你到那极为丰盛的自助餐台上挑选东西加进面包中,真正好玩的就从那里开始。在那里你明白了,那个肉饼,就是那肉,纯粹是个名义,是一种精神支柱,就像罗西尼的歌剧中的旋律那样,重要的并不在那里,而在于附加的东西,在于美化,在于修饰。湖人队的一位球迷在那两片面包之间(且有一块肉饼作为基础)所能做到的,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有一种艺术来使不稳定的东西呆着,控制住调味汁,把洋葱圈圈堆起来,不让那咸肉掉出来。在这方面,真有些大师。弄完了的时候,你拿着那〃东西〃(〃汉堡包〃已经变成了不那么贴切的词了),把它放在一个带有你心爱球队颜色的小纸盘子里,你还用薯条把那东西埋了起来,然后回到你的座位上。你旁边有妻子,她正在喝完那半升的奶昔;有第一个儿子,他正在埋头于一个巨大的三色棉花糖;有第二个儿子,正在把那奶油涂得满脸都是;有第三个儿子,厌食症患者,正在吃紫色的糖爆玉米花。所有这些东西总重量大体上达到一只熊猫的重量。
从表面上初看起来,似乎这一切可能带来可怕的胃肠灾难的幽灵:一种心甘情愿、兴高采烈的集体自杀。不过这里也要有所区别。因为美国人具有一种完全是基本的价值体系,好像都还没有到先锋时代,把纯粹而简单的〃挽救生命〃摆在首位,他们坚持注意安全。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到了一定的时候做出了戒烟的决定,而且他们做到了。当他们决定在市内限时速三十公里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发动机排量从来就没有小于三千毫升的,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是硬汉子。于是,为了对付滥用食品,他们搞了一系列的伪装和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一进入某个超市你就会看到那醒目的东西。到处可见的对你发出袭击的只是一句话:不含胆固醇。再到里面一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