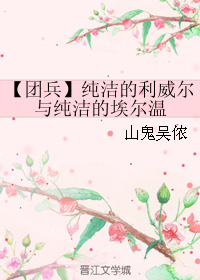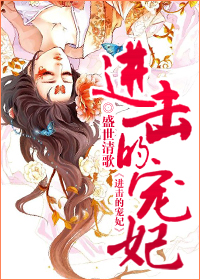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安诺尔·尼马科也有着某种英雄的东西:他像一座雕像似的在那里主持着博览会里最令人悲伤的展台。灯也一直关着,以便使效果完美。书架上摆着的似乎是一些教堂公报,封面上连一张照片也没有,只有素描画。书名诸如《鹰和鸡》、《大象跑哪里去了》、《喜爱柑橘的利齐尔》。是加纳的出版社,由八家国家出版商组织在一起,由政府出钱送到法兰克福这里来的。尼马科是一位政府官员。他为自己在那里关着灯同书在一起而感到骄傲。我不信任地问他,那些书是否卖掉了一些。他大笑起来,回答说:没有。为什么?他说几乎都是儿童书籍。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你想要一棵高大的植物,你就应当在它还是幼小的时候特别注意浇灌它。我想,第三世界也各有其作为的方式。当我告别尼马科而走到邻近的展台的时候,我确信这点。孟加拉出版商展台灯光极为明亮,在墙上挂着耀眼的大挂历,挂历上的女孩子们有着杏仁眼和高高的乳房。那不是画的,而是照片,似乎是立体的。的确,各有各的方式。
/* 21 */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钢琴科学家
世界当然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去想,但是,波利尼①把贝多芬的奏鸣曲集中在一起,这可是非同一般。不管那会使人觉得是多么愚蠢的事,但那是发生的一段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一段次要的、外围的历史,但那是历史。就是发生这样的事。
①毛里奇奥·波利尼(1942…),意大利钢琴家兼乐队指挥。1960年获华沙肖邦音乐比赛奖译注。过去,听波利尼的演奏曾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奇妙经历,绝对的。这是说七十年代。那时有人像上帝那样在外面演奏,但是如果你碰到一场他的音乐会,那么你听到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从那黑色大动物里弹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如果想要给那一切找个名字,你就会想到:科学家。他是科学家。他在发出音符中的完美和干净,是其他地方所听不到的。即使是乐谱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密密麻麻,你也能听清所有音符,而其他人则会用没有区别的、诗一般的声浪来对付过去:他却让你听到所有音符,仿佛在读出一种化合物的成分。如果有把一个符号变成字面上的音响的一种方式,而又没有感情用事或者侥幸处理,那就是他的演奏方式。像任何一种科学那样,它也似乎是不人道的。其他人延长和缩短时间,用踏板来走私艺术,添加油彩,弄脏这里和那里,故意这样做或者出于需要;他却是绝对忠实于原作,着迷地尊重节拍,彻底拒绝任何模仿做法、感情用事的转调、表情方面的混乱波动。进入他手里的东西,出来已经过消毒了。他演奏肖邦的作品,似乎是在少有的一个晚上因稍有一点感情波动而被喝倒彩的一部巴赫作品。他演奏舒伯特这位怀旧天才的作品,就像是在听一位从不认识死者的优秀演说家所致的悼词那样。如此说来,似乎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说,他演奏的比那写着的东西一点也不多,这是真的话,那么,他演奏的一点也不少,这也是真的:而在这方面,他是最伟大的人。那音乐原来的东西一点也不丢掉。其全部给人深刻印象的力量都还给了你,这是由于他善于把完全清洗干净的东西奉献给你,没有任何个人主观的改变,你的激情是一种盲目而无限的真实性的激情:并不认识的激情。已经沉醉在梦幻之中和淹没在内在迷宫的欲望之中,最后到了波利尼的面前,发现了能够产生纯粹现实的那种潜力,只要你让它原汁原味。我发誓,那是一种激情。
后来发生了一件似是无关却有关的事情:他们发明了光盘和数字录音。无论是听还是演奏的效果完美,便突然变成更为容易和几乎必须做到的事情。对于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来说,像鲁宾逊整个一生所做的那样乱七八糟的事情来使世界着迷,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则已习惯于在音乐厅里期待受光盘教育而习惯的那种干净和准确。在波利尼身上作为独一无二的奇迹的东西,今天已变成演奏实践的必要前提。好像被集团所吸引的一位自行车赛车手那样,波利尼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宝贵的半明半暗的地位之中,继续走他的路,科学家的苦行僧之路,很少去迎合正在他周围形成的新的娱乐思想。我对他的最后的见面记忆是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演奏的一场《帝王》,我记得好像是阿巴多①在指挥台上。作为几百年都是波利尼的忠实崇拜者,我要说,我的记忆是:极为厌烦。
①克劳迪奥·阿巴多(1933…),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曾先后担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译注。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那样的结果。观众有其路数,他也继续走他自己的路。你可以打赌:他们迟早会再相见。带着这种想法,上星期天我去了斯卡拉歌剧院,去听首场马拉松式的贝多芬音乐会。我想发现多年前曾教我懂得想干净意味着什么的那位惊人的科学家情况如何。
当我进去时,跟过去是一样的,他不上台去,而是向我们跑来。这是我一直喜爱的他身上的一件事:因为当他最后再出来时,他以缓慢而疲劳的脚步这样做。但是当他进来时,他跑着来,似乎是不愿让任何人等待,或者是因为他感到急躁,我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原先和后来不一样的那些钢琴家,因为在他们身上写着:中间发生了某种事情。面孔也总是那一张面孔:仿佛是一分钟之前他们把他叫醒的,像被大灯照着的一个人,模模糊糊地毫无防卫,感到十分尴尬。他们一般来说都有那样一张面孔,而他们却是些天才。他坐在凳子上,开始忙碌着,把凳子升高,又把它降低,最后又把它放到原先的位置上。当他开始演奏时,突然一下子就开始:好像是解放了一样。
①格伦·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译注。使你吃惊的第一件东西是你听不到的那东西:过去的那种明显的完美。也许有,但事实是,再没有过去那样突如其来地让你感觉到。只过一会儿你还感觉到,那是一种基本的钢琴演奏方法:基本音调色彩少,采用一些基本强弱法,而毫无细腻的东西,毫无小游戏、点缀、魅力,仿佛是选择了一种几乎是原始的坚硬材料来加工:石头。一种石头贝多芬。然后你逐渐地感觉到,所有那没有的东西,不只是不存在,而且以某种方式被吸入了你所不曾期待的一个漩涡之中,你从开始忍受着,而后渐渐地对准了焦距:最终你看见了这个漩涡。这是一种力量的突然爆炸,它在音乐里面燃爆,并以其冲击波打击每一个音符。一个人并不习惯于想到,开头的那些奏鸣曲里面会写着这样的强度。并不是克莱曼蒂式的一些小玩意儿,而是、并且永远是十八世纪的东西。而就是波利尼,他没有动原来所写的东西的一个标点符号,只是在可能的地方加进了你无法想像的整个强度。你们看,这并不是弹奏得强点或者快点的这类平庸问题:他能使人觉得那慢速的极轻的弹奏法有一种惊人的强度。不仅是觉得这样,而且就是这样。而当他无限地加强那些音符的时候,你听到的音乐在冲击波作用下跳动一会儿,而后又立即严密组合,监管着爆炸,给它装上铁甲。真是天才。的确这是一种杂技。古尔德①(比方说)让地雷爆炸了,就在那中间,在圣母那里,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废墟。漂亮,但是废墟。而波利尼,用左手点燃导火线,用右手把铁甲大门锁上,整个儿爆炸了,但什么都没炸碎。你想想就会明白,贝多芬就是那里的那个东西。人们发现,人类本身具有十八世纪不想认识的巨大强度:当时是试验这种巨大强度,去找到它并使之爆发,但是一切都好像在一个试验室里,也就是在一种能控制的局面中,不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就像是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感情科学。
我自问,当波利尼演奏到最后的那些奏鸣曲时,也就是在那些奏鸣曲中爆炸已经不那么地下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般的听众也将能看到它。我自问,怎么样才能做到与那下面的进程同步。将于二月份发生,我将要去听。我也带着好奇心去看看是否将重新出现在听他演奏前面一些奏鸣曲时使我吃惊的第二个东西:从那黑色大动物中向我跳出来另一段贝多芬作品,我从来就没有非常清楚地看到它。这是贝多芬的呼喊。
原先已经直觉到了,而当星期四波利尼演奏了《悲怆》的时候,我就有了清楚的概念。如人们所知,以慢板序曲开始,以美妙的技巧加强。我总是觉得那是一种庄严的东西,一个设计精明的大门。我要重复说,这是一种美妙的诡计。而现在我听到了波利尼演奏打开那扇大门的那几组和弦。然后同样的那几组和弦又回到了接着演奏的刺耳的快板,这快板就像是对一个记忆的突然袭击。我以为简单地只是一些记忆。波利尼演奏它,那是恐慌,绝对的害怕:悲痛欲绝。那根本不是什么诡计:他在呼喊,被关在他的什么笼子里,监狱里,疯人院里,谁知道呢。那是优美而善良的呼喊。你再想想,你就会明白,贝多芬正是在那里的那种东西:把一种痛苦呼喊的初步经历包装在试验炸弹的一座宏伟建筑里的一个人。在那座建筑周围修建了一些主教堂,以便隐蔽它,使之合理化,以便战胜它,使之新陈代谢。但是,如果你下到教堂地下室墓穴里,你所感到的则是:一种痛苦的呼喊。我喜欢看见那位表面上不人道的、惊惶失措的科学家一直下到那下面来,让我听到那痛苦的呼喊。
今晚有另一场音乐会。还有作品二十七第二乐章,人们所熟知的《月光》:其开头便是轻而易举的激情的撞击,对浪漫垃圾的一种预言,在废糖蜜中旅行的原型装置。谁知道波利尼是怎么回事。在我看来,如果可能,他要跳过它。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严格地一个一个地演奏那些三连音,而在他把我们让掉在上面的所有矫饰都清除掉之前,就不会错过一个音符。谁知道经过反复擦亮,还会留下点什么东西。
/* 22 */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没有脸和没有害怕的人
①布斯托阿尔西奇奥,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瓦雷塞省小城,工业发达,并有中世纪建筑文物译注。
②瓦莱隆加,意大利西西里岛小城镇译注。
③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先锋派作曲家译注。整个周围什么也没有。一个随便的西班牙,也可能会是布斯托阿尔西奇奥①。巴塞罗那只是离一小时高速公路的一个假想。赛道叫做卡塔罗尼亚赛车道,四公里多点,一条没有尽头的直道。最近一次摩托车世界冠军赛,已经颁发了三项奖:二百五十毫升(明白这是发动机容量)的冠军,在罗马出生的一个人赢得它,此人二十五岁,名叫马西米利阿诺·比阿吉,人称马克斯。他原来踢足球,后来一位朋友带他在瓦莱隆加②转了一圈,他上了摩托车,他们就再也看不见他,一下加速就把他给射出去了,这加速还没完呢。这似乎是传奇,然而事情却真的是这样。他们说,他就是两个轮子的新的伟大天才。而当你问他比别人多点什么,他们回答你说:此人很坏。看上去他似乎并非如此:他的脸是你数百次亲眼所见的某些二十多岁人的脸,这些人星期六晚上是领班工头,而后,星期一便穿着白色工作服在酒吧里做咖啡,梦想着加利福尼亚。只是对他来说,一直就是星期六晚上,他真的是领班工头。我来到这里看他跑,因为人们说那是一种激情。我看到了他周围的所有一切,发现那确实是一种激情。
你感觉到的第一件东西是气味。开始时你会自问,天哪,在哪里烧糊了数公里长的腊肠?而后你搞清楚了,腊肠消失了,剩下的是烧油,但是不臭,是香的,跟橡胶和汽油稍有差别。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在你的鼻子里还有那香味,并且永远留在了记忆里。第二件强加给你的东西是噪音。谁知道凯奇③是否从来没有听到过那种噪音。他会喜欢的。并非是毫无约束的噪音,而是跳动的节奏,以优雅的强度不断地升高分贝。每个弯道都有其旋律,而每个摩托骑手都有其自己的声音。最后似乎是一个开玩笑的斯特拉温斯基①所写的一部总谱。最好的你在直道结束时听到,这里有一公里长,也就是一种无穷无尽。如果你两腿之间有一辆五百毫升的摩托车,如果你用手腕把油门加大到底,如果你贴着油箱,一直到消失,那么几秒钟内你就变成一颗射出去的子弹,时速三百公里。但是,由于最后还有一个大弯,它又把你带回到现实中来,你不能永远保持这样,你得做点什么事。那么,离终点还有二百米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像降落伞似的突然张开,力求同空气碰撞,直起腰身,双膝向外张开,伸展双臂,同时放松油门,捏住闸,希望做出了正确的计算。看起来非常漂亮,听起来更加漂亮,如果你正好在那个时刻到了离终点二百米处,靠在离赛车道三米的小护墙上。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迎面向你扑来,似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种发出嘶哑声音的喘气,而后当打开降落伞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但是那并不是寂静,而是一种声音黑洞,它吞没一切,是一种可怕的聚爆,是一种特别的声音倒转,是一种无声漩涡,它抓住你并把你扔进你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深渊。此后,相当令人吃惊的是注意到你还是完整的,靠在那小护墙上。而你还在听着。
①伊戈尔·斯特拉温斯基(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译注。在家里,在电视机前,你注视着他们,你在想:他们都是疯子。那些人在拐弯处头部只离柏油路半米,臀部在摩托车外,膝盖在赛车道上摩擦出火花。接近时速二百公里,他们像蛇一样走弯曲路线,他们不时地觉得那两个轮子也太多,于是高兴地向上仰,不用那前轮子跑。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