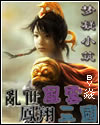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山上松柏苍翠,山前麦田开阔,坡间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小村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环境幽静,风景优美。
西柏坡正处于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从华北根据地的大城市石家庄进山,沿河岸顺大道可以直达,不用再翻山。如遇敌人进袭,后撤就是太行腹地,回旋余地很大。既交通方便,又安全可靠,中共中央选定西柏坡,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部。
中共中央书记处驻在西柏坡。滹沱河再往下流,四五里是统战部的李家庄,沿岸还分布着社会部的西黄泥村,外事局的柏里村等中央机关驻地。
西柏坡的建筑都是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土坯墙,青瓦顶。毛泽东的小院,推窗可见周恩来的邻院,西北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间屋里有三张桌子——一张作战科,一张情报科,一张资料科。周恩来说:“我们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
西柏坡虽然位于华北根据地,但是,华北根据地依然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困之中,对外交通仍被封锁。
国统区与海外的报纸进不来,中央机关的电台频繁遭遇轰炸,也许,这也是西柏坡没有得到香港详细情况的原因之一?
8.周恩来批评潘汉年
无论什么客观原因,周恩来决不允许耽误党的重要工作。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经济、妇女、青年、华侨各方人士均有热烈响应。
周恩来回顾:中央曾布置上海局与香港分局,向各方面征询对召开新政协会议、讨论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意见,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两份通电内容约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问下,迟至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它通电及宣言。
周恩来气愤:这就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乎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展,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来认为:此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证明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这批评可是够严厉的。
潘汉年其人,可以说深得周恩来器重。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改组特科领导: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特科工作,一把手陈云兼任一科科长,二把手康生兼任三科科长,三把手潘汉年兼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从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调任特科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很快完成从文化人到情报人的转变,不久又实际负责特科的整个工作,显示出特有的情报工作能力。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派人寻找红军谈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周恩来就指定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潘汉年从此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指派陈云和潘汉年去白区传达会议精神,并设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的联络。几番传奇经历,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潘汉年往返于陕北与上海之间,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之间建立联络渠道。在完成谈判任务的同时,潘汉年还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广交朋友。
1941年12月日军进占香港,潘汉年又通过情报渠道,把众多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回内地。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很早就活跃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与高层。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一明一暗,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可是,一旦延误中央极为重视的新政协筹备工作,还是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人们不由得不诧异:潘汉年其人,一向具有战略眼光,曾准确预报德国侵略苏联的日期,何以忽视新政协大事?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更有切实的体会。
据说,农工民主党一位严先生曾访问延安,把毛泽东的一封信捎到香港。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除鼓励外,也批评民盟在南京政府的压迫下自动解散是错误的,还提醒民革有第三方面倾向。
在1948年年中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政治协商的看法还远未统一。
双周座谈会在连贯住地讨论了七八次。尽管大家拥护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主张,但是,具体到新政协的宗旨、内容、参加者、时间、地点,还有诸多分歧。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
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谭平山也同意,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
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开。王绍鏊表示赞成。
李章达认为:何时召开要看形势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快固然要快,国际形势凶险也要加快。
郭沫若起初说现在讨论开会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茅盾则认为: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
定在解放区没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在关内。
王绍鏊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
李济深认为:还是拿下平津以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李章达认为李济深此见不妥: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最后反成了以军事为前提。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
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谭平山认为:任公的宽大主义甚有问题。李章达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马叙伦认为: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酢的工具。
内部讨论久议不决,外间就有传言: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另有打算!
李济深在国民党中,既有黄埔的中央军背景,又有独特的地方资源。出身广东军界的李济深祖籍广西,因此与桂系头面人物相知甚深。八年抗战,两年内战,蒋介石有意消耗地方势力,北方军阀伤亡殆尽,但是,长期处于后方的桂系却得以坐大。如今,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在国民党内,论实力,除了老蒋的中央系,就算桂系了。蒋介石虽然如愿当选“总统”,“副总统”却被桂系领袖李宗仁拿下。论民主声望,李宗仁甚至超出老蒋。而且,战局的发展,正在迅速削减蒋系的实力,于是,桂系的分量就相形加重。
近来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岂不可以把国民党中央政权一锅端?
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立下大功!
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香港的民主人士争论热烈,共产党方面与会的方方、连贯、饶彰风通常都不表态,避免使人以为共产党征求意见只是走走形式。
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
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
1948年五六月份的中国政坛,许多民主人士尽管赞同共产党,但尚未心服口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如何召开,恐怕还是众口难调。
有个在旧政协时代跟蒋介石走的党派领导人找到连贯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是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如果再不行,那也要有民社党和青年党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还说:若要他张君劢参加新政协,中共必须放弃土改!对于许多民主人士而言,谈起民主人人喜欢,谈起革命就要考虑考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农村拥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香港的新政协运动热热闹闹,但也有人是日谈政协,心向他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形成两极对立格局。1947年春夏,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苏联则于9月组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形成。有意味的是:苏联组建情报局没有邀请欧洲的希腊共产党和亚洲的中国共产党。据说,苏联并不赞成这两个党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苏联希望以自己在亚洲的妥协,换取美国在欧洲的让步。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司徒雷登喜出望外。此时美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战胜共产党。因此,美国期望以和谈方式,诱使共产党放下武器。但是美国明白,由于自己在内战调停中偏袒国民党,已经丧失对共产党的影响力。现在,苏联大使主动伸出橄榄枝,怎不令司徒雷登惊喜!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还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疑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有了这些幻想,还会积极投入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吗?
潘汉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战上。
《华商报》创刊就刊登了一幅“两‘胡’于‘途”’的漫画:
胡适背着标有“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飞奔,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一具无头军人尸体……
旁题打油诗:
“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
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3月1日复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与《华商报》配合,同《中央日报》、《大公报》打起笔墨仗。“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的道路”’等文连续发表,大力批判第三道路。
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曾昭抡、翦伯赞等人在报纸上笔谈:“假如说中间路线在1946年还只是错误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产的话,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简直变成反动阴谋的护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也许,潘汉年的失误,并非由于对新政协不够重视,而是认为,此时召开新政协时机尚未成熟?也许,潘汉年认为,当前要务是思想准备?
其实,组织准备也很艰难。
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并非人人享有自由,有些重要的人物潘汉年一时还联系不上。
致公党有两个部分,香港总部拥护“五一口号”,美洲总部却尚无态度——大龙头司徒美堂此时正在香港呢!
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拒绝参加国大,避居香港,国民党派了三个特务看着他。陈其援去找了几次,特务都不给开门。还是连贯想出办法,《华商报》的编辑司徒丙鹤是司徒美堂的老乡,派他冒充亲戚去找。
司徒丙鹤一口台山话,说是来看叔父,才见到司徒美堂老人。可是,两个司徒上街喝茶都有带枪的特务跟随。
一直混了两个多月,司徒丙鹤才得到机会,在建国酒楼为司徒美堂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司徒美堂公开表示支持“五一口号”。司徒丙鹤又为他起草文字声明公开发表。
如何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运动之中,潘汉年还得煞费苦心。
不止香港,中共上海局那边也有难处。
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胡厥文等诸多民主人士,都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很难与他们商榷新政协事项。
国统区此时不可能公然开展新政协运动,“五一口号”之后的上海,政治热潮是“反美扶日运动”。
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1947年下半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联合民盟、民建、民进、民联等民主党派成员,建立“对日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多次发表批判美国扶助日本反动势力的文章,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美国驻上海领事却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这种言论。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反而压制中国的言论自由,更激起中国知识界的反感。
1948年春,上海各大学纷纷召开反美扶日讨论会。5月4日,上海一百二十个大中学校二万多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在军警围困之中,学生们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报道,惟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谴责学生。全市学生更加激动,又于5月20日举行大检阅,发起十万人大签名。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孟宪章、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