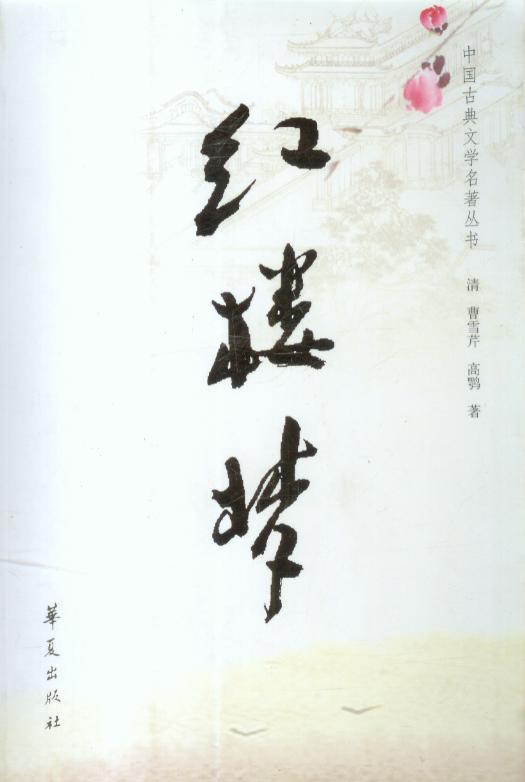追月楼-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屡作呕;喜酸;盖有喜之症候。读《彭注五代史》;萃文书局本。第三章八姑娘婉南归省亲;正赶上办慕容氏的丧事。慕容氏生前最显赫之处;便是逢到初一十五;丁老先生必向她请安。她是丁家辈分最长者。丁老先生这么做;也是为了丁家后人作表率。这习惯一直延续到丁丑浩劫之前;丁老先生不下追月楼;慕容氏也没有上楼让他请安的道理。婉回家后;大家都说丁老先生为了不能忠孝两全;在追月楼上哭了几回;跺脚声震得楼板灰尘直落。婉听了;叹口气说:“爸爸也是的;人老了;这种事难免;何必。”婉守寡已好几年。她从一个旧式家庭嫁到另一个旧式家庭;对旧式家庭的一套说不出的厌恶。她从母亲那继承了一身日本女人的好皮肤;如果不是一双眼睛生得小一些;嘴唇微翘了些;她一点不比大她一个多月的七姑娘娅逊色。大学毕业以后;按照丁老先生的意思;婉远嫁到北京。嫁过去以后;生了一儿一女;男人死了。婉的婆家旧式而不糊涂;说好了守孝以三年为期。期满了;天下的男人;随她嫁。因此八姑娘在男人死后三年回南京;上上下下都知道丁家多了一位待嫁的姑奶奶。这一天;明轩领了位西装革履的绅士;笑着往追月楼上走。丁老先生正举着线装书在读;侧过头来;从老花眼镜片后打量来者。大约是事先说好的;明轩只是站在一侧笑;不作介绍。待丁老先生疑问的眼光转向明轩;那位绅士笑道:“老先生;真认不出我了。”丁老先生白了他一眼;继续用眼睛问明轩。明轩说:“衍公;这是少荆。你看;人混阔了;就难认了。”少荆毕恭毕敬地鞠了个日本式的躬;说:“先生;学生给您请安来了。”丁老先生早想起是谁了;淡淡地说了声“坐”。男仆端上茶来;明轩半个主人似的对少荆笑了笑说:“衍公;当年在日本听先生讲学的弟子中;就数少荆有出息。”少荆笑着谦虚;问老先生这一向可好;见丁老先生脸上有些不快;忙改口把老先生的“老”字去掉。“先生;学生自东京一别;一直不曾通过音讯;实在失礼了。”丁老先生说:“我教过的弟子多呢;都通音讯;忙不过来。”少荆有些尴尬;红着脸说:“那当然;先生;先生说的是。不过;学生哪有忘了老师的道理呢。”丁老先生脸色和缓了一些。少荆本是得意之徒;虽然一个劲地委屈谦恭;仿佛短大褂罩不住长内衣;不时地要露出得意来。追月楼上坐谈了一会;少荆说:“学生这次随汪先生来南京;”一眼瞥见明轩在摇手;便改口道;“学生来南京;觉得南京是个很不错的城市。”他的思路叫明轩打断了;一时无话可说。明轩打岔道:“少荆兄;你看衍公这楼;简而不陋;朴而不俗;难道不比日本人那矮矮的木房子好。”少荆随明轩往楼下看。楼下八姑娘婉正在院子里;抬头往楼上看。明轩喊道:“八姑娘;你在那做什么?”婉回答不做什么;反过来问大姐夫在楼上有什么事;眼睛盯着他身边的少荆看;少荆也对她看。明轩作了介绍;楼上楼下点了点头;算是招呼。少荆离开丁家;向明轩抱怨说:“这老头子怎么回事;阴阳怪气的。”明轩笑着说丁老先生就这脾气;得哄着他老人家才行。少荆听了;说做他老先生的女婿也不容易。明轩说:“那是;你要做了;就知道。”两人无意中谈到八姑娘婉。少荆说:“这什么八姑娘的;人倒不俗。”明轩嬉笑着说:“怎么;少荆兄也有意做丁家的女婿?”少荆说:“丁家能要我这号人做女婿?”两人都笑。明轩回家;和婕闲谈;谈到少荆。婕说:“他那人;我爸爸肯定看不上。”明轩说:“不管怎么说;八姑娘也是嫁过人的。”婕不以为然地反驳说:“嫁过人怎么啦;你那师兄不也是风流得很吗。”明轩说:“男人和女人不一样。”话音刚落;婕光火起来:“怎么不一样!”明轩急忙声辩他不是那意思;婕说:“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什么男的女的不一样;我看你们这些死男人才是一样呢!”明轩既有些惧内;又有些烦;发狠说:“我不跟你说了;你这人强词夺理;都是你对。”婕回娘家;把她和明轩争吵的事告诉婉;没想到婉听了;一笑;不当一回事地说:“谁嫌谁呀;他要是有那个意思的话;见见面也没什么;你说是不是?”在这期间;仲祥突然从内地回了处在沦陷区的南京城。丁老先生老大地不高兴。恨仲祥放着好端端的义民不做;回来做偷生的顺民。仲祥知道爷爷不赞成自己回来;因此回来了;也懒得上追月楼听爷爷教训叹气;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他早就觉得爷爷老糊涂了;就算是不糊涂;老人家也不会理解他在外头的苦楚;更不会理解他还有一颗为了失恋而痛苦的心。他所相思的那位姑娘;一腔爱国热血凉得比他更快;嫁给了一位不大不小的青年军官做太太。国统区仿佛有许多事都不称心;工作不好找;大学又很难考上。听说去延安是个很好的出路;苦于没有靠得住的人指引。想来想去;还是回家最好。回了家;又后悔;又怨;因此便去找旧时的同学好友喝酒。他的酒量不好;一喝就醉;一醉必吐。偏偏他是个好胜的人;越是醉越要喝;喝着喝着没钱了;便从家里随便捞点什么东西;当铺里当了再喝。仲祥堕落成酒鬼的时候;婉和少荆的事有了很大进展。少荆是个尚未娶妇的鳏夫;多年来一直在外交部门供职;对付女人很有一套。这一段时间正是汪精卫酝酿重建南京国民政府之际;作为汪的心腹;少荆代表上海的汪精卫集团留守南京。在和南京的维新政府接洽之余;少荆便带着婉乘小车四处兜游。幸好有辆小车;南京本是个多名胜的地方;少荆天天晚上翻《南京指南》;然后按图索骥;把个司机辛苦煞。婉也算南京土生土长;第一次知道家乡有这么许多地方可以去见识。小汽车开来开去;婉的心也跳来跳去。少荆的岁数大得可以做她的父亲;除了这点不满意;婉实在找不出他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婉发现自己又回到大学时代;那正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季节。也许出自策略上的考虑;婉把丁老先生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上升到夸大的地步;婚事一直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婉不断扮着旧式家庭孝女的角色。这个角色使她进可攻;退可守。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在以婚姻为目的的前提下逐步进行;倒不如说是在结合不可能的幌子下发展起来。丁老先生是个借口;这个借口在婉和少荆之间筑成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在婉看来;有一种特殊的美。少荆买了架相机;出门时带着个木制的三角架;拍了许多照。婉有时也把小妙带出去做模特儿;任她随意在草地上玩耍;然后在少荆的指导下学拍照;从小小的取景框里;婉注意到小妙的一张嘴与自己的十二分相像。不知怎么的;婉一想到自己有一位可以做母亲的大姐婕;有一个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妹妹妙;便有一种堵在胸口的滑稽之感。这一天的太阳很好;到了看晚霞的时候;西边一片红;东望四处发亮。草坪上;白杨树拖着长长的倒影。小妙在树荫中奔跑;掐那草心里长出的小黄花。婉和少荆就地而坐;同靠在一株大树下;不远处是支在三角架上的照相机;再往远处歇着黑色的小汽车;坐在里边打瞌睡的司机。少荆的一件米色呢风衣扔在草坪上;婉斜眼望过去;仿佛一只忠实的狗卧在那里。少荆说了一会话;忽然告诉婉南京的国民政府就要正式成立;届时南京的维新政府和华北临时政府都得解散。“汪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在教育部干事。其实;干个次长也没什么意思。”婉说:“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我又不想做次长夫人。”少荆笑着说:“要不是为了让我喜欢的人做次长夫人;这瘟官我还真不愿意屈就呢。难道你没听说夫荣妻贵的道理。”婉咬着嘴唇说;“什么贵不贵的;谁答应嫁给你了?”少荆说:“你看;如今和汪先生一起干事;弄不好就要吃重庆政府军统的枪子;人家冒着生命为你干;你倒不领情!”婉把脸侧在一边笑。她不愿相信少荆就一定死心塌地迷上她。不过她知道少荆这样的风流鳏夫;不会喜欢那些急于想嫁给他的女人。她越矜持;越表现得若即若离;少荆才会越觉得离不开她。虽然门第对少荆是个诱惑;但婉深知自己毕竟是嫁过的女人;她得看准时机;她必须看准时机。少荆做了次长;果真忙了许多。他上任第一桩事;就是接待日本的教育代表团。代表团中有一位专攻汉学的专家;当年曾听丁老先生在东京讲过学;这次既然来中国;提出要见丁老先生。这位汉学专家叫藤冢;是个严谨而确有学问的学者。他读过丁老先生的《春秋三传正义》;觉得是本了不起的书。明轩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事不妙;少荆领着藤冢来约他去见丁老先生;他只好硬着头皮奉陪;心里奇怪少荆怎么一点不懂得老人的心。那位藤冢是位极谦恭多礼的人;见了谁都鞠躬。但是丁老先生连站都没站起来;冷冷地看着藤冢;像是一尊木雕。藤冢似乎很能理解丁老先生的心情;红着脸;露着微笑;和明轩交谈。明轩十分尴尬;一边谈话;一边用眼睛看少荆;少荆脸上有些不好看;恨丁老先生太过分。丁老先生始终坐在那里;像尊木雕。其他三位勉强坐了一会;站起来告辞。藤冢深深鞠了个躬;头低在那里足有一分钟;仰起脸来;极诚恳地说:“先生虽然一语不发;学生对先生的尊敬;有增无减。此时无声胜有声;学生告辞了。学生虽是日本人;却是认为中日不该打仗的。”说完;又是认认真真地鞠躬。丁老先生依然不动;依然是尊木雕。过了几天;少荆见了婉;直骂丁老先生是块老僵了的榆木疙瘩。婉说:“你看;到底做了次长了;就这么说我爸爸。”说着;眼睛有些红。少荆连忙说:“不是;你知道我多难做人!”婉意味深长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爸爸;是你的老师。”少荆一笑;说:“那当然;我也不过和你说说;怎么说;我也不敢得罪未来的老丈人呀。”见婉笑了;又说:“对了;我明天就要去上海;一个星期吧;你和我一起去;别忙着说不;你知道上海女人的厉害;没你在身边;我可抵不住诱惑。别拒绝;求你了;再说一遍;求——”南京一家由中央党部出钱办的小报;报道了藤冢先生和丁老先生会面的消息。消息上说;中日一流的学者握手言欢;共谈中日亲善。这条消息让明轩看到了;吓出一身冷汗。幸好丁老先生从不下楼;这事瞒着他也不难。因此上上下下地都关照;说这事若让丁老先生知道;非把他活气死不可。丁老先生曾在日记上大记特记和藤冢会面之事。和黄老先生闲谈时;黄老先生也夸他大义凛然;不失国节;士可杀不可辱;为中国人争了口气。明轩一直害怕那该死的报道让黄老先生看到。这些汉奸办的小报从来没什么人看;明轩空担了一些天的心。明轩在老派人眼里是新派;他懂外文;课堂上能穿插讲几段辩证法。在新派人眼里他又算老派;他追随丁老先生反对过白话文;把新文学骂得一钱不值。新老派之间;他力争两头逢迎;但是效果上一头都不讨好。要不是少荆的关系;他也许要到下辈子才能做教务长。事实上;自从日本人来以后;他一直处在半失业状态。每周几节课的收入;已经足以使婕轻视他;而两个儿子也比过去更不服管。教务长并不好当。和汉书院的院长内定丁老先生。书院的前身就是明轩家对门的那家小学堂。少荆的意思;是丁老先生担虚名;明轩掌实权;办一所遗老遗少风格的汉学学堂。体制上相当于研究生院;因此学生的人数不在多。明轩为了这事很难长久瞒住丁老先生;越想心里越觉得不踏实。丁老先生因为这一向明轩常上追月楼;有时也间到他外面的时局。明轩总是笼统地说“蛮好;蛮好”。丁老先生生气地说:“当然是蛮好;顺民都做顺了;怎么能不蛮好。”明轩十分尴尬;只好和他打岔。丁老先生又问:“我听说少荆常来;还说婉和他一起出去过;怎么回事?”明轩说:“少荆一直没娶过太太;他时髦什么单身;不过自打认识了婉;倒真有点迷上她了。他几次失魂落魄地对我说;他喜欢八姑娘。”丁老先生便问:“那婉的态度呢?”明轩故作严肃地说:“八姑娘的脾气;衍公还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家的子女;没你一句话;八姑娘会许诺别人?”丁老先生满意地点点头;找着机会便和婉说起了这件事。婉红着脸说:“爸爸;你别信这事;女儿怎么会嫁给他呢。我不过看少荆是爸爸的学生;才和他敷衍敷衍。我才不想嫁人呢。”丁老先生说:“爸爸不是那种死脑筋;你男人既死了;断没有死守的道理。不过少荆这人总不是太踏实;他若要做丁家的女婿;脾气得好好改改。”婉脸更红;说:“爸爸的意思;倒好像女儿真要嫁给他似的。”明轩做了几个月的教务长;惭愧得有些良心不安。和汉书院只是个领干薪的地方。不到发钞票的日子;甚至学生也懒得来。那些学生都有些来头;书院按月送津贴;毕业时再送张文凭。老师的数目几乎超过了学生;水平和脾气一样坏;动不动就骂人。比起来还算明轩干了点实事;坚持着天天去弯弯。书院凡是带长的人都介绍亲朋好友来供职;明轩便给仲祥谋了个比跑腿高;比教书低的差事。仲祥有了份工作;并不好好干;只当多了份酒钱。八姑娘婉和少荆的婚事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少荆作为情场老手;经历了不知多少姑娘;最后栽在婉手里;他买了幢花园洋房;只等着娶亲的日子到来。丁家上上下下都把少荆当新姑爷看;丁老先生对他也较过去客气。婉脸上不知不觉就流出笑来。九姑娘娈和十姑娘嫘回娘家;看着八姑娘小汽车进进出出;都怨自己嫁人嫁得太匆忙。刘氏平白无故地受了好几回气。丁老先生不知怎么知道少荆做了次长。丁老先生突然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大汉奸。丁老先生大发雷霆。丁老先生差一点气死过去。丁老先生把明轩臭骂一通。丁老先生想勒死婉。丁老先生看着丁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顺眼。又到了滴滴答答的雨季;连绵不断的大雨小雨浇得人心头说不出的烦。空气太潮湿了;仿佛用劲一捏;就能挤出水来。丁老先生在追月楼上踱来踱去;打着腹稿;表情十分严肃。他要写一篇书信体的《与弟子少荆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和章太炎的《谢本师》;在丁老先生看来;都足以不朽。但是嵇康与平辈绝交;章太炎与长辈;只有加上丁老先生的和晚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