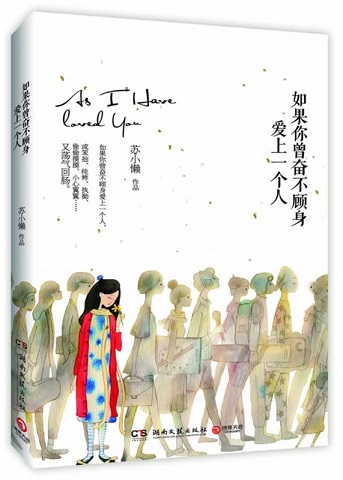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呢?她辛劳一世的报酬呢?她的钱呢?
我没法去问这个老人。这不该去问她。她的贫穷是无辜的。该自问的是我们街上 行走的每一个有钱和没钱的人。一个可以做我们奶奶的老人,贫穷成这样,我们谁能言富。
再一次经过这个道口时,那个老奶奶已不在。台阶上趴着一个脏兮兮的男人,蓬头垢面,几乎全身匐地,双手贴地伸出,不住地以头磕地,问行人讨要。我准备了零钱,但没有给他。我不同情故意作贱自己的人,尤其是为几个零钱。这是卑贱的不礼貌的乞讨者,他在用自己的身体作贱人。他让我看到人性中令我厌恶的那部分。
跋 不和你玩
亮程总是扛着一把铁锨或背着一堆柴禾出现在某一个他根本不该出现的地方,一脸疲惫地对着他荒芜了的家园。他不肯放弃铁锨或柴禾的重量,或者这也是他所需要的分量,使他不至于轻得丢失了自己。他在他的散文里布置了那么多路障:逃跑的马所留下的空间,父亲年轻有为时作为地界埋下的一块石头,熟睡的妻子(遥永无归期的妻子?),女儿脖子上因他的离家多出来的一串钥匙,花了半年修理好的却是别人的房子或者在离家时被别人修理的自己的房子……这一切路障有足够的理由让亮程迷途,尽管对他而言,道路本身就是迷失的。当他背着巨大的家乡故土的背景游荡于外时,他所感受的抑或正是〃轻〃的考验,紧紧握住的东西使我们失去了其它,而若没有紧紧握住的东西,谁来证明我们?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一个地方长久地住下去,像一颗钉子一样把周围事物钉住。这或者也是亮程说的他是〃农民〃 的意思吧。这个写诗的农民又说:〃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渴望被一个人或一些事情/永远留住……/我一生的村庄遥无地址……〃。他说,〃生命是越摊越薄的麦垛/生命是一次解散/有人走过你一生的村庄没有遇到你……〃当然有时阳光也会照在另外的一些东西上,比如说比他先老掉的房子,但这也是失去的另一面,反正有些东西老了,无关紧要无声无息地老了。它们都是我们,都是错过、丢失、逃亡和因我们的缺陷凹住的天空的雨水,缀出几颗快乐的星斗,在莫名的夜里,亮着。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海德格尔的一句话: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亮程不喜欢引用别人的话,他可以扛着铁锨在别人的城市里乱跑,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扛着别人的话偶然在他的农村里晃一圈。
北野君说亮程把沙湾一带的精气吸完了。由此不由促狭地想,这家伙,是不是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沉郁击掷中了我们之后,自己去受用看青菜是青菜,看清水是清水的清明了。
亮程用很多年的时间写诗,然后他说,散文是回过头去捡诗歌剩下的东西。我不知道对三十出头的亮程,回过头去捡剩下的东西,把诗歌留下的两边过多的空地都种满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比如说如果向前走的路还不够长,回头的路耗不掉他的一生怎么办?但人一旦背着一个想法,就能支撑他走一段路了。
关于亮程和他的散文,他自己在那篇《关于黄沙梁》中也曾说过:〃我全部的见识就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见识,我在黄沙梁出生,花几十年岁月长大成人,最终老死在这个村里;……生活单调得像翻不过去的苦涩课文,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唯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大地把最艰涩难解的章节留给这群没啥文化的人。〃
其实亮程在这段话里概述并不能说是准确的,他很简单地启用了〃艰涩难解〃这个词,想把一个村庄的生活生存概括成一篇枯涩的课文,这是所有的试图概括都要犯的斩钉截铁的错误。和亮程那种恍惚深远,若即若离,甚至不知所云里所透出的整个村庄的氛围是不相契的。有人说亮程的散文里没有城乡冲突,没有现代城市留在乡村身上的擦痕,但对几乎亘古不变的土地岁月而言,这种擦痕也只代表了某一个时代的特殊情形。亮程的野心似乎更大,他似乎想通过让时间静止的方式,以他自己来来去去行走的〃闲锤子〃的方式,切近村庄和生存这个母题。他做得貌似漫不经心却处心积虑;貌似语无伦次自说自话却是在惨淡经营。在他笔下,驴和人是缰绳两头的动物;逃跑的马肯定有他自己的和人自以为是的世界无关的事情;而人呢?正在忙着为一根麻绳大打出手,为一只鸡蛋和亲戚结仇……这些具体而细小的事情经亮程一分析却变成了:那你说他们该计较什么?坐在如此荒远而不为人知的村庄里分析东欧局势?还是讨论香港回归问题?这些天下大事哪有一件有牛啃了他们的庄稼这事更大?亮程的〃荒远而不为人知的村庄〃的村庄的封闭性似乎也不仅仅是地域使然而更像有意为之的。当人们以飞机和宇宙飞船的速度逃离一个又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时,有些东西却不因速度的改变而改变,那就是我们流传了几千年的一颗心和它所体会到的全部喜怒哀乐。这就像亮程的村庄,村庄里似有所有言而又默然无声的一切。这一切似乎都有着更遥远而意味深长的所在:逃跑的马的去向,荒野墓碑上〃冯宝贵〃的名字,从〃我〃的走向路上彻底走失的我。……然而,这〃所在〃是什么,是这个或另一个村庄?像关于所有事物的终极启问,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解答。亮程作为一个偌大村庄的冒牌农民和实际的偷窥者,他的村庄是一棵锯开的树的横切面,他指给我们看的,是那横切面上深藏不露的水纹,是水纹里静住的时间,是时间静住的生存人群小小的欢乐和更小的悲哀。是我们本身的无知和在无知中体味的世界。这种体味无大小可以界定,对此时此刻的经历者,所有的事都是大事。
说起亮程诗歌散文里的节奏,亮程总喜欢拉上乡村牛拉车行走在泥路上的场景支撑自己,似乎他的那种缓缓的语调完全由牛拉车来负责。但我却以为是有意为之。那种缓慢,那种漫不经心,像一个人没事沿着千年的土路走,有时脚落在自己的脚印上,那从容的样子,拉长了时间,似乎时间是不过去的。记得第一次见亮程,他在一群热火朝天的文学青年中正朗诵着他的《寂静家园》:〃我看见你们走过家门/不知几更了/我看见你们/在依稀的星光下边走边朝后望……〃。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朗诵的声音是从一个远远的地方找到了亮程的身体,然后再从他的声音里走出来。那一刻,我看到亮程喜欢用的一个词:很多年,村庄悄无声息……在这种悄无声息里,亮程的诗和散文延伸成我们和他的村庄的一种通道,用〃很多年〃这样的天空低低地笼罩着。
比起以往的诗,亮程的散文里出现了一些细节,出现了一些带着个体生命色彩的小心翼翼的温情,在长散文《一个人的村庄》里有一个藏钥匙的细节:我把钥匙压在门口的土坏下面,我作了个记号给你,走出很远了又觉得不踏实,你想想,一头爱管闲事的猪可能会将钥匙拱到一边……;一头闲溜的牛也会一蹄子下去,把钥匙踩进土中;最可怕的是被一个玩耍的孩子捡走,走得很远……这甚至可以算深情的担忧只让我感到心酸,是对生存本身的不确定,还是面对普通人琐细碎小却处处可见恐惧汇成的一生?这种痛像一枚尖尖的针,深深地陷进一生的肉里,无痕无迹的,想说,也说不出名姓。而亮程说出来了,这是让人欣慰的。亮程的细节里还有一个门楼:父亲修好了大院之后,任重道远地把修门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很小,他以他那很小的年龄自以为修了一个很大的门了,以后一看,门还是太小了,这小院门一直影响着他和成长。成年后的他为自己的院子修了个很大的门,院门修好后他特意把父亲接来,他想让父亲看看这个院门够不够大,可是这时候,门在父亲生命中已变成另一种东西了这门,已和他无关。
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说,卡夫卡是给当代人指引痛苦的人。亮程展开他的村庄和他关于村庄的思考似乎要立志为我们这个时代指引〃无知〃:我们对他的村庄的历史一无所知,永远不知道这堵墙是谁垒的,那条渠是谁挖的;不知道亮程屋顶上那片天气,那窝子空气,怎么被他吸着吸着,就有了他的气味和温度,从此变成他在一个地方长久住下去的理由。就是好不容易认识些驴狗马的,亮程却又说,狗对自己的忠诚和怀疑与年俱增,它化一辈子时间都弄不清岁月变幻和喜怒哀乐中哪一张面孔才是真正的主人;而卑微的驴也许正给人的世界一个参照,好让人在驴背上看世界,也好让世界从驴跨下看你;马自然还要高贵些,尽管骑马飞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了亮程的村庄,但马的存在肯定有它的意义的,马从来就不属于谁。而人却也有人的办法:吃马〃我们用心理解不了的东西,就这样用胃消化掉了〃。亮程还说: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
那〃丰收〃这类我们所习惯了的好事在亮程那里也变成了对人某种意义上的掠夺:(他们憧憬着丰收)〃剩下的岁月,可以啥也不干呆在家里。往往是今年的收成还没吃上几口,另一年更大的丰收却又接踵而来,排着大队往家里涌。人们忙于丰收忙于喜庆,忙得连一顿好饭都顾不上吃,一村人的一辈子就这样毫无余地地完蛋了〃。这种异乎寻常的叙述让我们感到智慧,新奇好玩还有荒谬。亮程是把镜头拉得很长去看的,是在别人匆匆忙忙往前赶时以往回走的方式看的,此时此刻的一切意味深长和惊心动魄便显出了它的渺小和细致,显示出它的细致和跃动,显示出意义和荒谬的相互叠加,互换位置,也显出了很多年,显出了很多年的事,都有是一件事被悲哀和快乐以及对幸福的渴望掠夺了的人的一生,村庄的一生。亮程的散文是他一个人的村庄,也是他指给我们看的村庄的后脑勺。
当然能指给我们看这后脑勺的人是足够智慧的,这有时不仅仅是读者所沉缅的智性,似乎也成了亮程的一种爱好,他确实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他给我们挖了一个坑后还不想走,就又开始讲映进坑里的阳光以及意义,甚至有些乐此不疲。这不由使我想到傅雷评价张爱玲的一句话:聪明机智成了习性,也是一块绊脚石。这些我是不懂的,我只是单纯地喜欢着亮程的聪明,希望他更聪明。
让一个城里的五谷不分的人评头论足一个村庄其实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好在亮程已把村庄的大致轮廓沟勒了出来,种地时也留好了路,让人们日日朝那进而望,也让人们走进走出。我能做的便只有胡扯了。
亮程也挺宽容,他说:〃胡扯吧!〃
1996年6月6日
先 父
一
我比年少时更需要一个父亲,他住在我隔壁,夜里我听他打呼噜,很费劲的喘气。看他躬腰推门进来,一脸皱纹,眼皮耷拉,张开剩下两颗牙齿的嘴,对我说一句话。我们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他坐上席,我在他旁边,看着他颤巍巍伸出一只青筋暴露的手,已经抓不住什么,又抖抖地勉力去抓住。听他咳嗽,大口喘气――这就是数年之后的我自己。一个父亲,把全部的老年展示给儿子。一如我把整个童年、青年带回到他眼前。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这个过程中儿子慢慢懂得老是怎么回事。父亲在前面趟路。父亲离开后儿子会知道自己40 岁时该做什么,50岁、60岁时要考虑什么。到了七八十岁,该放下什么,去着手操劳什么。
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我活得比你还老的时候,身心的一部分仍旧是一个孩子。我叫你爹,叫你父亲,你再不答应。我叫你爹的那部分永远地长不大了。
多少年后,我活到你死亡的年龄:37岁。我想,我能过去这一年,就比你都老了。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我会活得更老。那时想起年纪轻轻就离去的你,就像怀想一个早夭的儿子。你给我童年,我自己走向青年、中年。
我的女儿只看见过你的坟墓。我清明带着她上坟,让她跪在你的墓前磕头,叫你爷爷。你这个没福气的人,没有活到她张口叫你爷爷的年龄。如果你能够,在那个几乎活不下去的年月,想到多少年后,会有一个孙女伏在耳边轻声叫你爷爷,亲你胡子拉查的脸,或许你会为此活下去。但你没有。
二
留下5个儿女的父亲,在5条回家的路上。一到夜晚,村庄的5个方向有你的脚步声。狗都不认识你了。5个儿女分别出去开门,看见不同的月色星空。他们早已忘记模样的父亲,一脸漆黑,埋没在夜色中。
多年来儿女们记住的,是5个不同的父亲。或许根本没有一个父亲。所有对你的记忆都是空的。我们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你。只是觉得跟别人一样应该有一个父亲,尽管是一个死去的父亲。每年清明我们上坟去看你,给你烧纸,烧烟和酒。边烧边在坟头吃喝说笑。喝剩下的酒埋在你的头顶。临走了再跪在墓碑前叫声父亲。
我们真的有过一个父亲吗。
当我们谈起你时,几乎没有一点共同的记忆。我不知道6岁便失去你的弟弟记住的那个父亲是谁。当时还在母亲怀中哇哇大哭的妹妹记住的,又是怎样一个父亲。母亲记忆中的那个丈夫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你死的那年我8岁,大哥11岁。最小的妹妹才8个月。我的记忆中没有一点你的影子。我对你的所有记忆是我构想的。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父亲,通过母亲、认识你的那些人。也通过我自己。
如果生命是一滴水,那我一定流经了上游。我一定经过了我的祖先、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就像我迷茫中经过的无数个黑夜。我浑然不觉的黑夜。我睁开眼睛。只是我不知道我来到世上那几年里,我看见了什么。我的童年被我丢掉了。包括那个我叫父亲的人,
我真的早已忘了,这个把我带到世上的人。我记不起他的样子,忘了他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