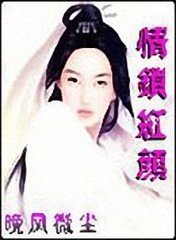无语的爱情-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天的时候,楼道里总是阴阴的。甚至有点伸手不见五指。因为黯淡,所以也免不了让人觉得怕。尤其在上课半途中回寝室拿东西,你揣着你的希望奔向8幢,可那迎面扑来的阴黑总是冲淡了你本鲜艳的心情。于是独自一人的你更不安起来,尤其你就被那黑包围着。于是你急急的开门,然后如释重负地冲出8幢。
只有在初冬的雨季,当和一大群同伴哆嗦着下课回来,才会觉得8幢的好——那城堡般的厚实似乎挡住了冬天的严寒,而给予了你一个家的感觉。老8幢的红,也使人想起“风雪夜归人”的诗意,想起雪夜小红炉上煎茶的温馨。
挂在一楼顶铁丝上的总有长短不一的衣服,一如某位宋朝词人的长短句。我喜欢这些变幻着的长短句,它会稀释你的离愁和惆怅,给你以生活的动力。
8幢虽阴黑吧,但它毕竟是我们的家!8幢无疑是一位年长的老者,虽曾心浮气躁过但如今也安详起来。还是挺偏爱她的红色外套,一如无意间听到了一首老歌,亲切、感动。
8幢也好比外婆的旧外套,闻闻它上面强烈的透出箱底的樟脑味,你也许会想起,在某个陡冷的日子里,你穿上它时心底会沁出的阵阵温暖,丝丝感动。
第八部分:少女的祈祷最初的感动(1)
成千上万的花朵散发出满世界的芬芳与温馨,那种甜美的香味让人想起一段最纯真的友情,它并不那么浓烈,但却那样幽雅,那样持久,那样刻骨铭心。
据说,有着七个花瓣的格桑花是幸运的花。金秋十月,它们又像赴约似的纷纷扬扬来到高原。成千上万的花朵散发出满世界的芬芳与温馨,那种甜美的香味让人想起一段最纯真的友情,它并不那么浓烈,但却那样幽雅,那样持久,那样刻骨铭心。
“我好喜欢它,明年我一定还来,嗯,还要把琼瑶他们也带来。”她坐在素净的病床上用带着磁性的声音说。
可是格桑花儿来了三回,她却没来,她失约了,永远的失约了。我看到格桑花瓣大瓣大瓣的滴落,像一滴一滴粉红的泪珠。
为什么美的东西总消失得这样快?
我是在一月五日早晨知道她自杀的,那天早晨9点钟太阳还从云层里爬不起来,我就知道上班不会有好事,觉得心里凄凄惶惶的。
果然,还在走廊上陈医生就满脸哀伤的样子向我走来,说:“三毛自杀了。”我不相信,睁圆了也曾是在这地方睁圆的眼睛,那天是听说:“三毛来了。”
她总是让我不能相信,说来就来了,说走就走了。然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存在又让我不能不相信。我用手捂住胸,觉得好心痛,可分明感觉到十指和手掌还留着我给她按摩过后的余温;书桌上她托人带来的书,字迹还未干,给我的那对尼泊尔耳环还明明珍存在书柜里……怎么就能走了呢?永远地走了呢?她与格桑花的约定呢?唉,我这个签约人呀,真想拿出充分的权利命令她好好地回来。
三年了,每每想起她,我心里只有一份慰藉,她一定在另一个世界,带着美丽的格桑花环赴了约,你看,今年的格桑花开得多好。
九月七日,我一接班就被告知:“五床是三毛,肺水肿。”“三毛,台湾的?”“对。”“三毛,她不是在撒哈拉沙漠和那群会哭泣的骆驼中吗,又到了这高原?”直到穿上工作服时,我才相信这不是我昨晚做的梦。
远远地,看到一个浓眉大眼,高大结实的小伙子走过来。他叫董天林,是三毛所在日光宾馆的副总经理,也是她在藏期间的全陪。
“小姐,能找块胶布吗?她鼻上的导管总是掉。”
“哧拉!”我很专业地撕下胶布,随他到了五床病房。
一个瘦小的女人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于是显得越发的瘦小,只是那一袭雪白的床单映得那头浓黑的头发异常地浓黑。左手滴着点滴,右手扶着鼻导管,旁边的氧气瓶咕嘟咕嘟的开到大容量,一副憔悴疲惫的模样。孤独就像这床棉被,紧紧裹着她。我的脑海里闪回了一下耶稣受难图。这就是三毛,是我那中学同学上课也埋头读她撒哈拉故事的三毛。
我轻轻地用胶布按“V”字形把鼻导管固定在她鼻翼上。她睁开了眼,很重很重的睁开。并把手缩回了被窝,我看到被单一阵滑动到胸前隆起。
量了体温(39℃,血压P18/12)稍高,我知道这是高原反应。
“我会死吗?”她轻轻地说。
我说:“不会的,很多人进来都会有这种反应,把发烧控制下去就好了。”
“她能吃点东西吗?”董经理小声地问。迷蒙的眼里透不尽的关切和焦急。
我说可以,然后就到小灶吩咐小张他们准备些稀饭之类好消化的食物。
小张似乎大半天也没出去,就是等这个吩咐,一转身跑进了厨房。我觉得今天上班的人都很沉默,脸上挂着神圣。连平日爱跑东跑西的小张也严阵以待了。
等我一个钟头再去时看到她精神好了许多。
“小董啊,你知道我钱包放哪的吗?哪,我一直放在胸前这个包里。”她疲惫的脸上有了孩子般的笑容,宽大的床,让我产生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此时外面的阳光直直的从窗口射进来,有一抹抚在她略显憔悴的脸上,像上了一道彩光,显得精神了不少。但我却仿佛看到她灵魂深处的泉眼已像撒哈拉沙漠那样枯竭和疲惫。
“小姐,你坐吧。”她笑着说,小董也很客气地给我端来椅子。
我说我不坐,习惯了站。
她似乎对当兵的很有兴趣,转问我什么时候入的伍。“哇,三年了!”我想起她写的那篇《两个老兵》,也许她们那个时候兵都挺老吧。
她问得很多,很细,时时发出一声声惊叹,像一只只放飞的鸽子,很美丽的一声“哇”。
这时阳光送来格桑花儿的缕缕清香,灿灿的,暖暖的,我感觉像一个梦,梦中总以为过了很久很久,其实时间很短,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已像三位久别的老朋友那样谈着各自分别后的经历了。
当然,我们多是听她在讲,她的声音很慢,很有节奏,像泉水一样缓缓流淌着。
“我就知道我要有劫难,在布达拉宫拜药王神的时候,我就感到一阵冷风,忽然觉得身后有人,我向后看了看,什么也没有了。”
她绘声绘色地说,说得我们也感觉身后有人了似的睁大了眼晴。
我发觉她是一个很相信灵异的人,她说她看到了她祖母,祖父,爷爷奶奶,还有荷西。“真的。”她的眼睛像一个惊叹号,我们不由点了点头。
第八部分:少女的祈祷最初的感动(2)
下午四点我下中班了。一人呆在寝室里,很想去看她,但想想去的人一定不少,也就克制了自己。推开窗户,夜寂静地永恒着。我想,这就是对尘世繁琐纷乱的最好安慰了,和煦的夜风吹来,今晚她一定能睡好。
晚班应下午六点半去接,还没到六点,我就收拾好了上夜班的东西。
她似乎一直在等我,一见我进来很是高兴,拉着手说:“怎么这么久没见你了嘛。”我很想说我也好想你,可我没说出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以前我很反感别人搞名人崇拜(这也是我克制着不来的原因),但她是我的朋友呀。
像被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忙完了夜班护理工作,我就不由自主地来到她的病房,坐在她身边。
今天她的气色好多了,而且化了淡妆,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得整整齐齐,昨天在发际的两三根白发也不见了,显得年轻了许多。
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一双清炯炯的黑眼澄澈得像秋湖一样,目光犀利,是可穿透现实的面幕而看到精神空灵境界的那种。
“成都,成都是一个好地方,小吃特别多,人也特别好。那天我一人在一个小饭馆吃饭,几个中学生在大家凑钱打平伙,看着特可爱的样子,我就悄悄地替他们付了款走了。”她很豪放地说着。
“还有呀,那天我在你们成都那条街上,看到一位老大爷蹲在地上卖书,我开始说帮他卖他挺不相信地看着我,看到我拿了钢笔签上名还很好卖,一下围了许多人,把他高兴得直笑。”她很开心地说着,脸上越加放出了许多光彩。
这时,我才觉得她的出色不是漂亮,而是善良。善良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它使女人的脸上蒙上一层圣洁的光环,看上去格外动人。例如菩萨,例如佛。
小董突然想起,昨晚三毛一晚没睡好,腰痛,问这里有没有按摩师。
我说专门的按摩师没有,业余的倒还有一个,家母天阴下雨也时时腰痛。都是我按摩。
“太好了,”她很高兴,一下翻过身来,很规范的趴在床上。
我只有硬着头皮上了。平时在母亲面前很自信地这套业余按摩技术,现在在她面前倒有点犹豫,毕竟没有专门训练过。
“很好,很好。”她很懂心理学似的鼓励着我。我越发有了兴致,感觉到她的身体温温柔柔的又不乏一种刚劲。我又想起这就是三毛,就是我那中学同学埋头在课桌上读那撒哈拉故事的三毛。人生只是个机缘巧合呀。
“好了,别累着了你。”她叫着,“太舒服了,”她感激地看着我。
我觉得心里很高兴,医生护士为病人减轻痛苦都是全力以赴的,何况我们还是朋友呢。
不知不觉已到两点,我想起了我的职责,说赶快熄灯睡吧,高原反应一定要注意休息的,她很听话的躺下了,我熄了灯和小董出来把她一人又留在了黑夜里。
第二天我去时,她已坐在窗前沙发上了,穿着紧身牛仔裤和一件宽松薄毛衣,轻便鞋,手里拿着一支摩尔,一副潇潇洒洒走天下的派头,我想这就是真正的三毛了,她又很成功地把自己的懦弱掩藏在这副满轻松的外衣里,脸上荡漾着微笑,似乎随时都准备着去理解和宽恕别人,无拘无束无怨无恨地像一个风筝。
风筝总是在空中飘飘荡荡,有时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心中一定好凄惶,但下面看的人总觉风筝好自由,好随意得像一个王子。
病房里有几位医院的护士慕名来找她签名题字,热热闹闹的围了一屋子,她很爽快的签着,和她们闲谈着,看着我进来了微笑着招呼我坐。
小董过来告诉我,三毛决定明天回内地了。
我迫不及待地等这批人走了后问她,能不能多呆几天?
她满脸抱歉的样子说:“不行呀,这次行程安排挺紧,不过,我明年一定还来。”她看着桌上我采的格桑花,似乎在对花儿又在对我说:“西藏很美,我一定还要来,还要把青霞和琼瑶她们都带来。”
我记下了这个约定,我想,格桑花儿也一定记下了。
小董拿出像机说:“给你们合个影。”
这一晚,我们说了很久很多,她告诉我当作家的艰苦,“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好,每月还有工资,我是不写就没得饭啦,所以只有写,很苦的,赚了稿费我就出去旅游,用完了又回来写。”
我知道她已走遍了地球上50多个国家,艰辛而虔诚地读着大自然这部人类最伟大的书。也为许多学校和灾民捐赠了不少资金,只是她自己一直过着很俭朴的生活,所以也养成了吃东西很少很随便的习惯。
她是不吃早餐的,只是抽烟很厉害,一支接一支的不停,袅袅香烟让她很兴奋,说到大陆出版她的书很是气愤的样子。“他们也不经我同意,选的照片印出来太得罪观众,我在台湾香港出的书很精美的。”看得出她还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怕大陆读者看到扉页上的照片说:“三毛好丑。”
缭绕的烟雾,早已变成一支珠笔,在她脸上写尽了感伤的心事。往事不肯落叶,总是青青葱葱。她讲了许多事,提了许多人名,只是没再提到荷西,她的最爱。我知道那是她精神的源泉,女人的心就像一匹野骆驼那样耐饥渴,只要有了爱情的承诺抑或对爱情的追忆,它都不会枯槁的。
第八部分:少女的祈祷最初的感动(3)
烟灰缸已满了,月亮也不知不觉升上了中空,高原的月亮总是像银盆一样圆得格外动人,像一个人的生命,出生,死亡。
我说:“明早我要送你。”她说五点的车,早晨太冷,别来了。我没说话,回到宿舍上床前把闹钟调到了四点。
早晨的确很冷,从来没有过的冷。周围漆漆黑黑一片,到病房时门还没开,为了不打搅值班护士我就绕到她病房窗台前。
病房已亮着桔黄的灯,像这夜里唯一睁着的一只不倦的眼,生命能这样永远不倦地亮着多好。
“三毛——”我喊了一声,窗户很快打开了,她扑到窗前,小董也伸出头轻声叫着:“等一等,我去给你开门。”
我手上拿了一只绢做的白玫瑰,这是毕业分手时一位好得要命的同学送的。我踮着脚送到她手上。她接了跑过去拿着一副硕大的银耳环对我说:“这是一位印度最好的朋友送的,我走到哪都一直带在身边,很是心爱的,把它给你留着纪念。”我接过来握在手里,看着小董还没开成门,她把身子扑在窗台上说:“外面好冷,我拉你进来吧。”窗台好高,我踩着墙沿,借着她的力连拖带爬地进去了。做了一次墙上君子。两人都为刚才的果断和勇敢像孩子般大笑,特别是外面小董在门口平台上叫着:“小高,小高,咦,人呢?”我们更是大笑不止了,她扑到窗台上压低声音叫着:“进来了。”
小董进来时,她正把那只白玫瑰插在她那红色旅行背包上拍照,一个很有诗意和很浪漫的画面,我想只有她才会有这么快而丰富的灵感。
我们忙着又把东西顺理了一遍,却没有说话,燃完一只烟的功夫外面就响起喇叭声,这是日光宾馆的三梭车,我和小董一人帮她拿了一个包出门,走到门口她又回头看了看刚才还充满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