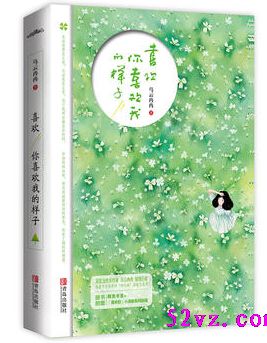刀子和刀子 作者:何大草-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 麦麦德的孩子
如果我告诉你,虽然我是女孩子,可我的吉祥物是一把刀子,你不会吓坏吧?哦,我已经从你的眼里看到了惊讶和不安。是啊,女孩子的吉祥物应该挂在脖子上,一串珍珠、一颗玉坠、一只十字架,或者是一张小男人的小照片……可我不是的。我的刀子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那种真正的刀子,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出鞘时带着不易察觉的风声,有金属的酸味,就像是淡淡的花香。换一句话说,我喜欢刀子,如同一个花痴迷恋着花朵。事实上,在我的故事里,很多时候也总是有花的,只不过当花枯萎的时候,刀子还在花丛里闪烁着安
静的光芒。泡桐树老了,南河干枯了,瓦罐寺坍塌了,可我还是我,刀子还他妈的是刀子啊。
十二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把刀子,十八岁的时候我有了另一把刀子。
两把刀子都是生日的礼物。
十二岁的刀子是土耳其的弯刀,十八岁的刀子是德国的猎刀。至少陶陶送我猎刀的时候,他说是真正的德国货。
那天窗外落着雨水,窗户上粘着雨珠,雨珠就像电影里俗得发腻的眼泪。陶陶牛高马大,蒲扇一样的双手捧着刀子,刀子用红绸缎裹着,裹了一层又一层,在十八只蜡烛的照耀下,就像他的双手捧着一滩鲜血。我把那家伙接过来,掂了掂,就知道是一把好刀。红绸缎一层一层地解开,刀子跟个婴儿似地躺在里边,又嫩又亮,亮得透明,也亮得扎眼,弧线那么优雅、柔和,却千真万确是一把好刀。刀子看起来甚至就像可怜的小宠物,而其实正是刀刀可以见红的猎刀。刀身有一尺长吧,还凿着细如发丝的凹槽,我把它握在手里,就像握着了一束阳光。刀把上缠着一圈一圈的铜线,金黄色的铜线,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只有我的手才晓得,它其实是那么的冰凉。在刀把和刀身之间,横着弯曲的挡板,挡板上刻着一只狼头,白森森的,却睁了眼睛在睡觉。我亲了亲狼头,用刀把大蛋糕切成了一十八牙。刀子是真他妈的锋利呢,它剖开蛋糕就像剖开一汪清水,蛋糕的剖面非常的光滑,光滑得好似小美人的脸蛋。
我一手拖了刀子,一手圈了陶陶的颈子,在他的耳轮上“吧”地亲了一大口。陶陶很高,为了受我一亲,他得俯下身子,这就叫你们说的那个屈尊吧?我说,谢谢陶陶。
陶陶屈尊地笑了一笑,他笑起来也就是把嘴角歪了一歪。他说,风子,风子你喜欢就好。陶陶是我的同班同学,是我喜欢的男孩。我看他,他看我,两情相悦,彼此顺眼,都不是问题孩子。什么是问题?有问题的人看没问题的人,不也全成了他妈的有问题?
噢,那一天是过去多久了?想起来,那一天的雨水淋在头上,好像还没有风干。
是的,我是愿意和你谈谈我的故事,谈谈我的两把刀子,可你千万别拿那种眼光看着我,就像东方时空的主持人,看着一个问题女孩,万分关怀也是万分痛心的样子,刨根问底要弄出点什么启迪青少年。别这样,拜托你,你真的别这样,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随便谈一谈。就像在茶楼里喝茶,或者在南河的堤坝上遛达,很随便当然也是很正常地谈一谈。噢,是的,谈一谈,因为我很怕“谈心”这个词,谁只要说要跟我谈谈心,我立刻就要晕死过去的。很久以来,我都难得开口说什么话了。尊口免开,这个词,我没用错吧?哦,错了,那就错了吧。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很久不说话了,我的嘴巴都要发臭了,看来的确是应该跟谁谈一谈了。就像把下水道的盖子揭开,敞一敞吧。跟谁谈呢,最好就是你这样的人吧,跟我素昧平生,不知道我的过去和我的今后,只知道我就是我说出的那一堆东西。那一堆东西里边有诚实也有谎言,当诚实多于谎言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肉馅很小的包子,虽然不上口,却经得住饿。可当谎言掩盖住诚实的时候,它就像一杯浇了冰激淋的非洲黑咖啡,在舔去了甜蜜之后,苦得你发慌。你别笑,我哪懂得什么哲学,哲学不是我这种人能谈的,也不是一个女孩子该谈的,对不对?我只是打了一个比方,用这种方式先谈谈自己,也许就说明我还是很正常的吧。
真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一个问题女孩。你也别拿什么问题来难为我,更不要让我接受什么心理测试了,发问卷、填表格,诸如多大年龄、什么血型、属于哪个星座、有何特长、暗恋偶像、是否失去过贞操等等等等,那完全一个傻瓜的感觉。当然,我晓得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傻瓜的世界,对不对,到处是傻瓜相机、傻瓜飞机、傻瓜明星、还有傻瓜的男孩和女孩。就连奔四十的男男女女都自称“男孩”、“女孩”,嗲得让人发腻。满世界都是傻瓜,可傻瓜堆里也就一个家伙是伟大的,那就是阿甘,也就是所谓的弗雷斯特·冈普。这是我们亲爱的英语老师宋小豆告诉我们的,她说,是弗雷斯特·冈普,而不是阿甘。她还是我们的班主任,经常用中英文夹杂着骂我们是地道的傻瓜,却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冈普。她随手在黑板上写了一行英文,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洋码儿,因为这是她对我们的梦想,Forrest Gump,她说,是冈普,冈普现在都成了天才的别名了。她冷冰冰地说,不要怪我骂你们是傻瓜,我是做梦都希望高二·一班出一个冈普。
哦,可我真的不想成为冈普,或者那个更为知名的阿甘。我也不喜欢跑步、打乒乓,或者捕鱼捞虾。他的绝活是跑步,可是他跑那么快有屁用呢,他爱的女人还不是赶在他前头死掉了。我就算是傻瓜吧,我也想做个正常的傻瓜。正常的傻瓜就是傻瓜,跟天才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傻瓜,就读一所最稀松平常的中学,每天以无所事事打发漫长的时光。好在我的运气不错,期末只有两三门功课需要补考。这就是说我还算规矩,没有傻到逃学旷课,背了书包学三毛大街小巷去流浪。我说的三毛是头上只有三根毛的小叫化,不是你们喜欢的那个长头发女人。她的书我没有读过,写字的书我读起来都累得慌。我过去只喜欢漫画、连环画、卡通片,现在甚至连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边去了。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毛病,到了什么年龄就该用什么年龄的方式来说话,对不对?前年我在贵州遇见一个东北女
孩,她满口半生不熟的贵州话,我说你搞什么名堂,是东北人就说东北话嘛!这一回她是说了东北话,就是赵本山那种哭兮兮的东北话,她说,咋的呢,走啥山上唱啥歌儿呢!我一下子笑起来,笑得半死,我想起课本上毛主席的话,叫做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就说,真他妈有意思,你简直就是打东北腔的毛主席啊!她笑起来,用贵州话说,啥子格毛主席嘞,我是正常的女娃娃嘞。
哦,你听,我们都是正常的女孩子啊。但有些家伙偏偏说我不正常,就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是刀子。
哦,一开始我就说过了,我的吉祥物是刀子。仅仅是刀子。可在一个所谓正常的世界里,女孩子是不配喜欢刀子的,你说对不对?可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像我这样的傻瓜,是啃着连环画长大的。我最怕别人跟我罗嗦什么琴童、画童,还有贝多芬、莫扎特、毕加索,我们哪配提他们呢,提了都是糟蹋圣人啊。我读的第一本连环画是阿拉伯的故事集,勇士麦麦德为了向人证明他的勇气和诚实,就把一把刀子插在了自己的脚背上。那只光秃秃的赤脚塞满了满满一页的画面,连刀把都冲到画框外边去了,血顺着刀刃往上冒,把寒冷的刀子都烫弯了。我觉得那刀也像穿破了我的血管,把我的全身都烧烫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上刀子了。
勇士麦麦德,又叫做沙漠中的麦麦德,他骑着单峰骆驼,披着长长的白袍,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明明还是很年轻的男人,眼睛里却全是苍老的感情。我要是能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也是苍老、嘶哑的吧。麦麦德最爱说一句话,这可怜的人啊!在勇士麦麦德的眼里,穷人、富人,朋友、敌人,都莫不是可怜的人呢。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句话,可不知不觉的,我也老把它挂在了嘴边上。我就想,我们都真是他妈的可怜人吧,可谁又在可怜谁呢?
我是看着麦麦德的连环画长大的。如果把这些连环画加起来,可以塞满几口大皮箱子。但是,它们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我是一个跟书没缘分的人,到手的书,都随看随丢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课本在期末总有一半找不到了。是啊,我就想,我对麦麦德尚且如此,何况是狗屁不通的课本呢。
小学的时候,为了我期末总有补考,妈妈没有少扇过我的大耳光。后来,妈妈就不再打
我了,因为我比妈妈还高了,高出一个头了,我上高二了。那一回妈妈朝我举起手来,我一把就把她的手抓住了。我说,妈妈,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了。我使劲掰住妈妈的手腕,我说,妈妈,你真的别碰我了!妈妈的眼窝里淌出泪水来,她说,我没有白养你,你的手真是有劲了啊……从那以后,妈妈再没有碰过我了。
爸爸是从来都不打我的。即便是看着我成绩单上一半的不及格,他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的。我所知道的爸爸,是没有脾气的爸爸。他看着我时的表情,总是露着微笑,再加上一点儿歉意。爸爸总是给我尽可能多的零花钱,我就用其中的一大半买了麦麦德。爸爸知道我喜欢沙漠,喜欢麦麦德,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就用草绿色的床单把我裹起来,他裹得那么耐心、细致,我从没有看见爸爸这样一丝不苟地做事情。床单裹住了我的头、大半个脸、脖子、身子,最后拖在粘着落叶的湿地上。湿地上墁了青砖,还长着青苔。爸爸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我的头是微微埋着的,这使从床单中露出来的眼睛有些上翻,有了那个年龄少有的冷漠和阴郁。哦,其实我并不阴郁和冷漠,至少,我没有扮成麦麦德的时候,我看起来是多么热情和外向啊。
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傻乎乎地想,要是别人问我,你是谁的孩子啊?我就回答我是麦麦德的孩子啊!可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唉,从来没有……我的回答也就在肚子里边烂掉了。
我过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隔着蛋糕和点燃的12根红蜡烛,递给我一把土耳其的弯刀。这就是我的第一把刀子,刀身歪曲着,就像一把镰刀,也像一个苍老的老人。我拿手试了试,却试不出锋刃。但是爸爸告诉我,弯刀的锋刃是力量,弯刀加上力量,可以切断骏马的脖子。那时候我还听不懂爸爸的话,当然,那些话里可能根本就没有话,一把弯刀,就是一把弯刀。弯刀的刀柄上镶嵌着宝石,红红绿绿的宝石,刀鞘是鲨鱼皮的,或者是鲸鱼皮的,谁知道呢,反正带着海洋的盐渍味,上边还烙着虫子一样的阿拉伯文。把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它真被麦麦德白晰的手指抚摸过。我把刀挂在墙壁上,早晚都看不够。有一回我还把弯刀带到学校拿给同学看,我说,我爸爸是少将,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武官。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其实我一边说一边在想,我是他妈的快吹破牛皮了。我爸爸是什么少将武官!只是一座军需仓库的副股长罢了。那仓库远在南线的丫丫谷,离我生活的城市隔着天远地远,坐越野吉普也要跑三天两夜呢。我那张模仿麦麦德的照片就是在丫丫谷的营房拍的,背景是百八十座碉堡一样的仓库,仓库后边就是被雨水淋湿的群山和森林。我也把这张照片拿给同学们看过,我说我是去土耳其探亲时照的。我说,那儿靠近土耳其的南部边境,是麦麦德的出生地。其实,那刀跟麦麦德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爸爸的一个老战友送的罢了。这个叔叔早就转业了,多年来在新疆——哈萨克斯坦一线跑边贸。
我的确是吹牛了,可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在学校里,同学们为了争面子,哪个没有撒过这样那样的谎呢,告诉你吧,我们全班同学的家长都是有头有脸的,有的是工商局的局长,有的是刑事法庭的庭长,有的是“太平洋百货”的老总,最臭的也是揣着持枪证的警察……可我心里雪亮,全是些鬼话。在这种事情上,说真话的是傻瓜。真正的傻瓜,和天才的弗雷斯特·冈普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稍稍聪明一些,你就晓得说你爸爸是下岗工人,也没人给你捐献希望工程啊。
我的十八岁生日是在麦当劳过的。我的生日是4月11号,4月11号确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日子,除非一个和我同月同日出生的家伙名扬四海,它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好时辰。我是在麦当劳和同学们一起过的生日。爸爸没有回来,他还在秋风落叶的丫丫谷保卫军需仓库,仓库们活像碉堡,都是圆柱体的,有着一个尖尖的屋顶,就像是一些戴着草帽、不苟言笑的农民。妈妈也没有回来,她跟着爸爸的老战友跑边贸去了。就是那个送我弯刀的老战友,他现在据说是发了,手下有了十七、八辆大篷车,涂得花里胡哨的,载着清仓查库弄来的陈
货;在尘土飞扬的中哈边境乱窜。他邀请妈妈做他的合伙人,我觉得很可笑。我问妈妈,你都下岗了,拿什么去合伙呢?
妈妈说,除开你爸爸和他的战友情不算,我还兼着他的会计呢,算是拿我自己去入伙……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逸,我说,把你自己……拿给那个叔叔去入伙,有这种战友情吗?妈妈,这合适吗?
妈妈显然是心烦了,她心烦了就什么道理都不讲,她说,合适?我不晓得这有什么不合适!
唉,我就想,可怜的妈妈,她在闹更年期了吧,她跟我说过,她现在常常失眠、心慌、耳鸣,月经紊乱呢。妈妈下岗以后,爸爸赠送给妈妈一架老年车,约等于那种三只轮子的自行车。有一回妈妈骑着老年车横穿大街,差点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的撞倒。妈妈破口大骂司机瞎了眼,司机是个小伙子,赔着罪,说自己没有看见她。妈妈就冷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