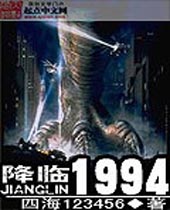5394-白星-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星》 孤星高照堕落到去挖别人的隐私(2)
“还有,过去这几天,只要我看着远距离的建筑物或树木,便开始自动推算它与我的距离,四百码、六百码、一千一百码。我的脑子开始出现各种数字,我花了十年才改掉这种随时估算距离的习惯,现在它们都回来了。”
柯茨抬起手腕闻了一下,拉高袖子又闻闻手肘。“我昨晚的确吃了鲔鱼,可是我怎么也闻不出身上有什么腥味。”
“现在我对所有出现在我视野边缘的物体,即使动作十分微小的,也都会自动加以注意。我的视线随时随地都在左右移动,巨细靡遗地看清和注意一切。这些虽然都是小事情,但它们正缓慢且不由得我不同意地改变我,好像我服了一剂很可怕的药。”
“我总觉得还是应该让警方的特警队去处理。”
“我们都见过尼柯莱·朱佐夫有多么厉害,俄方的资料也证实他在阿富汗时多么天才。所以真的必须我自己出马。”格雷深吸了一口气。“彼得,我花了许多时间想要忘记自己是一个整天抱着步枪的怪物,其实并非如此,我的天分只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能力,就像芝加哥公牛队的迈克尔·乔丹长于打篮球,或韦恩·格齐长于冰上曲棍球。早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能够很轻易地射下五百码之外一只鸟的翅膀。特警队当然有很好的狙击手,但就算隔了这么多年我没碰过枪,不管在靶场或任何场合,我仍然比他们高明太多。”
柯茨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最近常坐在办公室盯着墙胡思乱想,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
格雷用两根手指压在太阳穴上。“眼看站在我旁边的人脑袋开花,跟自己再次拿起步枪反击,哪一样会对我的精神状况更有好处?我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柯茨靠回椅背,若有所思。“越战时,我只是陆战队的文员,很多事都不知道。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越南的角色其实和轰炸机的驾驶员以及机枪员没有两样,只是你的方式比较个人。那是一场战争,大家奉命行事,可是我却觉得你一直为自己曾经善尽军人的职责而惩罚自己。”
“你的确不知道,”格雷口气粗暴。“什么都不知道。”
柯茨又谨慎地问:“你在越南时是否碰上了什么事,除了狙击之外的什么事,使你必须就医甚至提前退伍?越战中有许多狙击手,他们并不曾……像你活得这么辛苦,而且饱受困扰。”
格雷没说什么,转身走向等待他的艾柏。
当天晚上十点钟,布鲁克林区第六街那一带,白昼的热气仍未消退,每栋大楼的砖块和水泥都还在冒着热气,消防栓、火灾逃生梯和汽车引擎盖也都是热的。窗前花盆里的粉红色天竹葵和紫色的牵牛花也都垂头丧气地挂着,街上也没有一丝风,建筑物之间的空气混着汽车废气、大蒜味和臭水沟味,怎么也无法散掉。
似乎连街上的噪音都被难以忍受的燠热压低了。远处有两只猫在叫春,到街上来散步的人都静静地走着,彷佛也热得没有力气聊天。有人放着重金属音乐,也有人在看电视,声音都从敞开的窗里传了出来。
湾脊区这些整洁的公寓和四层楼的建筑,混合了希腊、美国殖民式和意大利的风格,楼房的表面也都有各式典雅的装饰。格雷一家人住的那一栋,门口是两根有凹槽的柱子,顶着一扇拱门,前廊有铁栏杆围住,古老的橡木门漆成红色,门牌号码旁边是各家的按钮,上面都没有姓名。
四层楼的窗户都漆成黑色,今晚大都开着。格雷住在顶楼,临街的大窗是两个女孩的卧室。薄薄的窗帘合拢着,可是由于卧室里灯光明亮,仍能透过窗帘的布料看见屋里的摆设和人影。
格雷那件格子睡袍是奥兰多送他的圣诞礼物。“别看书看到太晚,早些睡吧,小姐们。”
但这话像耳边风,床上的人动也没动。茱丽的床头贴着钢琴演奏家肯恩·杰瑞的海报,洛琳的床头贴着萧邦,房里衣服、书籍、洋娃娃、画图用具都堆得到处都是,洛琳的桌上还有一本《十七岁》杂志。奥兰多平常都会要她们收拾干净才能睡觉,但她从下午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进这房间来的人只好踮起脚步来走路了。
“你们今天下午一定玩得很高兴,被安雅·韦德累坏了吧?”他轻声笑笑。“连我都被她累坏了呢。”
床上的人各得到一个亲吻。“晚安啰,好好睡吧,别让睡虫给咬了。”
穿睡袍的人朝通往走廊的门口走去。
如果时间可以转换成空间,如果分秒可以缓慢些并静止下来,宣告变动的一刻就会被记录在薄纱窗帘上那个铜板大小的圆洞中。那颗子弹像一道闪电般穿过洛琳床上的躯体,射穿床头板,嵌进了墙壁。
两秒不到,另一颗子弹又穿过窗帘射进房里,打进茱丽的身体。
穿着格雷浴袍的彼得·柯茨在门后对着无线电说:“他动手了。”
在屋顶上,只有星光观测镜、头顶微微凸出于阳台护墙的艾柏中士跟着吼道:“看到了!闪光出现在第二区三点钟方向,距离四百码,正是那栋公寓的屋顶。”
短短几句话,艾柏已替狙击手指明目标的方位。
欧文·格雷透过M40A1狙击步枪上的星光观测镜开始瞄准,同时听见艾柏画蛇添足地说:“往下调两个刻度。”
“我找到他了。”格雷没有时间去对自己拔高的声音感觉奇怪,他已二十五年来不曾听到这森冷如铁般的声音。若在其他情况下,那冷酷的腔调应会让他不寒而栗。
观测镜里,格雷看到四条街之外那栋公寓屋顶护墙后的角落,低低地露出半颗头,头的旁边还有一支步枪指着天空,可能想再朝他的公寓射击,也可能正要撤退。
格雷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一半。他在狙击手生涯的早期就已悟出,不必留心脖子或胳膊脉搏的跳动,而只需注意自己的视觉,视线会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有极其短暂的模糊。他等着那稍纵即逝的模糊,扣下扳机。那是艾柏报告目标方位后的两秒钟。
步枪因后坐力撞进他的肩窝,观测镜里的视野跳向天空。
《白星》 孤星高照堕落到去挖别人的隐私(3)
亚伦·艾柏发出欢呼:“正中红心,他完了。我看见步枪也掉下去了。”他拍拍格雷的肩膀。“干得好,这种场面可不是每天看得见的。”
艾柏以无线电联络柯茨。“彼得,拿刀叉来享用朱佐夫吧,他被解决了,我们过去收尸。”
在他们下面公寓的双胞胎房间里,柯茨自言自语地说:“感谢上帝,那狗娘养的终于被摆平了。”他看向床上那两个用枕头伪装得很好的躯体,和因子弹穿过而跑出来的鸭绒。三个孩子今晚都在安雅·韦德的旅馆套房里。
屋顶上,艾柏对格雷说:“你要过去吗?我们去到这家伙的尸体上跳个舞,我想看看你像以前一样扔下一个纸星星。”
格雷把枪靠在护墙上,全身瘫软地靠着砖墙用力喘气。他知道他一定会扣扳机,他一定会的。然而重操旧业引起的痛苦回忆,以及必须拼命压下心中的反感专注于手边的工作,这些努力让他精疲力竭。好吧,现在总算完成了。他费尽力气才把自己支撑起来,拿起步枪。
他朝黑暗中远处的目标望去。他的确曾望见一个头、一支步枪,他也很有把握那一枪打得干净利落,可是他仍小声对自己说:“好像不太对。”
然后他跟在艾柏身后往楼下走。
脱去睡袍的柯茨与他们在街上碰头,一辆没有任何标识的警车立刻过来接他们。狙击手的巢穴在第十街一栋五层楼公寓的屋顶。才几分钟,他们就赶到了。
柯茨按着房东的电铃,直到他出来开门。为了怕打草惊蛇,警方并未预先通知房东今晚的行动。那人穿着汗衫短裤出来,柯茨把警徽朝他一亮,立刻拉着房东推门进去。
“带我们上屋顶去。”柯茨命令道,艾柏与格雷跟在他们身后,狙击枪留在车里。
“没问题,”房东惊叫着。“但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啊。这栋房子向来都很干净,从来没出现过妓女或毒品,只有三楼住了一对希腊人。”
柯茨推着房东的背,催他快点上楼。
“你们是来找他们的吗?”房东越来越慌。“我就知道,他们煮的东西真是太臭了。”
一到通往五楼屋顶的楼梯口,柯茨推开房东拔出身上的点三八手枪。
“用不上的,”艾柏说。“我亲眼看到他脑袋开花了。”
但柯茨仍然两手持枪登上最后那段楼梯,推开通往屋顶的门跨出去,格雷和艾柏跟在后面。
屋顶上用来防水的沥青都被太阳晒软了,黏在他们的鞋底。他们绕过突然拱出屋顶平面的楼梯间,往东侧的护墙走过去。一具尸体蜷曲着,倒卧在距屋顶边缘三英尺的地方。格雷的眼睛尚未适应,他知道视力完全恢复正常需要三十分钟,可是即使如此,他仍看得出,那具尸体倒地僵卧的姿势,弯得不太正常。
他们再走近一点,鞋底已经开始踩到溅得一地的脑浆。
“怎么回事?”柯茨突然喊道。
尸体被绑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一大堆绳子由胸到腰到脚地把它紧紧绑在椅子上,嘴上还用水电专用的宽幅胶布贴着。
一支枪甩在尸体旁边不远的地方,艾柏捡起那武器。“史蒂文斯点二二的枪,没有狙击手会用这种枪。怎么回事,这是某种伪装吗?”
柯茨则在尸体旁边拾起一枚涂有红漆的弹壳。“朱佐夫的商标在这里。”
格雷蹲下来,用手扳住尸体肩膀,把它的脸翻过来,小铃铛的声音轻轻响起。原本长着满头黑鬈发的脑壳已被打碎,只剩下血肉模糊、脑浆横流的下半截脸还勉强看得清楚。
奥兰多剩下来的半张脸上,一对无神的眼睛瞪着他。
《白星》 破釜沉舟刚好在手边的就是最好的武器(1)
刚好在手边的就是最好的武器。
——阿富汗谚语
9
欧文·格雷将要回归大地,回到山里,回到他的老家。只有大地才能收容他、拥抱他。山岩、树丛和夏日的热风,将能让他再次呼吸,让他在花岗岩和野草丛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或者,他将死在这些山岭之中。
他终于领会尼柯莱·朱佐夫信息里的意思了。那个俄国人想赶他离开城市到荒野里,前往一个适当的决战地点。在格雷就范之前,敢靠近格雷身边的人就会遭殃。
如今,朱佐夫应该会尾随格雷进入山区。格雷想趁对方出现之前尽量做好准备,应付即将面临的挑战。俄国人必定很快就能推测出他去了哪里,而且马上就会追上来。格雷不知道朱佐夫何时会抵达山区,但应该很快了。时间已所剩无几。
那条泥路上长满了盛开的野花,椭圆的叶子刮着租来的吉普车的两边。格雷必须使用四轮驱动车的加力档,才能将车开上抵达狩猎小木屋前的那段陡峭山路,开过最后几百码。轮下的小石块因此四处飞散。峡谷中白色的冷杉和马尾松此时已变得稀稀落落,被容许晒到太阳的紫丁香和野山梅因而长得十分茂盛。格雷十二岁时就已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甲虫的幼虫会吃掉紫丁香茎部的心,蛀空的细杆便可以拿来当烟管,而山茱萸叶子混合甘草蕨则是不错的烟草。他从小就对爱达荷州三个印第安族的风俗习惯很有研究。
他把车速慢下来,让吉普车绕过一块巨岩后,已经能瞥见木屋前面空地上种的那棵巨大的落叶古松。这种树干挺拔、只有顶端有枝叶、高达两百五十英尺的巨松,在这一带并不多见。自格雷记事以来,这棵巨松就像哨兵那样,一直守卫着他祖父和父亲传下来的木屋。
他开着吉普车绕过松树,驶上为防止春天雪融时的泥泞而铺了碎石的小路,到前门外的空地上停住。打开车门,爱达荷的山景迎面而来,美不胜收的山花、绿树、奇岩,各种植物的芳香、湿润的泥土味,全部一览无遗,让他渴望回到过去,并想起往昔的人与物。
他绕过车头,朝木屋的前廊走去。用圆松木材筑成的木屋,是格雷家族三代人的出生地。
一九○三年刚刚盖起来时,这里只是一间简陋的小房子,有一扇门和油纸糊的窗户,几十年来增建了好几个房间,也铺了硬木地板,添加了水电设施、阳台、厨房、壁柜和一座很大的石砌壁炉。格雷走进前廊,用钥匙开了门进去。
屋里有些微的霉味,还有灰尘和干燥松木的味道。格雷任由大门开着,先拉开窗户上的护板让光线进来,记忆也跟着阳光涌入。这里面的每样布置、每个角落、每条缝、每件用得斑驳的家具,都是跟他一起长大的。格雷的父亲将屋子连同四周的五百亩地,一起传给了他。
平常,他托住在十几英里外山下小镇上的一位老友每星期上山打扫整理一次,还把屋子出租给猎人,收来的租金用作维护费用。
他家的传家宝还放在角落里。据格雷的父亲说,那张椅子是他祖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鹿角制作的,它的座位和靠背是内塞马毛的鹿皮,其他的椅脚、扶手、框架全是巧妙地接在一起的鹿角,总共二十几支,到处都是交错的弧线与危险的尖端。它的怪异让格雷的母亲既想丢掉又非常舍不得。这件引人注目的传家宝既然不好坐,又要花三十分钟才能擦干净,格雷只为了证明自己敢坐才坐过几次,每次都迫不及待地跳下来。现在它仍盘踞在角落里,看谁有胆子敢接近它。
当年不缺木柴,那座大壁炉几乎占了靠西的一整面墙,炉架和炉床都是用河里的石头砌成的,木柴箱大如小金龟车,炉前的栅栏则是找铁匠用驴子拉的雪橇改造的。
他的家族一直都跟鹿角有很深的渊源。在这屋子